致敬李文亮,致敬疫情中的每个普通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玮
第一次读加缪的小说《鼠疫》时,我还是个本科生,当时更多想要挖掘的是加缪在关于鼠疫的叙述背后传达的更深层的“思想”(比如反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以及这部小说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带着沉重的心情重读了《鼠疫》,却感到小说最表层的文字所传达的精神就足以让我感动至深,加缪在小说里描写了很多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与鼠疫的战斗做出了贡献。他们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更多就是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遇到了某个机会,发生了某种转变,而促使他们转变的从来不是英雄主义或者圣人情怀,而一次次对“人”的直接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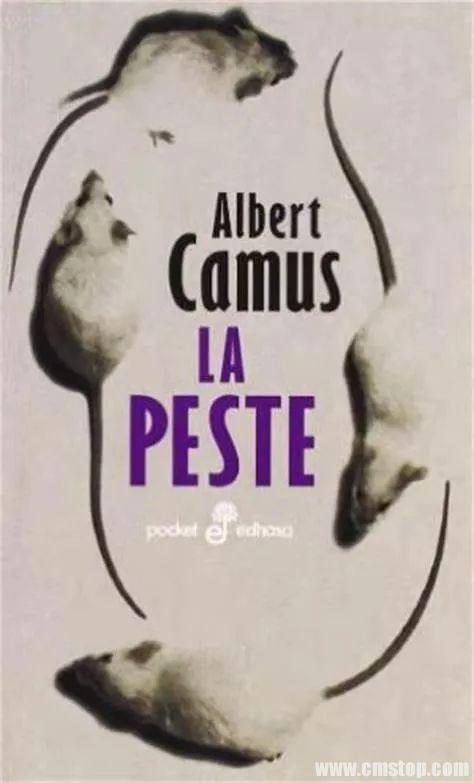
塔鲁的父亲是一个检察官,他曾经邀请年轻的儿子去旁听一次庭审,希望他能够子承父业。结果儿子却被那个充满恐惧、不断咬自己指甲的被告深深吸引,那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被告”这个范畴来概括的抽象物。相反,他父亲代表法律和正义发表的那一套想要至被告于死地的慷慨陈词却让塔鲁难以忍受。他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之后为废除死刑四处奔走。他承认世界上有很多祸患,但是坚持一定要尽可能站在受害者一边。 帕纳鲁神父在书中做过两次布道。第一次是鼠疫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他站在上帝的视角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带着豪迈的气概向教众宣扬这是上帝对人们道德败坏、信仰松弛的惩罚。后来,他近距离地看到一个无辜的男孩被鼠疫折磨后失去了生命,这让他深受触动,不久他做了二次布道。这一次他对教众讲话时把“你们”换成了“我们”,他承认了鼠疫带来的痛苦,甚至质疑信仰承诺的永生和幸福是否足以抵消今生的痛苦。他同时号召人们不要放弃信心,用爱继续与鼠疫战斗下去。 来自巴黎的记者朗贝尔在鼠疫发生之前碰巧来到阿赫兰城。鼠疫爆发之后,阿赫兰完全封闭,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朗贝尔焦急不堪,只想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的女友身边。他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屡试无果之后又想要通过买通守城的门卫逃离阿赫兰。但是在参与到里厄、塔鲁等人为鼠疫进行的抗争之后,他放弃逃离的计划,他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但是我看到了这一切,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一员。”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哲学家
加缪用近乎冷峻的、历史学家式的笔调记载了很多让人心碎的场景和令人愤慨的场景。这里有普通市民的惊恐绝望,有患者和家属的生离死别,也有经过漫长的瘟疫之后人们的麻木冷漠。这里有行政人员的不作为和踢皮球,有商人的囤积居奇和发瘟疫财,也有人宣扬迷信和妖言惑众。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加缪对普通人的赞歌。小公务员格朗、法官奥东、做走私生意的冈萨雷斯,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了这场对抗疫情的战斗。整部小说最核心的人物里厄医生本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因为是他最早意识到鼠疫的来临,是他坚定地主张要告诉民众实情,也是他自始至终坚守在直接面对病人的第一线。但是加缪却只用最平实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里厄大夫的理想不过就是让人尽可能避免因为灾难而死。在他眼里,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帮助这些人,让他觉得没有愧对自己是“人”这个身份。对抗瘟疫,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诚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最早向外界发出预警,被称为疫情“吹哨人”
如今身处疫情之中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令人心碎的场景:本该喧闹却无比冷清的春节,劳累过度穿着防护服躺了一地的医生护士,因为医疗资源紧张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和家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令人愤慨的事情:隐瞒真相、一问三不知的官员;把发文章看得比对抗病毒更重的“学者”;坐地起价的药房和超市;瞒报出行记录造成恶劣后果的旅行者。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身边一个个平常人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投入到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在春节告别家人整装出发“逆流而上”的医生和护士;在疫情期间如常经营的超市、药店;不厌其烦地宣传抗疫知识、进行体温监测、登记返程信息的社区工作人员;与时间赛跑、加班加点建设新医院、赶制口罩的一线工人;深入疫区报道疫情的记者和制作正能量视频的编辑;自冒风险坚持将快餐外卖和生活物资送到医院及居民手中的快递员;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坚守岗位的公共交通运行人员;在线免费问诊的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各行各业通过移动办公方式履职的人们。 面对疫情中出现的种种场景,我们并不需要多少伦理学理论的武装,因为高下立现,善恶立判。作为身处疫情中的大多数人,我们也不需要用英雄主义或圣人情怀鼓励自己做出惊天动地的举动。我们只需要怀着同情之心、善良之心,诚实地面对每一个真真切切的人,我们就都是这场战斗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