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通进:疫情防控、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通进
人类最初是作为自然存在物出现在地球表面上的,并把自然作为其文化创造的背景舞台。然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技术化与人工化。“技术圈”逐步遮蔽和取代了“生态圈”。自然渐渐隐退,似乎只存在于浪漫主义者的乡愁中。被“技术圈”所包裹的现代人,似乎很难感受和“捕捉”到自然的存在。自然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凭借先进的技术,人类似乎可以完全可以不依靠自然而建立一个技术化的“人工伊甸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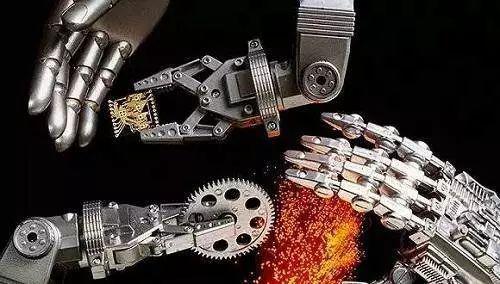
然而,武汉肺炎的爆发使人们再次觉醒。面对自然,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人类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密不透风”的技术圈并不能把人与自然隔离开来,既无法阻隔“自然”对“文明”的渗透和侵蚀,也无法确保高效率的现代生活永远“照常进行”。

自然是文明的根基。无论工业文明的技术化如何发达,人类都必须要首先处理好人与自然(包括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与其他生命、以及整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天人关系”依然是人类无法逃避、且必须面对的“第一哲学问题”。
一、动物保护与环境伦理

与18年前的萨斯病毒一样,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再次迫使我们重新拷问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源于蝙蝠或穿山甲的推测,我们首先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动物。
人类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动物。这些动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人类与驯养动物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历史悠久。这些动物虽然也携带多种病毒,但是,这些病毒不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灾难,这或者是由于,这些病毒不能直接传染给人类,或者是由于,人类对这些病毒已经具有免疫力(通过疫苗种植或先天获得等方式)。因此,人类与驯养动物大致能够和谐相处,俨然构成了一个“混合共同体”,并达成了某种“未言明的契约”,即人类为这些动物提供食物,确保它们的繁衍,这些动物则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或为伴侣,或提供劳役与娱乐服务,或成为食物)。人类与驯养动物的交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善待”,即不给这些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善待原则的伦理基础是同情与怜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国家逐渐实施“动物福利法”,“善待”原则更是被赋予了很多“积极的内容”,驯养动物的生存状态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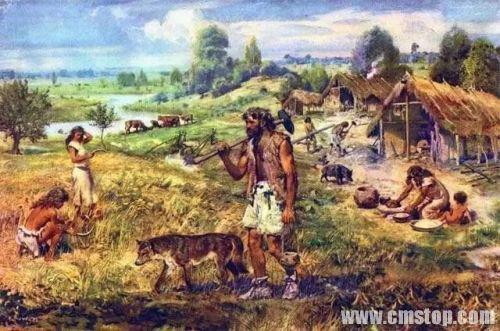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总的来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交往具有较多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绝大部分野生动物都生存在自然界中,也有部分野生动物(如蝙蝠、老鼠、蚊蝇等)与人类“杂居”。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许多公共卫生事件(如历史上的黑死病、以及其他流行病的爆发)都是源于人类与这些动物的“不当交往”:或者是过于深入地侵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者是“过度亲密地”接触野生动物,或者是食用野生动物。此次引发武汉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或穿山甲携带的病毒高度重合。对于此次疫情,某些人与这两种野生动物的不当交往(尤其是贩卖和食用)难辞其咎。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野生动物(尤其是与人类杂居的野生动物)的关系,是预防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

一般来说,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往应遵循不干扰与自卫的原则。对于那些不对人类的根本利益(安全、健康、生命、以及其他重大利益构)构成威胁和伤害的野生动物,人类应当尽量不要去干扰,遵循“人类活也让野生动物活”(living and let living)的“共生理念”。对于那些对人类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和伤害的野生动物,人类则可基于自卫原则对这些动物予以限制。但是,即便是自卫,人类也要基于理性与责任。
首先,只有当人类的根本利益与野生动物的类似利益发生冲突时,人类才可牺牲野生动物的利益以确保人类的根本利益。当人类的非根本利益(如以虐待动物为乐)与野生动物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人类应做出适当让步。
其次,即使不得不伤害野生动物,人类也要基于科学理性把这种伤害控制在最底的限度内,而不能基于盲目的“恐惧”而将这些动物“赶尽杀绝”。在捍卫自身利益时,不毁灭野生动物物种是人类行为的底线。再其次,人类应当尽量给野生动物留下足够的栖息地,以便野生动物能够自行繁衍。如果人类为了满足其根本利益而不得不侵占某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么,他们就应当在其他地方保护该野生动物种群的栖息地,以免该野生动物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维护野生动物物种的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重要责任。

最后,不提倡人类饲养和食用野生动物。即使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不得不饲养和使用野生动物,也应遵循动物实验的3R原则,即优化(refine)、减少(reduce)与替代(replace),并根据动物福利法的基本要求,确保试验用野生动物的基本福利。
如果人类在与野生动物交往时遵循了上述基本原则,那么,人类与野生动物就能相安无事,甚至和谐共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工业革命以前,地球上的的物种(包括动物物种)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自6500万年前白垩纪的最后一次物种大灭绝事件以来)。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逐渐被人类“侵占”。在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号角面前,许多野生动物灭绝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被迫与人类“杂居”,那些“侥幸”还保有栖息地的野生动物则在生存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有鉴于此,人类在与野生动物交往时,更应该秉持一份“愧疚”和“节制”。生命是一道奇迹。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物种”,人类应自觉承担起看护和守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责任,选择能够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二、尊重自然与生态文明建设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只有走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工业文明所遭遇的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动物)的矛盾和冲突。
生态文明是以吸收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不仅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价值理念,还包括确保人们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制度。生态文明在借鉴和吸收工业文明的这些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将致力于克服工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把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与人权理念落实为全球层面的制度安排,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最终克服近代以来把人类带入“全球囚徒困境”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来,我国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创新工作,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这次武汉疫情的爆发表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短板和局限。
首先,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还非常脆弱,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城市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过度的城市化也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风险。不合理的生态空间布局使得绝大多数大城市陷入“承载力超载”的困境。绿地的减少和拥挤的城市空间布局导致城市的环境卫生严重恶化。大量的城市垃圾给老鼠等“食客”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寄生在大城市的野生动物数量随之增加。污染严重的环境,人与动物的无序杂居,流动性高的人流,拥挤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这些都为疫情的随时爆发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因此,为了避免武汉疫情这类悲剧的重演,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态文明的建设,把中央关于生态空间布局的政策(即把生态空间区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落到实处,并依照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调整或修改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使城市空间布局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提升城市应对各种风险(尤其是流行病爆发)的能力。

其次,我们的城市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我们的城市治理也必须积极贯彻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政治文明,它既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把尊重公民的的基本权利视为实现人与自然之和谐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的城市治理应当以人为本,应当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为目标。武汉疫情的爆发表明,我们的城市治理能力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治理在环境保护、医疗保障、基本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还比较小,我们的城市管理过于注重秩序与城市形象,对城市弱势群体、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关注不够。
另一方面,某些领导和官员的“体制性思维惰性”比较严重,对公共权力的使用比较“任性”,人民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比较淡薄,过于重视管理的效率,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不够,甚至“克扣”和“削减”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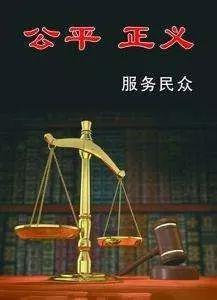
武汉疫情防控遭人病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有关部门不够尊重人民的“知情权”,侵犯了公民的正当的言论自由权,导致“为众人抱薪者冷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的悲剧的发生。因此,我们的城市治理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在污染治理、环境卫生、公共健康等方面的投入,而且要诉诸法治思维,提高治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和基本自由的日益增高的诉求。
最后,我们应当把生态文明的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结合起来。
一方面,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五大支柱之一;生态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向度。
另一方面,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全球环境问题。除非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否则,任何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不可能成功。

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密不可分。流行性疾病的跨国传播,更是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角度看,我们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向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一方面要在应对全球环境与全球健康风险等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及时通报疫情风险,共享预防和治疗各种跨国性流行疾病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把跨国性流行疾病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与不便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角度看,我们还应加强全球共享价值的建设,提高国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预防和抵制各种排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似乎总是要遭遇大灾大难、日常生活都已经无法正常进行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来关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的制度建设。但愿这次的武汉疫情能够成为提高国人的环保意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助推剂。
(在本文即将完成之际,武汉疫情的八位“吹哨者”之一李文亮医生因感新型冠状病毒不幸逝世。仅以此文纪念李文亮医生。愿他的责任感和良知在天堂不会被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