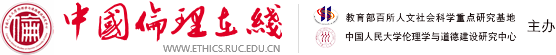新书推荐|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
摘要: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讽刺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包括散文、诗歌、政论等,但至今只有《格列佛游记》为中国读者熟知。这部斯威夫特作品集,除首次翻译《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和《书籍之战》外,还提供了《木桶的故事》新译本(从Walsh编本的150余页注释中选译了少量注释),另附沃顿对《木桶的故事》的反驳,以及几则相关文献。

内容简介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讽刺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包括散文、诗歌、政论等,但至今只有《格列佛游记》为中国读者熟知。这部斯威夫特作品集,除首次翻译《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和《书籍之战》外,还提供了《木桶的故事》新译本(从Walsh编本的150余页注释中选译了少量注释),另附沃顿对《木桶的故事》的反驳,以及几则相关文献。
随着我国学界古典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文学作品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斯威夫特的作品不仅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也是我们更透彻理解西方“古今之争”的门径。另外,刘小枫教授为本文集写了题为“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的五万字长篇导言,揭示了斯威夫特及其写作在整个思想史大脉络中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讽刺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包括散文、诗歌、政论等,其《格列佛游记》在中国家喻户晓。
译者简介
李春长,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在美国诗人庞德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曾在《外国文学》、《中山大学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几篇;翻译《论古人的智慧》(2006)、《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2015)等3 部,译文十余篇,总计70余万字;出版专著《庞德乌托邦思想研究》(2015);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庞德《诗章》的主题思想研究”(08CWW002)与江西省社科项目“英国中世纪诗歌溯源与影响研究”(08WX60)等课题。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研究”(16BWW051)及两项省级教改课题。曾教授本科生研究生《英国文学选读》《英语论文写作》《英美文学经典选读》《当代文学理论》《科研方法论与论文写作》《当代文学》《学术英语》等课程。
目 录
中译本导言: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刘小枫)
木桶的故事
书籍之战
论圣灵的机械运转
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
附录
评《木桶的故事》(沃顿)
坦普尔遗著的编辑问题(斯威夫特)
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节选)
刘小枫
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种文化史分期观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欧洲文化史“常识”,也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认识。然而,由于这种分期观忽略或者说删除了古今之争这一发生在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欧洲知识人(更不用说在中国知识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识”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常识:古今之争不仅堪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称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古今之争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一说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论争;广义的古今之争得从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算起,一直贯穿到当代。狭义的古今之争起初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伦敦爆发,两个战场很快融为一个战场,并向欧洲其他学问城市蔓延——比如维科所在的那不勒斯,以至于催生了《新科学》(1720年第一版)这样划时代的著作。研究古今之争的已故权威学者列维尼(J.M.Levine)说:
这场论争更像一场伴随有许许多多小冲突的持久战,而非只是大战一场;它铺天盖地地展开战斗,涉及了无数问题,但论战双方最终都没有(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分出胜负,而是陷入了某种僵局。
所谓“陷入了某种僵局”,未必符合历史实情。毕竟,古今之争刚刚兴起,崇今派就取得优势,孕育了托兰德(1670—1722)这样的年轻且激进的启蒙哲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前辈伏尔泰(1694—1778)出生在巴黎爆发古今之争那年,可以说是在这场持续论战中长大的。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标志出版,已经是著名文人的伏尔泰当时正旅居柏林的普鲁士宫廷,他深受鼓舞,决意亲自撰写一部类似的启蒙辞书,名为《袖珍哲学辞典》。这部辞书后来集成四大卷,其中的“古人与今人”词条一开始就说,“古与今的大论战还没有完结”……尽管如此,伏尔泰通篇以崇今派已经完胜的笔调来描绘刚刚过去的古今之争。事实上,《哲学辞典》站在现代新哲学的立场上全面贬抑所有古老文明(而非仅仅贬抑西方古代文明),本身就是一部参与古今之争的“战斗性哲学著作”。十分明显,启蒙文人是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的嗣子。我们虽然不能说,谁编撰辞书或掌握了教科书的编写权,谁就赢了,但既然启蒙文人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列维尼就得承认,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赢了。
当然,从西方思想史的长河来看,由于卢梭、莱辛、尼采乃至20世纪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地位迄今居高不下,列维尼又的确有理由说,崇古派未必在思想上输了。他说古今之争“陷入了某种僵局”,而且是历史的僵局,的确没错。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如今的思想怪现象:我们虽然由崇今派抚养大,却仍然觉得崇今派不及卢梭、尼采和海德格尔有智慧,其思想不及后者深刻……
责任编辑:廖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