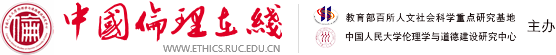新书推荐|劳埃德-琼斯:《宙斯的正义》
摘要: 劳埃德-琼斯教授认为,“正义”观念是早期希腊宗教的核心要素。因此,作者以荷马笔下的“正义”为核心,兼及古希腊戏剧家和哲学家们的正义观念,概括了从荷马史诗直到古典时代“正义”概念的特质,勾勒出古希腊正义的丰满图景,从而思考了希腊早期宗教信仰的总体特征。

内容简介
劳埃德-琼斯教授认为,“正义”观念是早期希腊宗教的核心要素。因此,作者以荷马笔下的“正义”为核心,兼及古希腊戏剧家和哲学家们的正义观念,概括了从荷马史诗直到古典时代“正义”概念的特质,勾勒出古希腊正义的丰满图景,从而思考了希腊早期宗教信仰的总体特征。
作者介绍
劳埃德-琼斯爵士(Hugh Lloyd-Jones),英国古典学家,牛津大学钦定古希腊教授,著作等身。参与主编米南德的《狄斯克鲁斯》,大型古典丛书“牛津古典文丛”中的索福克勒斯卷,以及大名鼎鼎的“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埃斯库罗斯残篇和索福克勒斯两卷亦由他负责编译。劳埃德-琼斯教授是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五家外国学会的成员,拥有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89年从钦定教席上荣休,被授予“爵士”称号。《宙斯的正义》是其众多著述中的一部代表作。
媒体评价
什么是正义?要想理解往昔欧洲最富于生机的东西,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可惜从未有人如此明确地发问过,遑论有力作答了。劳埃德-琼斯教授1969年在伯克莱的萨瑟讲座中做到了这一点……
以最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这本书必须视为与其伟大的古代前辈等同:它是新一代学人思想的结晶,反映了他们关于希腊人的现实乃至实在本身最犀利、最深刻的思考……
本书代表着作者本人的巅峰成就,可能要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能看到与它匹敌的东西。
——《时代》杂志文学副刊
劳埃德-琼斯教授认为,“宙斯的正义”基本含义是指某种神定秩序,类似于自然法。这种正义观自然而然导出其附属含义,即道德法意义上的正义观。从一个自然过渡到另一个,其间保持连续。琼斯爵士此书的贡献在于,它从希腊文化史的维度,对众多、历代古希腊经典进行了广角镜似的扫描。
——John Peradotto(1975)
目录
中译者前言
二版前言(1983)
前 言
主要文献缩写
第一章 《伊利亚特》
第二章 《奥德赛》、赫西俄德与早期抒情诗
第三章 玷污与净化:希罗多德
第四章 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和埃斯库罗斯
第五章 索福克勒斯
第六章 智术师、修昔底德与欧里庇得斯
第七章 结 论
跋
术语表
现代作者姓名索引
一般名词索引
中译者前言(节选)
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求,在古今中外都得到极大重视,但“正义”的内涵及其基础却大不相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被称为“正义”的dike首先不是人世间的伦理规范,而是宇宙秩序,后来才演变为人世的准则。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正义”的来源:人世间的公道正义乃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而宇宙秩序又是神明所设定的,因此,行事正义就是对神明的崇敬,因而正义本身就是虔诚。反过来说,不正义既违背了自然天道,又是可怕的渎神之举,当然要遭天谴和神罚。
古希腊正义观的这两种含义或维度大概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但与我们通常庸俗的理解不同,这种“合”不是平等的相互契合,而是差序格局中低级对高级的“符合”。这与后世的正义观大不相同。随着宇宙变成“自然”,本身无限丰富的“自然”坍缩固化为物质性的东西,宙斯的正义便不复存在。新的正义观在消除了神圣的维度后,只能以人的理性为准绳,而所有人的理性据说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正义”就成了平等的代名词,它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巨大的偏转。
这个理性化的潮流带走了古风时期很多美好的东西,最终似乎造成了人类(至少西方)社会的种种灾难。批判理性主义从古代开始就不乏其人, 20世纪之后,这种倾向更是泛滥成灾。毕竟,据说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拜理性主义所赐,至少是因为理性主义从上到下的理论建构让思想失去了自然的土壤。这种无根的逻辑产物要求现实给它让路,凡是不符合理性或逻辑理想的,都要被终极解决。
理性主义的第一场灾难就是雅典的衰败,本书作者琼斯认为,柏拉图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柏拉图则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与东方宗教更多相同之处,也与一神论以及现代世界无论是宗教上的还是世俗思想中的教条体系更为一致。很多讨论希腊衰亡原因的作者,都曾用到伯里(J. B. Bury)的术语 “精神衰竭”。而第一个重要的精神衰竭就是柏拉图的衰竭。(原文,页 136)
一般的思想史著作都会把希腊的衰亡算到智术师头上,毕竟,他们教导的东西,如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等,败坏了雅典高贵的传统道德。但琼斯认为,普罗塔戈拉这类智术师的观点反而更接近希腊人的传统看法,这着实令人费解。
在琼斯看来,新兴的哲学思想虽然抛弃传统的神话学,但并不因此就主张无神论。思想新贵们对传统神学加以理性化处理后新产生的一神论信仰,与古代信仰不仅不相抵牾,还能和谐共生,就像现代思想家并不与现行宗教相冲突一样。其理由就在于,古代的无神论从来没有引发过任何社会问题。但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才算得上是大问题?直接导致古希腊的衰亡——这还不算严重的社会问题吗?作者批判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批判了智术师,柏拉图把希腊人的无神论和非道德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政治军事灾难都算到智术师头上。但作者却认为,恰恰是那些保护传统思想的人最终破坏了传统,因为他们太过保守和虔敬!
本书作者采纳了多兹(E. R. Dodds)的看法,认为柏拉图经毕达哥拉斯学派而受到了东方宗教的影响,“把希腊理性主义传统与巫术-宗教的观念杂糅在一起”,因而提出了灵肉二分的观念,从此开创了西方二元论的先河。柏拉图偏离了传统的生活经验,过度诉诸理性,因此本书作者批评道:
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从原初的假设出发作出推导,但不能指导我们选择从哪一个假设出发,我们也很难强说,某一套关于神明本性或宇宙管理方面的主观假设,就比任何其他假设更“理性 ”。(原书,页 163)
就算柏拉图在自己的对话中极力弘扬“神明”,打算通过重建官方崇拜来训诫和引导普通人,那也与希腊传统宗教几无共通之处。柏拉图的超越性的理性宗教或许有高明之处,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这种新宗教关心的主要不是“此”世的现实。
本书作者关注的不是思想史中的“变易”,而是长期保持静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希腊人早在公元前 5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之前就已经十分成熟的世界观。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地说,但他的意思很显然:古希腊早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被哲学(尤其是柏拉图)败坏了。早期希腊人已经达到了一种高超的理性思考水平,远远超出了东方人,而柏拉图等人从学于东方,反倒让希腊文明有所退步。
作者直接提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希腊本土文明的独特性:
第一,希腊宗教既不是一神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多神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希腊宗教有很多神明,但从我们所知最早的时期开始,就有一个大神统管着其余神明。第二,这种宗教不以人类为中心,凡人不过是低级神祇创造出来的,在宇宙中也仅仅占据较低的地位,神明也不太在乎他们。第三,这些神明不是超验的,而是内在的(immanent)。他们不从外面干涉自然规律,而是通过自然进程统管无生命的世界,并通过凡人的激情来统管有生命的存在物。(原书,页 160)
其中,第三点似乎尤为关键,作者后来进一步阐释道:
神明通过自然和人心,而不是通过外部的干预来维系。宇宙由因果律来管理,这种宇宙观是思考宇宙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先决条件。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哲学发端于古希腊人而不是其他任何民族?要回答这个无法回避而又困难的问题,当然会从这个说法开始:有序宇宙这一观念为希腊人所独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东方邻居截然不同。正如第四福音书明白所示,基督教的最初假设虽然来自启示,但也破例接受了这种有序宇宙的观念。这种观点不来自犹太教,也不来自其他任何东方思想。(原书,页162)
凡此种种,当然都不无道理,不过要把希腊本土文明与东方彻底隔绝开来,只强调它的原创性,似乎就很危险了。理性宗教的神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的神大不相同,但也未始没有共同点。诚然,理性化的神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当然无法让人感到亲近,从而真正产生依附的情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后来形而上学化的神已经变成了哲学上的“自因”,反过来说也一样:
自因(Causa sui)……是哲学中表示上帝的名符其实的名称。人既不能向这个上帝祷告,也不能向这个上帝献祭。人既不能由于畏惧而跪倒在这个自因面前,也不能在这个上帝面前亦歌亦舞。
但在传统的祭祀规程中,歌舞乃是尊荣神明的必有节目(《俄狄浦斯王》 895)。但理性既然是不可逆的自然而必然的过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
我们无意来评判这场灾难的责任,也不会为柏拉图辩护——他也不需要谁来为他说什么好话,毕竟,他的著作就摆在那里,里面既有理性主义的主张,也不乏对逻辑、理性、二分法(甚至辩证法)的冷嘲热讽。单纯地截取某一个方面,发现其问题,再予以批判,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正义”。我们在这里只想简单为“理性”以及“理性主义”分辩几句。
诚然,现代世界“越来越热衷于逻辑和对世界的逻辑化”,越来越看重脱离了生活的理性,因而越来越走向颓废。与尼采一样,张志扬教授也在批判过度理性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理性本可造就的秩序,反而导致了极度的混乱:
现行的世界,不是没有理性,也不是理性太少,相反,恰恰是理性太多,多到混乱的地步。每一种理性都只看到自己光亮的部分,甚至干脆认为自己就是光亮本身,因而非己之其他理性都是特殊的、未开化的,甚至野蛮的、黑暗的等等。于是,理性之争,诸神之争,争高低之序,争主奴之别,成为当今世界混乱的原因。
似乎要摆脱现在的糟糕局面,只有告别理性,毕竟理性乃是现代危机的渊薮:
唯当我们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
海德格尔把现代社会很可能毁灭人性的技术化潮流归结为理性主义的结果,而理性主义又是希腊哲学的结果,所以要发现和超越理性主义的界限,似乎就必须告别理性,尤其要告别希腊哲学。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试图把握存在和整全,这是办不到的(其实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也重复着自己所批判的对象,无论他如何摆脱和撇清自己,他的“基础存在论”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余绪),因为,正如施特劳斯所概括的:
理性主义自身依赖于非理性、非明证的假定;理性主义虽看似权倾一时,却是空虚的;理性主义自身依赖于某种它无法主宰的东西。一种对存在(being)更恰切的理解为如下断言所暗示:存在(to be)意味着不可捉摸,意味着一种神秘。这是对存在的东方式理解。因是之故,东方并无主宰意志(will to master)。仅当我们变得能够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学习时,我们才能指望超越技术性世界社会,我们才能希冀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可中国正屈服于西方理性主义。
如果诚如本书作者所说,柏拉图与东方宗教关系密切,甚至谦虚地从学于东方,那岂不正是海德格尔所希望的?既然如此,海德格尔为什么一生都在跟柏拉图过不去,甚至还把西方文明的危机这笔账直接算在柏拉图头上?
东西方需要交汇(meeting),双方都必须做出努力,也就是要首先清理自身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大概就是要清理作为本己至深根源的理性主义。否则,东西方的交汇就没有可能,因为这种交汇不能在东西方最浅薄的时期发生,更不能在最吵嚷、最轻率和最浅薄的打工者之间发生。在没有充分理解对方之前,仅仅因为看到了自身的问题就喜新厌旧、自我痛恨,同时对异域风情的东西充满好感,这种做法大概就是浅薄的。
责任编辑:廖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