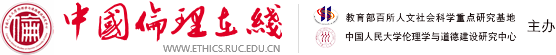新书推荐|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
摘要: 巨人与侏儒》是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布鲁姆的文集,书名取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布鲁姆之所以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对他而言,区分人的禀赋与自然差别,区分事物的好坏,乃是一切政治哲学的起点。

巨人与侏儒:1960—1990
[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著
张辉 等 译
华夏出版社,2020
内容简介
《巨人与侏儒》是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布鲁姆的文集,书名取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布鲁姆之所以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对他而言,区分人的禀赋与自然差别,区分事物的好坏,乃是一切政治哲学的起点。
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先哲们的高贵精神遗产——那些伟大的书。用先哲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臆想来判断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不仅由现代反观古代,而且更透过古代反思现代的问题,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
布鲁姆呼唤读者不放弃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追问,这样才能在所有看似无区别的生活样式中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只有以伟大思想的范例为对照来审察生活,我们才不至于简单认同那些末人哲学和侏儒人格。
作者介绍
阿兰•布鲁姆(1930-1992),当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早慧的天才,1955年 25岁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分别任教于耶鲁、康乃尔、特拉维夫、多伦多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并最终回母校芝加哥大学鼎鼎有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施特劳斯学派中的重要人物,被誉为该学派第二代的掌门人。布鲁姆既是一个公众人物,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才华横溢的哲人。他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令人一读难忘,是现代少见的兼具诗人和哲人气质的极具魅力的人物。
译者介绍
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前言
西方文明
书籍
巨人与侏儒
政治哲学与诗
基督徒与犹太人
《理查二世》
《希帕库斯》或《好利者》
民主社会的政治哲学家
《伊翁》或《论〈伊利亚特〉》
柏拉图《伊翁》解
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
《爱弥尔》
卢梭
老师们
纪念施特劳斯
雷蒙·阿隆
亚历山大·科耶夫
我们时代书籍的命运
商业与“文化”
文本的研习
正义
自由教育的危机
大学的民主化
致谢
索引
译者前言(节选)
记得2002年初夏,我在《书城》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短文,题为《在恐惧巨人的时代》,介绍阿兰·布鲁姆(1930—1992)的著作和思想。时隔不久,编辑李二民先生便转来一封读者来信。信中称,我的小文或许标志着知识界某种新的思想动向:“解构之后,试图重建的可能”。
十年过去了,当我准备为《巨人与侏儒》这个中文全译本撰写前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又想起了那位低调而敏锐的匿名读者所说的话。那句话,简洁而语重心长。
遭遇布鲁姆,究竟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什么?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桀骜不驯的犹太裔美国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观自己、反观我们的时代?我们解构了什么?我们又需要重建什么?如何重建?
《巨人与侏儒》当然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标准答案,更不要说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了。但细读布鲁姆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年间的这二十篇文章,无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沾沾自喜于我们所谓的“开放”与“现代”。在现代性的背景前,我们 “精神封闭”的程度,比布鲁姆所激烈批判的美国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带着很多消极的中国特色。
这其中,也许就包括我们对诸如布鲁姆这样的思想者的盲视和无知。即使大量翻译和介绍了他们的著作,也依然出于现代人“良知的傲慢”而带来的盲视和无知。
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明显的是,布鲁姆很难被归入哪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不错,他是著名思想大师施特劳斯的第一代传人,又在法国师从雷蒙·阿隆、亚历山大·柯耶夫等,可以说是师出有门;而且,早在1955年25岁时他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分别任教于耶鲁、康乃尔、特拉维夫、多伦多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并最终回母校芝加哥大学鼎鼎有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他的这些学术经历,即使按时下学院政治的标准衡量,也毫不逊色甚至足以骄人。但是,他的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却会让许多“专家”摸不着头脑。他是政治哲学教授,但是,他的很多文章却讨论了诗——广义的诗,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奥斯丁、司汤达、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他甚至与人合作了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专著《莎士比亚的政治学》,被他的好友唐豪瑟评价为:“我们时代最为不朽的莎士比亚评论之一”;而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伊索克拉底,应该属于古典研究范畴,可是他一生中除了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使之成为最重要的英译本之一,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卢梭,翻译并注解了《爱弥尔》以及卢梭给达朗贝的信(《政治与艺术——关于达朗贝“论剧院”一文的信》),似乎是一个法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家。如此上下古今纵横交错,难怪关注者寥寥矣!甚至包括他的最后两本文集:《巨人与侏儒》及《爱与友谊》,书中涉及的文类,传统上几乎也都应该属于文学范畴(poetry),而并不是哲学论文(treatise),因而很难用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谓专业分工来圈限。前一本书的书名,首先使人想到的是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似乎与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很远;而后一本呢,一开篇讨论的是《爱欲的沦落》,最后则以《爱的阶梯》煞尾,分明是在呼应柏拉图《会饮》中所提出的“爱欲”这个跨学科也跨历史、跨文化的永恒问题。
进而言之,布鲁姆很少被关注,恐怕与知识界流行的思想趣味不无关系。至少与布鲁姆相比,人们缺乏对经典的真正热爱,也缺少亲炙伟大作品的渴望。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作品”,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即使并不对这些大书了然于心也至少可以略知一二,而且略知一二也就够了。更何况,那些“大作品”常常是些“过时”的旧书,没有时效性也不实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足矣,有什么必要一遍遍翻译、解释甚至还要通过那些老古董来反观现代思想的弊端?汉语知识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解释传统尚且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遑论细读西方经典乃至对西方经典的解释性作品!
责任编辑:廖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