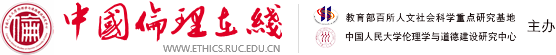孙伟平:伦理分歧及其本质
摘要: 科学与道德、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区分,是史蒂文森的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情感主义态度理论是从一个假定开始的,即科学以一致为标志,而道德以分歧为显著特征。在具体的道德生活中,人们的伦理争论往往起因于伦理分歧。阐明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关系,包括它们如何发生相互关系,是伦理分析的中心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任务。
作者简介:孙伟平(1966- ),男,湖南常德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上海 200444
关键词:情感主义/信念/态度/信念上的分歧/态度上的分歧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3&ZD007。
史蒂文森(Charles Lesie Stevenson,1908-1978)是美国著名的元伦理学家、情感主义伦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秉承摩尔开创的语言分析伦理学传统,改造和修正了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等人的极端情感主义理论,创立了一种“温和的”情感主义态度理论。情感主义态度理论是从一个假定开始的,即科学以一致为标志,而道德以分歧为显著特征。在具体的历史的道德生活中,人们的伦理争论、冲突往往起因于伦理分歧,关于“分歧”的研究便成为史蒂文森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史蒂文森创造性地提出的两种分歧——“信念上的分歧”和“态度上的分歧”——的理论,是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元伦理学领域富有特色的思想贡献。
一、信念与态度的区分
信念和态度的区分是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基石之一,也是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相区分的前提。史蒂文森指出,信念与态度的区分古已有之。按照那种古老的思想,信念作为众多内心印象的汇合,是一种特殊认识官能的产物,而态度不过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官能的驱力或能力。这一区分在历史上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自休谟以来的早期情感主义者更是以事实与价值(包括伦理学中的道德)的区分为名,将之推向了“二分对立”的极端。
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事实是存在于对象之中、与人的天性结构或价值无关、可以为理性所把握的对象及其性质。而道德并不是理性的对象,善恶并不是可以理证的。休谟从彻底经验论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德情感就像声音、颜色、热与冷这些知觉属性一样,并不依赖于观察对象的某些事实。善和恶不是对象所具有的性质,而是主体内心由于其天性结构而产生的“知觉”,即人们在观察一定行为或认识与思考一定对象时,在心中所产生的感觉与情感。人的行为的善恶等只受愉快或不愉快的情绪或情感的支配或指导,理性作为“情感的奴隶”,只是为情感服务的。面对善恶等道德问题,以理性为特征、以客观事实为对象的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科学所研究的关系与道德关系不同,前者的连系词是“是”或“不是”等,而后者的连系词是“应该”或“不应该”等。根据逻辑规则,道德关系既然不在科学所研究的诸种关系之内,它就不可能从那些关系中被推导出来。理性、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在《人性论》中,休谟认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509~510休谟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
后来,休谟的这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并不成熟的思想,被一些哲学家,特别是极端情感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尽管情感主义者对上述区分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如“科学”、“事实”、“认知”、“信念”与“价值”、“道德”、“评价”、“兴趣”、“感情”、“情感”、“态度”等等,但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甚至割裂它们之间的联系,将之严格地二分对立起来,却是极端情感主义者的一贯立场。他们认为,科学是关于事实的,价值是关于目的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可以进行逻辑分析,价值则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科学可以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价值则无法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等等。
史蒂文森虽然不完全赞成这种二分对立的极端立场,但也接受了二者之间的基本区分,并用自己独创的一对概念——“信念”与“态度”——具体地表示它们。而且,史蒂文森还将“详细地阐明信念与态度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视为伦理分析的“中心问题”,甚至“真正的问题”[2]11。史蒂文森也承认,关于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是十分复杂的,很难说清楚。但是,运用某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即“(至少部分地)联系行动的意向来分析”[2]7,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可是,史蒂文森并没有给出这两个基本术语的定义。揣摩他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我们大致可以把握它们的含义:信念主要是指诸如科学、历史、传记等方面的事实或认知“倾向”;而态度则类似于培里的“兴趣”,其主要特征在于纯粹认知中所缺乏的“赞成”和“反对”或者“喜爱”和“厌恶”等倾向。例如,科学诚然建立在“地球绕日公转”之类事实的基础之上,但科学并不因此“赞成”或“反对”什么,“喜爱”或“厌恶”什么,哪怕是对于它所描述的对象。
当然,作为一位温和的情感主义者,对于极端情感主义者绝对地割裂信念与态度的“二分对立”观念,史蒂文森并不赞成,并冷静地观察到信念与态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方面,信念是指导或纠正态度的必要准备。几乎所有的信念都与道德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在规范伦理学中,人们在描述一定事实的时候,总是会考虑它将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对它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不想愚昧无知地评价一个对象,就必须通过这个对象活生生的实际前后关系仔细地观察它。”[2]12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获得的信念常常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对某一事物的信念的分歧,或者信念发生变化,往往会引起态度的变化。例如,当人们以为麻雀总是偷食粮食时,可能会憎恶它,将它称为“害鸟”;但是,当人们通过周密的观察和食性分析,发现育雏期间的麻雀主要吃的是庄稼上的虫子时,对麻雀可能就不那么憎恶了,从而态度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对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人们的各种具体的态度,往往也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例如,人们的态度对哪些信念可能进入视野,受到关注,具有一定的影响。“正如很多人都指出过的,我们的态度经常影响我们的信念,不仅是因为态度使我们沉迷于希望的思考之中,而且因为态度会导致我们发展或抑制某些信念,这些信念可以向我们揭示出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2]5例如,偏爱某一事物会促使我们对之深入了解,形成正确、丰富、多样化的相关信念;厌恶某一事物可能导致我们回避它,对之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形成错觉、误解与偏见。“情人眼里出西施”可谓典型案例。对于信念与态度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史蒂文森在考察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的关系时,还会进一步展开阐述。
史蒂文森强调,态度和信念之间这种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不仅是“密切的”,而且也是“相互的”,虽然在“相互的”影响中,有时一方会占据优势。简单地追问是一般的信念影响一般的态度,抑或相反,这就如同追问“是流行作家影响公众趣味,还是公众趣味影响流行作家”,只会令人误入歧途。因此,必须摒弃那种认为信念和态度只能互相排斥的观点,从而立足信念和态度的相互联系进行思考,考察信念和态度各自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二、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
在史蒂文森看来,下述问题虽然看起来是表面性的,实际上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伦理一致和分歧的性质是什么?它与自然科学中出现的一致和分歧的性质相同吗?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仅仅是一种题材上的差异呢,还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差异呢?”[2]2史蒂文森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把道德问题与科学问题区分开来,找出其间的实质性差异,从而对道德术语、问题有清晰的、普遍性的认识,使道德语言和方法的研究找到适当的方向。只要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对规范伦理学问题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认识,使常常显得混乱的规范伦理学问题变得清晰,从而既易于论证,也易于反驳。
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等极端情感主义者一直试图将伦理学“科学化”,努力按照科学的范式和标准(如可证实性原则和意义标准)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根据极端情感主义者艾耶尔等人的见解,伦理判断不过是人们的情绪、情感等的宣泄和表达,我们从未真正地为价值问题而争论;我们关于一切问题的争论,“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发现所争论的并不是真正关于价值问题,而是关于事实问题”[3]126;在一个伦理争论中,如果不能指出对手犯了某个事实错误,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说服他的念头。而且,“当我们处理有别于事实问题的纯粹价值问题时”[3]127,理性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只能凭借对个人的“攻击和谩骂”来进行。
与艾耶尔等人不同,史蒂文森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能把伦理分歧统统诉诸个人的情感差异,虽然情感差异是伦理分歧中最重要的方面。他对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分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不同的伦理分歧具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性,有些伦理分歧是情感方面的,而另一些则主要不是情感方面的。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种分歧的理论,并把这两种分歧视为伦理分歧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可以称为“信念上的分歧”(disagreement in belief)。即在某种情形下,“一个人相信p是答案,另一个人则相信非p或者某种与p不相容的命题才是答案;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方都为自己的观点提出某种方式的论证,或者根据进一步的信息修正其观点”[2]2。例如,两个朋友在回首往事时,对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地点的记忆上的分歧,甲认为是p,乙认为是非p或者是与p完全不同的q,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并尽力提出一些证据佐证自己的观点,或者根据较新的发现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道德问题与信念存在密切的关系,任何道德评价都必须通过对对象的实际的前后关系加以仔细考察才能作出,甚至任何在复杂的信念中划分出哪些与道德有关、哪些与道德无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几乎任何信念都潜在地与道德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而在另一些情形下,还有一种与信念上的分歧截然不同的分歧,即“态度上的分歧”(disagreement in attitude)。史蒂文森认为,态度上的分歧“包含着一种对立面,有时是暂时的、缓和的,有时是强烈的,它们不属于信念,而是属于态度——这就是说,属于一种相对立的目的、抱负、要求、偏爱、欲望等等”[2]3。例如,两个人决定共进晚餐,一个人建议到有音乐伴奏的饭店去,另一个人却表示他不喜欢听音乐,建议去另一个饭店;当他们中至少有一方试图改变对方的态度时,就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存在态度上的分歧。再如,当两个人在处理一笔捐款时,一个人希望将钱用来建医院,让更多的穷人看得起病,另一个人希望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分歧即为态度上的分歧。态度上的分歧的特征是对某事、某物、某行为,一方赞成,另一方不赞成,并且双方互不相让,争论不休,试图影响、改变对方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伦理分歧,即关于态度的信念(belief about attitude)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不同人的相反态度,而仅仅与他们的关于某种态度的信念对立有关。例如,关于某一议案,张先生坚称,大多数人都赞成它,而李先生则坚持说,大多数人都反对它。张先生和李先生之间明显地存在分歧,并且这种分歧与态度——大多数人赞成还是反对该议案——有关。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却不是态度上的分歧,而是关于态度的信念上的分歧,即大多数人对该议案究竟是持赞成态度,还是反对态度。这种态度在这里仅仅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是可以通过调查、统计把握的事实。因此,“关于态度的信念上的分歧只不过是信念上的分歧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关于感冒的信念上的分歧一样,其区别仅仅在于题材的不同”[2]4。
在史蒂文森看来,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分歧:前者是信念上的对立,涉及怎样如实地描述和解释事物的问题,对立双方不可能同真;后者是态度上的对立,涉及赞成或不赞成,以及怎样通过人的努力促成或阻止某事的问题,对立双方不可能都满意。信念是思考、假定、预测的结果,既包括对事件、行为的信念,也包括对态度的信念(如“我认为他在某事上持某种态度”等)。它是科学争论的中心,从信念上的分歧到信念上的一致也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而态度则是指“任何心理学赞成或反对的倾向”,其含义与培里的“兴趣”是等同的,包括意图、愿望、渴求、偏爱、欲望等多种复杂的感情,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活动领域。“态度是一种以某种方式行动和体验某种感情的倾向,它本身不是一个单纯的行动或感情。”[2]90例如,假若某个人在道德上不赞成某种行为,那么,当他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行为时,他就会感到愤怒、屈辱、震惊;当他发现自己也有这种行为时,他就会产生羞耻感,甚至罪恶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态度上的分歧虽然与信念上的分歧迥然不同,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蒂文森认为,如何详细地阐明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这是伦理分析的中心问题,是伦理学的“真正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任务。尽管在现实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并体现为社会习俗的道德规范,总是比有争议的道德规范多。但是,由于伦理争论或分歧的研究更容易凸显人们所运用的道德推理方法,加之史蒂文森企图把信念与态度的区分加以扩展,贯穿于整个伦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因此,史蒂文森主要着眼于伦理分歧展开自己的研究。
实际上,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伦理争论常常并非只包含某一种分歧,完全排斥另一种分歧,而往往是二者兼存的。史蒂文森坚持,两种分歧的联系是“事实性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分歧的存在说明不同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判断和信念,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要、情感和态度。仅就逻辑可能性而言,可以在没有态度上的分歧的情况下产生信念上的分歧。例如,科学家们可以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但对某一研究对象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同样,也可以在没有信念上的分歧的情况下产生态度上的分歧。例如,A和B两人都相信X有Q,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X持有不同态度:A赞成包含有Q的东西,而B反对这样的东西。然而,这仅仅是逻辑上的可能性。事实上,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往往支配着他们对该对象的态度。“信念是态度的向导”,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态度上的分歧都植根于信念上的分歧”[2]136。这是由事实与价值、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任何非理性的因素如兴趣、欲望、情绪、情感、态度等无不受着理性因素的制约。没有人们对对象和自身的事实性认识与把握,就不可能有人们对对象的伦理或价值评价,不可能产生对对象的情感和态度。反过来,人们对某一对象的态度,又必然反映甚至影响着他们对该对象的认识和信念。在现实的伦理争论中,总是既包含着信念上的分歧,又包含着态度上的分歧,那种仅仅包含某一种分歧的纯粹的伦理争论是不存在的。
三、伦理分歧的本质在于“态度上的分歧”
确定伦理分歧的性质是史蒂文森探讨分歧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他随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人们争论什么是善的时候,是态度上的分歧,还是信念上的分歧呢?而且,对于两种伦理分歧来说,究竟哪一种分歧更为根本呢?
史蒂文森正确地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企图把规范伦理学完全变成科学,习惯于按照科学方式处理伦理道德问题;态度虽然是引起伦理争论的因素之一,但在伦理分析中却一直受到严重的忽视。以往的伦理学理论大多认为伦理分歧是信念上的分歧,把伦理分歧的本质说成是信念上的分歧与对立。例如,自然主义者把伦理判断等同于某种类型的科学陈述,从而把规范伦理学当成了科学的一个分支。即使是像里查兹、休谟、培里等强调情绪、情感、兴趣的伦理学家,强调信念的分歧也并不少于强调其他分歧;虽然他们都涉及到了态度,但强调的实际上仅仅是关于态度的信念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涉及的实际上是心理事实或经验事实。例如里查兹的愿望(或欲望)之实现,或妨碍愿望(或欲望)之实现;培里的兴趣之满足;等等。史蒂文森在分析之后指出:“培里仅仅强调了关于态度的信念上的一致和分歧,忽视了态度上的一致和分歧,从而使得规范伦理学变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直接分支,并因此使得伦理学方法论具有一种虚假的必然性。”[2]268也就是说,培里涉及的仅仅只是信念上的分歧,而很少涉及真正的态度上的分歧,因而他仍然把伦理问题当作科学问题来对待,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处理,从而也就无法真正揭示伦理分歧的性质。
实际上,“当伦理问题引起争论时,它们涉及的是具有二元性的分歧”[2]11,即既包含信念因素,也包含态度因素。只有仔细地分辨这两种因素,既不强调前者而排斥后者,也不强调后者而排斥前者,才能揭示道德语言的各种功能,才能清楚地认识伦理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异同,从而完成伦理学的中心任务——通过详细阐明信念与态度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从而把握现实道德的全部内容。
诚然,信念上的分歧是引起伦理争论的因素之一。传统理论的失误并不在于强调了信念上的分歧,而在于忽视了态度上的分歧。恰恰正是态度上的分歧才是伦理争论的显著特征,是伦理问题区别于科学问题的根本标志。史蒂文森一再强调:把伦理问题同纯科学问题区分开来的主要是态度上的分歧。例如,一位金融家一直敦促其财产委托人支持任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慈善事业。其中一个委托人建议,应该为穷人提供医疗设施;另一个委托人则建议,应该向大学捐资。于是,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在现有条件下哪项事业更有价值的道德问题。他们的态度决定着争论如何进行,问题如何解决。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史蒂文森还举了一个例子:某公司的工会代表提出,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提高工人的工资;而资方则认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是不应该的。这一具有伦理色彩的分歧显然包含态度上的分歧。尽管争论双方对近期生活费用的上涨程度、公司的利润收益等问题具有不同认识,但态度上的分歧在争论中无疑居于支配地位。对态度上的分歧的强调与分析,也正是史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学的特点与突出贡献之所在。
史蒂文森进一步指出,态度上的分歧是激发伦理争论,并在争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因素。首先,态度上的分歧标志着伦理争论的产生。例如,当人们对某人是否说了谎这一事实发生争执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分歧;只有当人们针对他说谎对不对、应不应该发生争执时,才产生了伦理分歧。
其次,态度决定着哪些信念与争论相关。“只有那些与某一团体的态度有关的信念才会被提出。而其他信念不管其本身多么有趣,都与所讨论的伦理问题不相干。”[2]14当工会代表要求公司增加工资的时候,假若公司坚持说,50年前的工资水准比现在低得多,工会代表将会立刻回击说,这种论据即使是真的,也与争论毫无关系。因为50年前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工资水平没有可比性,对目前双方的态度都没有什么影响。由于信念和态度处于因果关系中,信念的改变常常引起态度的改变,所以只有那些可能导致某一方态度转变,从而可以调和态度对立的信念才能被恰当地引入争论,产生影响。例如,对近期生活费用上涨、公司财政状况增加等事实的看法,则有可能使劳资双方一致达成提高工资的态度,从而可能成为争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态度一致是伦理分歧得到解决或者争论结束的标志。当态度上的分歧解决之后,即使确实还存在一些信念上的分歧,伦理争论通常也就结束了。比如在前述事例中,如果两个委托人都赞成向大学捐资,那么,尽管他们在教育的社会效果等信念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他们的伦理争论与冲突也就结束了;假如公司欣然同意工人的要求,那么,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有信念上的分歧,如双方对生活费用上涨幅度等看法不一,工会仍会同意结束这场争论。反过来,对于伦理争论中所涉及的事实问题,即使双方的看法一致,但双方的态度依然可以相互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会觉得他们之间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这时若想问题得到解决,双方必须或援引其他事实,或凭借热情的言词打动对方,以寻求态度上的一致,或服从某一权威(如法院)的裁决,否则,必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僵局之中。
总之,“态度上的一致和分歧是伦理学的本质特征,即使在伦理判断相对孤立且并不会导致任何公开的讨论时,它们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2]17。例如,如果一个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夸赞自己的优点,告诉人们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总是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常常就会怀疑他的动机,怀疑他是否正在掩盖某种不可告人的隐情。因为,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没有什么过错,没有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他就不会处心积虑地寻求人们的赞许,就不至于不得不直接使用伦理判断引导我们对他持赞成态度,对他表示尊敬。或许,他是觉得人们的态度与他自己的态度有分歧,因而才运用这种不甚高明的方法,试图影响、改变人们的态度,努力令人们的伦理评价与他自己相一致。
四、关于两种分歧理论的质疑
信念与态度的区分极为复杂,又具有全局性。笔者曾在《事实与价值》一书中对事实(信念)与价值(态度)的区分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之间的“二分法”难以成立①。如果事实(信念)与价值(态度)的区分值得质疑,那么,建立在这一区分之上的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另一基石——态度上的分歧和信念上的分歧的区分,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摇晃起来了。
首先,有些伦理学家声称,这种“二分法”与实际并不相符。在日常道德生活中,具体的伦理争论、分歧有时是极其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几乎是一种常态,就如同很难区分其中的信念因素和态度因素一样,也难以区分其中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有时,即使可以区分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也很难弄清它们在一定的道德情形中是如何分别发挥作用的,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其次,有些伦理学家进一步指出,不能说态度上的分歧是伦理争论的特征,因为在科学活动中,许多争论都不仅涉及到信念,而且涉及到态度上的分歧。例如,托马斯认为,信念上的一致或者说对实际问题的一致看法,也要依靠态度上的一致,至少争论双方首先必须接受逻辑一致性原则。接受这一原则也就意味着具有一种一致的“认识的态度”,因为这一原则不是根据逻辑推导出来的,如同史蒂文森在道德证明中所表明的一样,任何支持这种“认识态度”的理由与“态度”本身的关系,是心理的关系,而不是逻辑的关系[4]。
科学活动是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活动,其中难以避免活动主体的目的、利益、欲望、需要、情绪、情感、意志等的影响。既然科学活动中也存在态度因素的影响,那么,不仅在伦理学中,而且在科学活动中,都可能存在因为态度上的分歧而引起的争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说态度上的分歧是伦理争论的独特的“特征”。史蒂文森诚然已经看到,许多伦理争论不能仅仅依据信念加以解决;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在科学活动中情况同样如此。例如,在科学中的不同学派(学术共同体)、不同理论体系等之间,有时面对同样的事实、信念,具体的理解、解释都不尽相同,因而就不能仅仅依据事实、信念解决分歧。
当然,史蒂文森作为一位温和的情感主义者,也曾经指出这样的事实:“有一些评价性问题的争议集中在组织知识的过程上。理论家们对知识的兴趣可能会相互冲突,导致他们在什么是值得谈论的、什么特性是重要的、什么样的分类图式是合适的等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涉及到何种组织有助于达到既定目的的这些问题,并不总是伪装的事实问题,因为对于这个目的可能存在着分歧。它们可以是真正的评价问题,要求使用那些我们在伦理学中已经检验过的方法。”[2]286但毕竟,囿于情感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他不可能彻底地改弦易辙,在科学与道德、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相统一的视野内思考和解决问题。
再次,按照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语言的意义主要在于表达人们的情绪、情感和态度。但众所周知,人们的情绪、情感和态度是主体性的,具有主观性,从根本上说不是理性可控的。有些学者指出,史蒂文森认为不存在理性的伦理判断,不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伦理争论、分歧不可能仅仅通过科学的、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即具有一种“理性的不可解决性”(Rational Irresolvablitiy)。我们确实不难发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对于解决伦理争论、分歧,缺乏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严格的证明程序和明确的检验标准,更没有所谓“判决性试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屡见不鲜。
有些学者声称,如果伦理分歧、冲突是理性无法解决的,那么就可能产生道德混乱,甚至酿成严重的“国际灾难”[5]43~49。这实际上是指责史蒂文森的态度理论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可能将道德问题导向混乱与无序。史蒂文森则回应说,“道德混乱”在本质上源于一种“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无法通过假设发现某些客观真理,或者确认某些终极原则等来缓解。相反,只有对伦理冲突的性质、复杂性以及解决它们的可能方法的清晰分析,才可能缓解这种“恐惧”。
此外,如果我们通读史蒂文森的论著,观察史蒂文森的观点陈述和论证,不难发现一个与上述的非理性特征相反的倾向:史蒂文森属于“将哲学科学化”的语言分析哲学阵营,他一直都非常重视理性、逻辑,他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一直是试图证明“态度何以是理性可控的”。这说明,他的哲学观(伦理观)、伦理学方法与具体结论之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五、两种分歧理论的重要意义
无论如何,关于信念和态度、信念上的分歧和态度上的分歧的区分,以及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探讨,是史蒂文森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基石,在态度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史蒂文森曾经明确地说:“我的方法论结论的核心是我关于一致和分歧的观点,而非我关于意义的观点。”[6]731尽管关于信念和态度、信念上的分歧和态度上的分歧的区分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批判,但回顾史蒂文森关于伦理分歧和一致的学说,确实可以发现不少独到的重要的见解,并且确实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史氏风格”。
第一,史蒂文森尽管接受了自休谟以来情感主义者区分事实与价值,进而区分理性与情感、科学与道德的基本立场,并用独特的“信念”与“态度”具体地表示它们,而且比较突出地强调了情感、态度的作用,但不同意将它们绝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过激观点。他从常识出发,不否认信念(知识)、理性、科学方法在道德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认为,“我们能从科学中获得的力量,远比起道德哲学家习惯假设的要大”[6]733。这与极端情感主义者大相径庭,而且也更加合乎实际。他关于科学与道德,信念与态度关系的观点,特别是他比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克服了极端情感主义完全割裂科学与道德,否认道德领域中理性因素的片面性,也使态度理论表现出明显的调和色彩与温和倾向,从而引人注目地完成了伦理学从以理性为依据、以信念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向以情感为依据、以态度为中心的新模式的转变。
第二,史蒂文森坚持信念与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信念是态度的基础和“向导”,信念常常影响着态度;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也影响着信念,包括对信念的认知,以及在处理具体道德问题时的知识选择。这与极端情感主义者将信念与态度截然割裂、二分对立起来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史蒂文森对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分歧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独创性地提出了两种分歧——“信念上的分歧”和“态度上的分歧”——的理论。史蒂文森洞见到了态度上的分歧与信念上的分歧之间的联系,认为两种分歧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现实生活中,伦理争论常常并非只包含某一种分歧,完全排斥另一种分歧,而往往是二者兼存的。这对情感主义伦理学是极具特色的具体贡献。
第四,史蒂文森深刻地指出,伦理分歧的本质在于“态度上的分歧”。长期以来,人们企图把规范伦理学完全变成科学,习惯于按照科学方式处理伦理道德问题;态度分歧虽然是引起伦理争论的因素之一,但在伦理分析中却受到严重的忽视。信念上的分歧诚然是引起伦理争论的因素之一,但态度上的分歧才是伦理争论的显著特征,解决态度上的分歧才是解决伦理争论的关键。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道德现象,有效解决伦理分歧和冲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总之,立足道德生活的实际,首肯信念与态度、信念上的分歧与态度上的分歧之间的联系,首肯科学、理性、逻辑方法在解决伦理分歧中的作用,这是史蒂文森与极端情感主义者的重大区别,也是“温和的”情感主义态度理论的重要特点。也正因为史蒂文森的态度理论更加“全面”,更加“温和”,更加符合实际,因而改变了不少人对情感主义的印象,缓和了一些论敌的攻击,并使情感主义获得了公认的长足发展。
注释:
①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原文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C L Stevenson.Ethics and Language[M].City of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
[3]A.J.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Vincent Tomas.Ethical Disagreements and The Emotive Theory of Values[J].Mind,1951,60(238).
[5]B Blanshard.The New Subjectivism in Ethics[M]//J Sterba(ed.).Ethics:The Big Questions(2nd edition).Hoboken:Wiley-Blackwell,2009.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