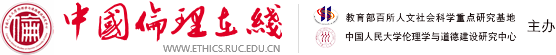晏辉: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的道德人格 | 系列之三
摘要: 没有危机事件便没有危机管理中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 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 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道德人格魅力便是行动者于特定场域下在瞬间迸发出来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晏辉
编者按
这是上海师范大学晏辉教授疫情伦理学三论的最后一篇。前两篇分别是《晏辉:面对疫情,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系列之一》、《晏辉:防控疫情,伦理学言说的三种范式及其困境 | 系列之二》。在论述了面对疫情伦理学的言说方式、言说对象之后,这篇文章提出“后疫情时代”及“后疫情时代”的道德人格两个概念,用以说明在疫情结束之后,应当进行何种道德反思,树立何种道德人格。文章主体部分首发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三期,标题为: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如需引用原文,烦请查校期刊原文。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诸种伦理道德问题,实质上是道德人格问题,公共危机既彰显着道德人格的魅力,也促成着健全道德人格的养成和形成。
成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不仅仅是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行动者自身成为一个自我旁观者,即或以心中的“道德律”,或以想象中的他者道德为自己恪尽职守、履行责任的道德力量;或在场的旁观者给予行动以公正的道德承认和赞誉;或不在场的旁观者借助相关信息给予行动以公正的道德评价;还指站在理论理性的高度对公共危机中的道德人格问题给予赋有时空结构、充满复杂性和冲突性意识的整体研究。因为,人类的好生活固然充满热情和激情,但拥有并充分运用理性知识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行动的正当性和沉思的科学性,才是最根本的。用反思、批判和建构三种致思范式分析和论证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人类实现目的之善、过整体性的好生活乃是必要的理论任务。
一、“后疫情时代”的概念和特征
这里的“时代”是一个比附性的用法,指的是疫情结束后的社会时空结构,以及需要修改、矫正和完善的社会场域。作为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社会场域,必须具备两种条件,或必须具备两种状态,以为实现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之善奠定基础。其一,人类必须凭借其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创造出用以满足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的价值系统,借以获得快乐和幸福;其二,必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建构起有利于实现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秩序体系。秩序是规则体系,是行动方式,是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组合方式。我们把这两个条件组合在一切的时空结构称之为“社会场域”。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之下,尽管也存在着破坏甚至解构价值体系和秩序系统的因素,如没有效率的治理和管理,人为制造的暴力事件,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等,但都不致于导致社会体系崩溃,因为这些事件都未能突破社会安全阈限,尽管道德宽容已将诸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纳入严厉谴责和批判的范围。而重大公共危机,尤其是被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确定为一定级别响应的致命病毒疫情,则是那种能够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秩序系统崩溃的公共危机。在人类所经历过的致命病毒的发生、暴发、传染、防控过程看,致命病毒虽经历程度不同的“打击”,但终被人类“战胜”,迄今为止,人类依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精英”。人类凭借其有限理性认知、分析、论证、描述病毒的原始发生及其演变、变异、传播、传染的内在逻辑,并研制了相对有效的药物控制疫情,尽管还只是相对地认知和防控,但毕竟积累了相关的理论知识,深化和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人类在应对各种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合作,体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道德人格魅力,但这种魅力毕竟不是创造好生活过程中应有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而是在应对无价值甚至是反价值的公共危机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得已”式的伦理精神。因为公共危机一定不是人类所意愿、所希望的事情,而是人类避之不及的“灾难”。事实证明,除去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之外,人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之下。在三种和谐状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下,通过手段之善实现目的之善才是人类的价值理想和实践目的。
“后疫情时代”描述的就是重大灾难和疫情过后,人们该如何思考、怎样生产和交往、如何过好平静、平凡甚至平淡生活的过程;如何通过修改、矫正甚至改变原有的观念、政策、制度,以创制更能体现手段之善、实现目的之善的社会结构的过程。“后疫情时代”不仅仅指疫情过后的社会时空结构,更是指这个时空结构中的人们如何反思、批判和建构的过程,借以建立起值得汲取的集体道德记忆。
二、“后疫情时代”的道德人格
康德在论述“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时给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即“能动性”“感受性”和“接受性”。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理性通过知性的自我构造原则,构造出了不依赖于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的“先验逻辑”,即先天的“原理”;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原理整理、改造借助感性直观即时空得来的感性材料,从而得出科学知识和知识的对象来。但人的理性认识创设的“原理”又是被动的,它需要得到激发、激活,没有外在的感性材料的刺激,没有感性经验的激发,没有原理对这些材料和经验的“感受”和“接受”,“原理”也无用武之地,知识也不可能产生。此所谓知性无感性则空,感性无知性则罔。
依照这个原理,道德人格类似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先天“原理”,它潜存于人的心灵深处,是等待展现、迸发的潜在力量。若没有外在事件、没有外在环境,道德人格便不可能实现其自身。没有危机事件便没有危机管理中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没有疫情肆虐,便没有全民“抗疫”,也就没有抗击疫情中道德人格魅力的集中迸发。然而,我们绝不能为着彰显人类的道德人格魅力而故意制造引发和激发这种魅力的危机事件,因为危机事件是反价值的非意愿事实。 借助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我们就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魅力的内在关系问题,可作这样两点深入分析和论证。其一,道德人格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心理和行动力量,可有不同的内涵和展现方式,而决定内涵和方式的“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就是外在的客观环境,即“场域”。稳定的、日常的场域与动荡、危机、灾难情形之下的场域一定不同,不同场域下道德人格的内涵和展现方式也就有别。其二,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道德人格魅力便是行动者于特定场域下在瞬间迸发出来的道德范型和伦理精神。
对此,我们既要充满理性和情感地、以公正的旁观者的视角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给予称颂和赞美;但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观之,却不能将这种范型和精神视为人类德性的正常或永恒状态,如果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主观地、情绪式地将这种范型和精神确立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的或核心性的伦理范型,就必然跌进道德空想主义、道德形式主义的陷阱。
三、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
如何直接面向“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关系本身,如何沉思隐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事实,乃是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的认识论前提。道德人格作为一个人能够正确思考和正当行动的主体性力量,并不独立存在,它与人的其他能力如知性和判断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的认识除了需要理性(实践理性)之外,还需要知性和判断力。德性的教化、命题的传播、训诫的灌输、榜样的宣传,对生产、交往和生活无疑是重要的,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也同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只构成道德范型存在状态中的应然部分,而实然和已然则是另外两种形式。人们从事生产、交往和生活,从事治理和管理所能应用的德性和规范则是人们实际拥有且可以反复运用的德性。所以真实的道德世界才是我们用以分析和论证危机事件以及日常生活状态下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系统如何可能的基础。
基于对“公共危机和道德人格”之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的正确认识,回归真实的道德世界可有三种进路:
其一,在对公共危机的认知、预防、管理和消除过程中,人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是不同的,并非只有“向善”一种类型,还有“向恶”的表现以及道德冷漠的呈现。真实的道德世界必须含括这三种情形,如若只是称赞那些勇于担当、忘我工作甚至自我牺牲的行为,而置那些投机钻营、发国难财、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道德冷漠、毫无同情、置若罔闻的行为于不顾,不制裁、不惩戒、不批判、不谴责,而是一味地树“楷模”、立“榜样”,进行单一的宣传、教育,这对那些默默无闻地奋战、奉献、牺牲的人们是严重地不公平,对营造一个真实的道德环境也有消极作用。不要用诱人的道德光鲜绑架那些“道德榜样”、“人民楷模”,使他们困在那个曾经的道德高地上,只有永远守住这个道德上的“战略高地”,才是榜样、楷模,否则便是无德甚至是缺德之人。而那些给他们“榜样”和“楷模”称呼的人,并把这些称呼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人,或许也是道德的践行者、公正的旁观者,但绝对不排除某些利用公共权力的支配权和权威媒体的话语权制造舆论、进行道德宣传的人,那些既无德性又无德行的人是没有资格进行道德宣传的。道德假象、虚假繁荣的制造者通常都是形式与质料的分离者:德性与规范的分离、言说与行动的分离、行动受益者与行动责任者的分离、德性与幸福的分离。他们总是向他者提出最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践行的却是最低要求,甚至是无要求。人们必须理性地、公正地看待“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中的道德乱象,辨别出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假象,哪些是幻相。
其二,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意识要求我们对造成“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诸种根源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如果说“抗击疫情彰显道德人格魅力”体现的是“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的价值逻辑,那么造成这一关系的事实逻辑是什么呢?就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始发生看,不排除不断出现的致命病毒乃自然之安排。在人类所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星球中,任何一种无生命物质和有生命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存在理由,没有哪一种存在者可以任性地说,只有我才有优先存在的理由,为使我的存在亮出耀眼的光辉,我可以任意看待和对待其他的存在者。自然有着属于其自身的自组织能力,它是一个自行调节以保持生态平衡的系统。或许可以悲观地说,不断暴发的致命病毒就是自然保持其自身平衡的手段。然而,似乎人类从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所有类属是同等重要的,他自称是灵长类动物中的“优秀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像自然进化论一样,根深蒂固。然而,事实证明,人的认知能力和理性能力都是有限的,可很多人不顾及这种有限性,理性无限论和市场万能论支配着他们任性地、任意地看待和对待身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虽不能完全证实和证明,致命病毒与人们的不正确、不正当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联,但作为致命病毒之源初携带者的自然宿主并不直接“参与”人类的生活,它们有属于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领地”,而人类却依仗自己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开疆扩土,不断侵占原本属于其他物种的“领地”。依照现有的致命病毒发生史看,疫情的暴发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人的活动。
其三,关于在处理“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之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实质性的激励、奖励和正义“补偿”制度,既重要又迫切。这可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精神的奖励;二是物质的奖励;三是正义意义上的分配性制度安排,如对公共危机的防控和解除有重要贡献,其付出已长期且远远超出其所得,可通过制度性的分配安排给予矫正。
四、“后疫情时代”的谨防、反思与重建
如果从大伦理观角度分析,在“后疫情时代”,人们需要进行整体性的道德反思,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体道德记忆”,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公共危机的防控、处置和解除中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经验为基础,以实现从公共危机向正常生产、交往和生活状态转向为契机,矫正、修正、完善原有的制度和体制,完善“前疫情时代”的道德规范、提升“前疫情时代”的德性结构。
首先,谨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复归”。在稳定的、常态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似乎已成为阻碍实现效率、平等、正义等社会核心价值的顽疾。虽然早已突破道德宽容的底线,但在社会安全阈限内,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并未从根本上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构和社会秩序系统崩溃,而在防控、应对和解除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的社会危害倍增,因为它掩盖了疫情、瞒报了实情、延误了战机、错失了良机,甚至置自己必尽的公共职责于不顾。对此,尽管权威媒体予以严厉批判,民众予以严厉谴责,暂时性地受到遏制,但如果不痛下决心,从制度、体制,甚至法律设计上予以实质性的根除,那么回复到“后疫情时代”,便又会“回归”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之中。诸如,在“后疫情时代”不从根本上反思在公共危机中预测、认知、判断、应对、防控、解除等等各个环节出现的道德乱象,而是沉浸在打赢战役之后的“非理性”的总结、宣传、教化中;如果危机过后没有危机感,反而大张旗鼓地营造“成就感”、“喜悦感”,那么在未来的道路上,同样的错误还会继续,同样的危机依旧潜伏。如果说,新冠病毒乃是一种“自然瘟疫”,那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则是一种“社会瘟疫”,如果得不到根治,极有可能毁掉社会主义改革积累起来的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精神体系。
其次,反思现有的科技体制、知识生产机制、科技转换机制。每一次的致命病毒的发生、暴发、传播、传染都充分证明了人类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现有的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无法从容地应对公共危机。功利主义的政策导向,使得科学研究、临床实验变成了谋得奖励、奖项、荣誉、收益的手段。如果不是出于科学研究和知识应用本身,即康德所说的,如果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合乎责任甚至反乎责任,其所遵守的就是假言命令,只有出于科学精神和人类福祉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才是定言命令。
其三,完善或重建新型科技创新体制和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显得极为迫切。这属于科技伦理和管理伦理范畴。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着人类对身外自然和自身自然的深度“开发”,各种科技伦理问题急速凸显出来。正在进行的疫情狙击战业已充分证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之间的深层危机逐渐显露出来。致命病毒也可能类型多样,我们如何在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创制出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使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定在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所规定的范围内。如何治理环境、保护动物、珍惜生命;如何使付出生命代价的公共危机不再重演,都成为了“后疫情时代”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解决的道德难题。另一方面,在应对和防控新冠病毒的过程中,许多环节和层次都暴露出管理上的“瑕疵”,疫情的预判、诊断、应对、控制,都显得“匆忙”,或许公共危机的预警、研判、控制、解除,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公共管理的常态。
公共危机与道德人格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关系,如上所论,乃是现代性场域下的共同问题和难题,它超越了地区和国界,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只有打破地域性知识的边界,去掉狭隘的地方和国家眼界,充分借鉴和运用人类共同的理智德性(理论理性)和道德德性(实践智慧)才能应对和解决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价值诉求,而分明成为了康德道德哲学视阈下道德行动的绝对命令。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