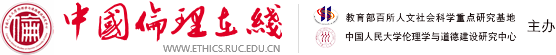论尼古拉·哈特曼价值论伦理学的典范意义
摘要: 价值伦理学, 因此价值问题必须是伦理学的又一基本问题, 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不是从舍勒开始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
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西方伦理学研究所所长,
《伦理学术》丛刊主编
文丨邓安庆
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对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我们一般知道他都是因为他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先驱之一的陈康先生的博士生导师,他对我国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国内学界对其著作的翻译非常有限,研究也完全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他依然是十分陌生的。因此,在我们开始研究其“价值伦理学”之前,稍嫌饶舌地介绍其哲学创新之路,应该是有必要的。
01 哲学创新之路

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
尼古拉·哈特曼1882年2月19日出生在里加(Riga),这座城市1282年加入自由城市“汉萨同盟”,期间经历被占领与短暂独立,最终于1991年成为独立的拉脱维亚的首都,是波罗的海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康德三大批判的首发地。尼古拉·哈特曼自小在此成长并读小学,中学时离开进入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人文中学(1897)学习,毕业后,1902-1903年先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Dorpat)大学学习医学,1903-1905年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语文学(Philologie),1905年才正式转入德国马堡(Marburg)大学学习哲学。马堡是尼古拉哈特曼的精神诞生之地,也是他的幸运之地,在此他成为新康德主义首领科亨(Hermann Cohen)和纳托普(Paul Natorp)的学生,从而定型了他未来哲学面貌的第一标签:新康德主义马堡派。1909年他以论文《柏拉图之前希腊哲学中的存在问题》(Das Seinsproblem in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vor Plato)取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出版专著《柏拉图的存在逻辑》(Platos Logik des Seins),同年出版《论普罗克洛的数学之哲学的初始根据》(Des Proklus Diadochus philosoph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Mathematik),获大学教师资格。1912年发表《生物学的哲学基本问题》(Philosophische Grundfragen der Biologi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兵役,当口译员、通信检查员和情报官。哈特曼真正进入大学当教师还是在战后,1919年他回到马堡大学取得了一个私人讲师职位,1920年成为“编外教授”,1921年出版标志其哲学独立地位的著作《知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同年,接替纳托普的教授席位,成为马堡哲学的重要支柱。
在此期间,马丁·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大力帮助下也在马堡大学谋得副教授职位,与哈特曼同事三年(1922-1925)。这是20世纪前期致力于重新确立Ontologie(存在论)基础地位的两位巨擘之间的相遇,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之间分歧于新存在论构想,并无思想交流。1925年,尼古拉·哈特曼调入科隆大学,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成为同事。与舍勒的思想相遇相当重要,哈特曼接受了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之构想,他们都想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学体系。哈特曼入职科隆大学的第二年就出版了《伦理学》(1926年)。在这本书中,他一方面认同康德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界定,探究“我应该做什么”,但同时认为,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却是,对价值要具有先天的明鉴能力,因此价值问题必须是伦理学的又一基本问题。他认同舍勒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对康德“形式主义”的克服,但不认同把“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建立在“心性”(Gemüt)对“价值偏爱”的“感受”上,而主张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因为“价值”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事物“自在存在的”“善”被主观所“明见”,所以要认同柏拉图意义上的先天的绝对价值直观,将此作为现象学伦理学的主题。他不认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是舍勒的独创,而是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已经建立在“质料价值”分析之上。所以,尼古拉·哈特曼的伦理学不仅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统合起来,而且把尼采、胡塞尔和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都融通起来,成为20世纪道德哲学的一大高峰。

刊登本文的《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5期封面
02 伦理学必须建立在价值学基础之上
之前的哲学史教科书都教导我们,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是从本体论(古典)到认识论(近代)再到价值论的发展。而在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伦理学,即古代是基于本体论的伦理学,近代是基于认识论的伦理学,而现代则是基于价值论的伦理学。但尼古拉·哈特曼却不是在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伦理学与价值论,而是对本体论与认识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关系做了全新的处理。
首先,他颠倒了新康德主义关于认识论与存在论(本体论)的关系。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讲席教授,哈特曼却是以与马堡学派分道扬镳的成果而登上马堡学派之高峰的,这也许只有在德国才有可能。马堡学派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认识论,正如陈康先生所言:“万事万物(Sein)消灭于思想里,认识论侵吞了Ontology。但哈特曼是新Ontology的创始人。万事万物不从思想解放出来,则根本无Ontology可言。因此哈特曼哲学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他的破万事万物依心的理论了。”于是他恢复了存在论为第一哲学,在此基础上探究对自在存在的认识理论。
其次,他的存在分层理论凸显出了“应该存在”的价值性。“价值”既不是单纯主观性的知识和评价,也不是纯粹的“自在存在”或“如是”(Sosein),而是存在之中的“应该存在”。对于“应该存在”,他又进一步区分为“观念的应该存在”和“实在的应该存在”,“价值”属于“观念的应该存在”,它是存在本身的本质性(Wesenheit),从而既不是事物满足于人的有用性,也不单纯属于人的主观评价。它属于事物的本质,是事物自身的“好”之呈现,但又不是实在地已经呈现出来的性质,而是就其概念或本质而言的观念性应该存在,这是对于“价值”之作为“内在价值”或“绝对价值”的最好的阐明。通过这种阐明,就可破解休谟提出的从“事实”(事物是什么)推导不出“价值”的所谓自然主义谬误。事物的事实(本质之是:Sosein,如是)和“价值”通过存在的分层给剥离了出来。这应该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存在论中对“应该存在”的揭示,就为伦理学奠定了价值论的基础。哈特曼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界定是从康德出发的。他认为康德界定的“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应该期望什么”是近代思维传统必须面对的三个实际(aktuell)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我应该做什么”。他高度认同康德的这一界定,认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境遇中都会不断地从而“日新”地给我们提出来,是我们不可逃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它甚至迫使我们做出决断,采取行动,并为后果承担责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也就表现在,我们生活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一旦实施就是现实性的了,甚至是历史性的了。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做了的事没法收回,没法再使之未实施;而行动的过失,也将是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更严重的是,行动是个人自己意愿做出的,但任何个人行动都会波及他人,影响他人,它会作为一个个环节被编织到世事发生的相互关系之网中,“它的效果总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它的存在方式是蔓延性的。一旦被卷入实存中,它就生生不息,永不消逝”。就此而言,“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揭示出来了。
但问题是,伦理学究竟该如何回答“应该什么”呢?伦理学作为哲学不可能具体地回答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特殊的境遇中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回答一般应该发生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性质,就像在存在本身的结构中必须包括可能存在什么、应该存在什么和必然存在什么一样。那么应该发生的东西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呢?或者说,“应该”得以被认知的标准是什么呢?

青年时代的尼古拉·哈特曼
首先“应该”发生的东西就时间性而言是尚未发生但有内在要求、愿望和需要发生的,因而是指向“未来的”。它不是规定、描述与定义实际上的应当“什么”,而是现实中缺乏却实际上被需要、被愿望它立即发生,“存在”因而才完满的东西。这种“未来”却“应该到来”的性质,又赋予它一种“实践的品格”,即一个应该发生的东西是要通过我们的“实践”或“行动”才通向“未来”之“到来”的,因此,这需要把“应该存在”作为“价值”化为实践规范的基础,才能使得“行动”以未来之“到来”的“意向性”实现“应该存在”,即将其作为“观念性的存在”转化为“实在的存在”。于是,这又使得“应该发生的东西”具有了第三个性质:人作为“造化者”(Demiurg)“参与”到“物之造化”,即儒家哲学常讲的“成己成物”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核心是“造化”问题,通过“实践”(行动)让“应该存在”的存在起来,这“实践”对人而言,是主体的行为,其使命或天职,是让应该存在者存在,这才是“行动”之善性、道德性;此“道德性”之“根据”,是主体行动由于“参与”到了物之成就自身的造化,让应该存在者存在了。因而“实践”对“存在”而言,是“应该存在”之实存化,即“道行之而成”的“道行”,此“道行”就是人的造化行动的道德性根据。作为“应该存在者”是“观念性存在”,是“价值”,作为行动的道德性根据,已经落实为“规范”了。因此,不能仅仅把伦理学视为规范性学科,尤其不能仅仅盯着习俗化和制度化了的那些规条,而且要审核这些规范或规条背后的根据,即价值,这也就使得伦理学同时或更为本源地是一门价值学。
于是,哈特曼对康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作出了深化和衍生,提出了他独创性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出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要把握什么,重视什么,才使自己成为属于自己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尚且缺乏的感觉与感官是什么,使得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自身中培育、磨砺并教育之?’”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就是价值论问题。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作为一个人应该的生活;而为了知道什么是应该的生活,必须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上,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在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和世界上我们就要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要通过参与有价值的(应该存在)的塑造,而自我造就属于自己的本真的自我和本真的人生。这就是伦理学必须返归本真自我的天命问题。伦理学的实践和行为区别于工艺性的制作之处,就在于它始终是“反身而诚”的,回到本真之我、本性之我,回到自在的存在之根,让物物之,让人人之,从而参与到宇宙万物的“生生”之道中。这才是人应该“率性之为道”的天命。为了完成这一天命,我们尚且缺乏的是什么呢?是价值感或对本真价值的感受。因此,伦理学在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唤醒我们沉睡着的价值感,培育和磨砺我们的价值感受。而且,哈特曼强调,价值感问题虽然说是伦理学的第二问题,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它是居于第一个基本问题之上的问题,因为它才是“应该做什么”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之所以说价值问题是“应该做什么”问题的前提,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价值意识”,那么对于“应该”什么是不可能明白其真正含义的,反过来讲,“应该什么”其实不是实际上有什么,而是一种“价值意识”。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价值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应该什么”。这两个问题本来是一个问题,但只有我们的价值意识“觉醒了”,“应该什么”才是清楚的。同时,如果“应该”问题只是局限于“做”/“行动”的正当性,常常是十分清楚但又是十分狭隘的。虽然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临思考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总是清楚的,诸如早晨起来先洗脸,再吃饭,再去工作之类,诸如工作中该做什么是正当的之类,也都是清晰的,不存在问题。因此哲学上的“应该做什么”恰恰不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但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地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刻,一定是面临着大是大非、善恶不明或“两可”却又必须“择一”之时。这就涉及了价值问题,而且不是特殊的价值问题,而是普遍的价值问题。艾希曼作为纳粹军官,他的职务就是负责把纳粹从欧洲各地抓来的“犹太人”迅速地通过火车运送到各地的集中营,那么作为一个“纳粹军官”而言,他“应该做的”就是服从他军人的职务要求于他的,他后来被审判时依然还在拿这一点为自己无罪辩护。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庸人”,阿伦特说他身上散发着“平庸之恶”,就是哈特曼所说的“价值盲”或“价值白内障”:分明长着一双并没瞎的眼睛,但却看不见价值,对价值有着职业上的漠视,价值感沉睡或死寂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除了知道什么是我们职业上的“应该”,还根本上“作为一个人”,对于职业上要求我们做的有一种反思性的是非意识,这是从我们“作为一个人”出发,对每个人自己的要求。只知道职业上的要求,而不明我们首先作为“一个人”有对自己“人性上”的天然要求,这样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不明是非,不分善恶。我们作为一个军官、作为一个犹太人或反犹主义者,有我们自己主观的立场、价值或职业上需要顺从的命令,这很正常,但是,无论是自己主观的立场、价值还是职业上的命令,我们还有一个普遍的身份,即我是一个人,一个抽象的人,一个不是军官、不是犹太人、不是纳粹分子的身份,这一身份让我们从出身、血缘、民族、职业、党派这些平时让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能“命令”我们“应该如何”的处境中抽离出来,仅仅作为一个人要求自己必须思考:这是我该做的吗?这才是伦理学需要询问的“应该做什么”。这时的“应该什么”是人类的一个普遍问题,无关你的出身、职业、民族与党派,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应该”。与这个“人”相对的,不是任何“他人”,而只是禽兽与神祇。你是在为“人类”思考一个普遍的“应该”,这个“应该做”的什么,决定了你不会让你因你做的事而沦为禽兽,当然你无论怎么做,也决不会让你成为超越的神,他让你成为一个最最普通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就是伦理学以之为基础的价值问题。
所以,哈特曼强调,在回答“应该做什么”的时候,首先要“本己地”唤醒“价值感”(Wertsinn),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做人”首要的不是考虑如何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兄为人弟的问题,而是如何“是一个人”(Menschsein)的问题。虽然我们生而为人了,但那还只是一个自然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人,还需要人的自我塑造。没有普通的伦理,即关于普通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就不会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进行人的自我塑造,自然人成为人的可能性依然是可质疑的。有些人辜负了上天造化之恩、父母培育之德,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而是成为禽兽不如的东西,根本原因在于人之为人的最低底线价值的扭曲和颠倒。因此,哈特曼赋予了一个人唤醒自己价值感、价值意识这一使命,实际上是一种最低的、底线的使命意识,而不是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善的意识,这种关于人之为人的底线的价值意识令人直觉地履行人的自我塑造、自我造就而使自己完成成为一个人的使命。完成这一自我塑造的使命,才是人之为人的生命之意义。因为人通过这种自我塑造,参与到世界生生不息的造化之中。人没能履行他在伦理上的造化之天职,创世(Weltschöpfung)也就不会完成。履行这一天职,才是我们自己不是“让人”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人宣示成年,意味着他真正成为一个人。但唯有伦理的价值意识,伦理的觉悟才能宣告他成年。所以,伦理学是人心中首要的、切身的哲学兴趣,是哲学思想的起源和最内在的动机。伦理学的目标就是通过价值引领人朝向他的在世天职(Weltberuf)而自我造化,使之成为造物主的同仁(Mitbilderschöpfer)、世界的共同创造(Mitschöpfer)。伦理学因此而让人类超越其在宇宙中的渺小、短暂与无能的生命状态,从而实现其作为高等生命的形而上的伟大与卓越。

尼古拉·哈特曼的《伦理学》(Ethik)
德文第四版(Walter de Gruyter, 1962)书影
03 伦理价值学的内容结构
哈特曼在其《伦理学》中系统阐述了其价值学的伦理体系。该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925年9月,哈特曼在第一版前言中明确注明是在马堡,因此,不可想象哈特曼的价值伦理学是在他调到科隆大学成为舍勒的同事之后才在舍勒影响下写出的作品。当然,不可否认,舍勒的伦理学著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一版前言”写于1916年9月,比他两人成为同事整整提早了6年,确实对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伦理学》在哈特曼生前一共出了3版,分别是在1925、1935和1939年。在其去世之后的1962年出了第4版。这是一部八百多页的巨著,让作者能够非常详尽地阐述其价值伦理学的完整体系。
这一体系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题是“伦理现象的结构”,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sitten);第二部分主题是“伦理的价值王国”,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价值学”(Axiologie der Sitten);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意志自由问题”,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
“伦理现象学”分为7卷25章。卷I:思辨的和规范的伦理学;卷II:道德的多样性和伦理的统一性;卷III:哲学伦理学之迷途;卷IV:康德伦理学;卷V:伦理价值的本质;卷VI:论应该的本质;卷VII:形而上学的展望。
“伦理价值学”讨论了伦理价值的内容及其构成的“价值王国”之结构,由8卷38章构成(从第26章到第64章)。卷I:价值表的一般视点;卷II:最普遍的价值对立;卷III:内容上有条件的基本价值;卷IV:伦理的基本价值;卷V: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一组);卷VI: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二组);VII: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三组);VIII:论价值表的合规律性。“
“伦理形而上学”讨论意志自由问题,由6卷20章构成(从65章到85章)。卷I:批判性的预审;卷II:因果的二律背反;卷III:应该的二律背反;卷IV:伦理现象的证明力;卷V:个人自由的存在论可能性;卷VI:自由论之附录。
我们现在再来稍微详细一点讨论上述“价值论”的体系的具体内容。

尼古拉·哈特曼画像
“伦理现象学”是以“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来观察和审视我们生存经验、境遇和历史中的“伦理现象”。“伦理现象”是何种“现象”,哈特曼自己似乎并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其整个哲学来看,似乎应该这样来描述:“现象”是“自在的存在”在特定的历史契机和境遇中“呈现”出来的趋向,但它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或“样式”出现在人类意识中,取决于人类的“价值之眼”,把其“可能性”呈现为“现实性”,把其“观念性存在”变成“实在性存在”。当然“看见”存在之中的“价值”,仅仅是“现象”的第一步,是将“应该存在”以明确的“价值意识”呈现出来;随之,“应该存在”的“价值”要落实为“规范”来激发和规定“意志行动”;然后,伦理的行动与道德的行动将应该存在的价值变成现实予以现实,完成存在的价值充实,存在之意义的完满实现。因此,“伦理现象”是“存在意义”之呈现过程中“天地神人”“共同创造”的奇观,把天性中的“应该”呈现为“价值”,是“思辨伦理学”的主题,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以完成天、地、人之造化,共同参与有价值的创世秩序之形成,是“规范伦理学”的主题。哈特曼因此说:“伦理学的纲领包含在这两者所提出的问题中。这两者并不把它们的任务区分为两个独立的一半。因此,它们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关系。它们是不可分的,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折面(Kehrseite)。我应该做什么,我只当我’看见’在生活中一般地什么是富于价值的时,才能估量。而’看见’富于价值的东西,我只能在我把这种看(Sehen)本身视为富于价值的、视为任务、视为内在的应当做(Tunsollen)时才能感觉得到。”这种伦理学理念与当今英美分析伦理学热衷于把伦理学区分为各个独立的碎片来研究完全不同,强调思辨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在思想、方法和内容上的统一。它表现在,伦理学无论是思辨的还是规范的,无论是美德论的、义务论的还是功利论的,它们作为伦理学都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去“看见”“应该存在的”、富于价值的东西并实现这个富于价值的东西。在这里,哈特曼虽然用了“估量”(ermessen)这个词,但他明显地反对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因为“估量”或“重估”,也有可能仅仅是“主观地看”,而不是“看出”事物本身的客观价值。富于价值的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不取决于我们主观的“重估”,而在于存在本身的“最好可能性”,这个“应该存在”的东西被“看”呈现出来。但鉴于“应该”作为可能性存在、却尚未现存存在,伦理学关照的是存在之“未来”,由于“思辨”的本义theoria即是“观看”:从事物本身“看”事物,即以家观家,以社会观社会,以国家观国家,以天下观天下,这种“看”是一种现象学的“看”,它不是对象性地置身事外的主观性的“看”,而是“看见”事物之“天性”的自我呈现。因此,研究伦理学,就得学会现象学之“观看”,通过这种观看,才真正能“看见”什么是富于价值的(wertvoll)。就此而言,伦理现象学首先的部分就是基于价值“观看”的“思辨伦理学”。
从经验层面而言,价值作为我们独立的个人生命意义的表现,在于让自己的生活富于意义,在此意义上,价值与意义是同义词。那么进而言之,富于意义的生活,有价值的人生也就将自己生命之中最好的可能性实现出来,活出最好的自我,以此参与世界的造化,让世界富于价值,也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这种“看见”“发现”价值的眼光,不是发现事物之于我们的有用性,万事万物像我们一样,有其自身的自在存在,它不为我们存在,我们也不为它们存在,我们各自存在,各自安好,展示各自天性之美善,才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而,我们注目于事物自身之价值的观看,无非就是要“看出”其各种可能性中“最好的可能性”,这种“最好”是系于事物本身,而不是系于我们的。它之所以“对于我们”也是有价值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多元关系的,每一事物也是由其多种因素的复杂关系(如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构成的,只有万物各美其美,我们才有一个“美好世界”。所有伦理学都基于唤醒这种价值之眼的价值洞察。这绝不意味着“价值”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人们“评价”的东西,相反,“价值”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中的“应该存在”在生活中被照亮,被激发,人们的“看”本身是发现、是洞察、是洞见,凭着这种发现、洞察和洞见,富于价值的东西构成了意志的“意向性”,要将其从“应然”变成“实然”,变成生活中“实在的存在”,即变成富于价值的美好生活。所以,伦理学本质上是为未来世界而“闪光”,至于它究竟能否照亮未来,取决于其所“看见的”价值是否落实为制度性规范。落实到了制度性规范,价值才参与到“实在存在”的造化进程。因此,规范伦理学的核心不是描述现实世界的规范,而是“建构”现实世界的规范,“为世界立法”。立法的核心就是实现伦理价值从“应然”(观念性的存在)到“实然”的转变。
如果说思辨伦理学重在发现、认识和论证什么是“富于价值的东西”,那么规范伦理学则着重于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使得我们的各项制度性规范具有正当性、伦理性与道德性。正当性体现为法律政治层面的规范,伦理性体现为相互关系中的规范,道德性体现为个人自律立法的规范。
因此,伦理的认识就是对各种规范、戒律的价值性的认识,其问题体现在,如何在杂多的道德中发现其伦理(道义)的统一性。规范、戒律确实异常丰富,哪怕就是道德性规范,也无限多样,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同的政治都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学如果不能发现与洞察到伦理的同一性,就不能洞察到先天的绝对的伦理法则的道义意义,于是只能陷入相互对待的道德规范的冲突中作出自己的排位或选择。但是,由于每一种道德规范,都是因为其各自的文化、宗教、政治、民族的现实处境下的价值“显像”,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的不足和有限性,因此,伦理学必须有一个为超越于各种特殊处境的规范之价值而辩护的本原性道义原则,这就需要在存在论中发现一个绝对先天的价值域,来为一切现世的规范奠基。哈特曼价值绝对先天领域的设立,为化解“应该的二律背反”这个现代自由世界才出现的“诸神之争”提供了可能,是一种比几乎所有的通过商谈对话来寻求伦理共识的理论更为有效地化解价值冲突的哲学方法。
先天价值领域确立在人生、宇宙的创造性造化这一点,对于我们熟悉《周易》“生生之大德”的民族而言,无疑也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哈特曼进入了其“伦理价值王国”,这是具体地处理“价值内容”的“伦理价值学”。他试图以“价值表”来处理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和伦理价值王国的结构秩序。“价值”本来是由经济学引入思想中来的,在其进入价值哲学的当初,就有意地在哲学上把伦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区别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探究的是事物实在的有用性价值以满足于人类的需要,因而与“物质”的商品属性相关,而哲学的价值虽然哈特曼也像舍勒一样,强调价值的“质料性”、内容,因而与“物质性”有关,但哈特曼更强调的是“价值”属于事物的“自在存在”,但不自在存在本身不是“实在的价值”,价值作为“观念性的自在存在”,是其应然的“好”,这种“好”作为“应该存在”只有通过人格才实现出来。所以,他说“伦理价值的质料早已以财富价值的质料为前提”(S.252),“生活价值只是精神价值之实在的存在论上的前提”(S.253),但是,“以有用价值为定向的做法也就证明自身是最最糟糕的;因为正是这类价值不是固有价值,其本质恰恰仅在于能够成为固有价值的手段价值”(S.255)。这就从根本上拒斥了哲学上的伦理价值以任何经济性的有用价值为基础的可能性。而哈特曼也反对舍勒把质料性的伦理价值奠基于更高级价值之上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旧形而上学目的论构想的偏见。因为所有层级的本真的固有价值都有自己独特的自主性,不会因为对更高价值的依赖而减损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坚定地维护“价值”属于“观念性的自在存在着”的“本质性”,对目的论伦理学、康德伦理学、各种经验主义伦理、后果主义的伦理学等在伦理价值上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判。
当然,对价值的把握更重要的还是对各种价值之关系的意识,如果我们不能对所有价值之间的等级秩序有个明晰的意识,那么,当我们面临应该怎么做才是正当的问题时,依然会手足无措。“布鲁丹的驴”就因为在两堆同样距离的同样的稻草之间无法作出选择而活活饿死,成为千古笑料。我们选择和决定该做什么时,往往不是在善恶之间做选择遇到了困难,而恰恰是在同样有价值、同样有必要做而又不可兼做时要作出选择,这时唯有一种可能,就是能区分出价值的高低秩序,才有选择的依据。所以,价值论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也就在于对于价值等级秩序的确定。在这里,哈特曼批评了人们通常所犯的错误,就是从最普遍的价值中认识最高价值,从最个体性、具体性的价值中认识最低价值。这一批评把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一网打尽。同时也批评假定一种唯一的价值梯度序列和以价值强度作为价值高度的两种错误倾向。那么究竟该如何确定价值等级秩序的价值偏好之标准呢?他几乎否认了以舍勒为榜样,因为舍勒以高级价值为低级价值奠基的思路遭到了他的摧毁,能够作为榜样的,他认为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所带来的重大启发意义是,这种价值高度区分所追求的不是大线条,而是更细微的差异,是狭义上的伦理价值范围内的划分。这正是人格自身的品质,由此人格的价值高度得以区别开来”(S.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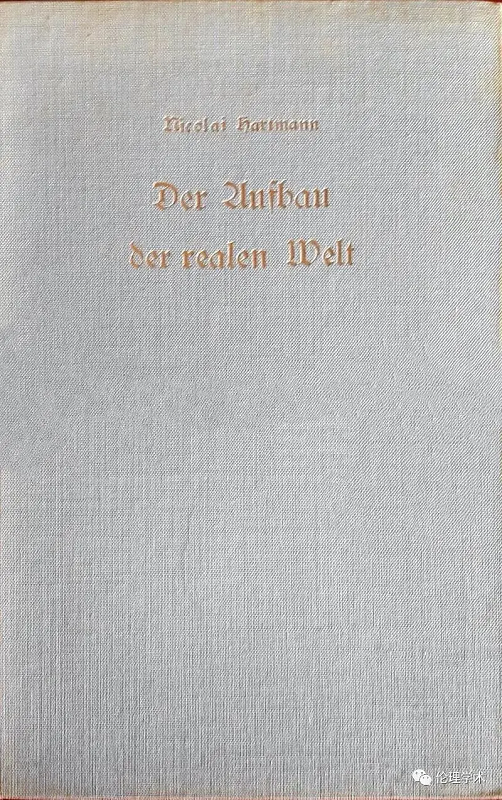
尼古拉·哈特曼的《实在世界的结构:一般范畴论纲要》
(Der Aufbau der realen Welt: Grundriß der allgemeinen Kategorienlehre)德文版( Anton Hain, 1949)书影
在弄清楚了前两个基础问题后,哈特曼就从第二部分的第三卷开始来具体讨论伦理价值的内容及其价值等级秩序问题。在第III卷“内容上有条件的基本价值”中,他区分了“附着于主体的基本价值”:生命的价值、意识的价值、主动的价值、被动的价值、力量的价值、意志自由的价值、预见的价值和目的活动的价值;和“善物的价值”:达在(Dasein)一般的基本价值、处境的价值、权力的价值、幸运的价值和特殊的善物秩序。
在第IV卷“伦理的基本价值”中,哈特曼首先讨论了伦理价值与自由的关系,确认一切伦理价值无不基于自由而成立;接下来讨论了善、高贵、充实和纯洁。他强调了之前一直强调的一点,对于伦理的价值内容而言,“充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作为最高价值的思辨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作为最高价值的理念一直是抽象的东西,对价值感来说一直是未充实的,因此也无法让人没有获得价值洞见,有陷入彻底的价值无序混乱的可能。纯洁,这个只有在基督教伦理学上得到肯定的价值,在哈特曼这里作为伦理基本价值再次获得了肯定,他认为纯洁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
在第V卷“特殊的伦理价值”之“第一组”中,哈特曼讨论的是“德性”价值。他一直认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不是从舍勒开始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质料性价值的探讨了(第一版序言)。他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具有对最为丰富的德目的讨论,当然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价值”这个现代才有的术语,但相当于“价值”的概念,就是善、恶、美、丑、是、非等。哈特曼所使用的“特殊的伦理价值”(die spezielere sittliche Werten)是相对于上两卷“伦理的基本价值”(die sittliche Grundwerte)而言的,特指“德性价值”(Tugendwerten)。“德性”既指性格品质特征,也指行为特征。当然,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性格品质特征也不是指天生具有的好品质,好品质也是习惯养成的,需要在长期的行为中锻炼、磨砺而塑造。哈特曼也一样,强调德性价值是行为的价值:“德性价值都是人的行为本身(Verhalten selbst)的价值;而且由于行为本身延伸到事态(Sachverhalts)的不同类型,那么,对于质料上差异化的‘种种德性’也就必然地存在丰富的杂多性”(S.416-417)。所以,德性价值的一种完整的价值表也就足以构成“伦理善的王国”(das Reich des sittlich Guten)。但就其具体探讨的“第一组”特殊伦理价值而言,涉及的是:正义、智慧、勇敢和克制(Beherrschung)。这属于古希腊的“四主德”,他还加了一章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几个主要德性。
在第VI卷“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二组”,哈特曼讨论的是“邻人之爱”(博爱)、真诚与正直(Wahrhfigkeit und Aufrichtigkeit)、诚信(Zuverlässigkeit)与忠诚(Treue)、信任(Vertrauen)与信仰(Glaube)、谦虚(Bescheidenheit)、恭顺(Demut)和保持距离。这一组德性明显地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德目之外了,尤其是“保持距离”作为一种德性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另外,他还讨论了“外部交往的价值”。 在第VII卷“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三组”,哈特曼讨论的是“最遥远的爱”(Fernstenliebe)、惠赠之德(Schenkende Tugend)、人格性(Persönlichkeit)、人格之爱(Persönliche Liebe)。
在第VIII卷“论价值表的合规律性”中,哈特曼继续探讨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概观的局限(Grenzen der überschau)、“价值等级秩序的结果”、“价值表合规律性的类型”;价值对立的五种类型;对立关系和价值综合;价值充实;个人之间的价值综合;价值的高度和强度;价值王国的开端与终点;等等。
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介绍到这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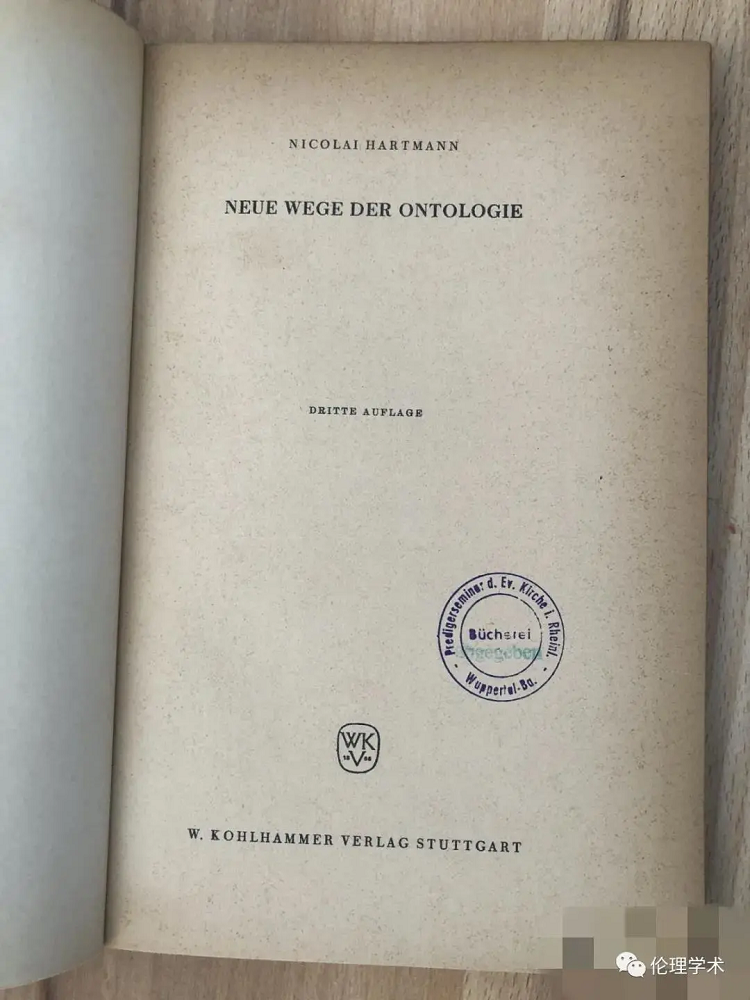
尼古拉·哈特曼的《存在论的新道路》
(Neue Wege der Ontologie)德文版(Kohlhammer, 1949)书影
04 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典型意义
在20世纪道德哲学发展史上,有五本书最为经典,第一本是英国摩尔1900年的《伦理学原理》,开创了“元伦理学”的先河,直接表达了道德直觉主义的观念;第二本是德国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表达了一种超越康德“形式主义”先验哲学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的理念;第三本是尼古拉·哈特曼的《伦理学》,以一种来源于柏拉图的“存在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实践哲学而又从现象学的价值哲学对之进行改造了的“新存在论”对“伦理现象”进行价值学奠基的原创性著作,对价值伦理学的理念、方法和原则、特别是价值内容了系统论证;第四本是汉斯·约纳斯的《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尝试》,开辟了技术文明时代“责任伦理”以及随后世界流行的“应用伦理学”新范式;第五本是众所周知的罗尔斯的《正义论》,迄今为止依然占据实践哲学研讨的主流中心。
在这五本著作中,摩尔的“直觉主义”、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和罗尔斯的“正义伦理”都作为伦理学的典范形式获得了普遍认同,只有“价值论伦理学”作为独立的类型尚未得到承认,这是不公允的。当然,在价值论伦理学中,情况比较特殊,虽然现象学的伦理学从布伦塔诺开始对“道德意识”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建立在价值意识的基础上,迈农在建立“对象理论”之后也以其《一般价值论》开启了“格拉茨价值哲学学派”,该学派的特点就是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论的基础上。胡塞尔在20世纪前20年也留下了大量的伦理学讲稿和著作,将伦理学建立在由现象学奠基的价值哲学之上,但真正让“价值论伦理学”进入一般哲学的视野并获得了一种特色标志的,依然还是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概念,而尼古拉·哈特曼的价值论伦理学在国内却一直没有被发现与研究,其实在价值论伦理学的脉络中,准确地说应该是这样的:哈特曼接过了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概念,但同时他又系统地超越了舍勒。作出如此定位的不是别人,而是,20世纪著名哲学家汉斯伽达默尔。他在一篇名为《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中,探讨了当代哲学伦理学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的可能性,就是能创造性地综合古代典范亚里士多德和现代典范康德。古代的典范之所以需要超越,就是因为其古典性,它的伦理理念和论证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伦理出路。现代是个自由伦理时代,伦理道德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个人自由基础上,而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任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是城邦伦理,城邦伦理的原则是正义,而不是个人自由。在城邦正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人性自身的德性卓越,这才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特征,因而被称之为德性伦理学。德性伦理学采取的是目的论的论证框架,即善之为善的标准,不从外部而从事物自身因其自身之故的“好”来说明,这种“好”当然就只能是“自身品质”所能蕴含的最终目的(目标)作为最高善。但这种目的论框架被现代人几乎普遍地抛弃了。现代伦理学面临的任务不是德性之完善,而是一个自由了的现代人为什么还需要履行具有绝对命令性的道德,因而是道德本身所蕴含的必然性和自由的二律背反成了最亟须解决的课题。康德伦理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伦理学的典范,原因就在于他最为系统而经典地解决了道德的“绝对命令性”如何是基于个人的自由立法的,这就是必然和自由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康德的解决方法,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论证框架,而是“形式主义”的立法原理。正是这一形式主义立法原理使康德从一开始就既遭到费希特、黑格尔等后继者的内部批判,也遭到形形色色的各种哲学的外部批判。但正如麦金泰尔所言,尽管如此,不管人们如何批判,康德依然还是康德,我们关于伦理学所能说的,依然就是康德所能告诉我们的那么多。

尼古拉·哈特曼
不过,在所有这些批判者当中,唯一一个得到了肯定的人物,即被视为真正克服了康德形式主义立法原理的人,是舍勒。因为他以现象学的方法论证了有一种“质料的先天性”,先天性保证伦理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但这种普遍有效性又不是靠康德的形式主义立法来保证的,而是靠价值的“质料内容”来保证的。因此,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被视为一种新的、超越了康德之根本弊端的伦理学形态。伽达默尔先是充分肯定了舍勒的功劳:“价值伦理学是有意识地与康德的形式主义作对提出来的。如果说价值伦理学在舍勒那里也是完全没有分寸和不公道地错误认定了康德关于义务的形式主义伦理理性特征的话,但它毕竟具有不可争辩的正面的功劳:它使伦理性的实体内容以及不仅仅是应该和意欲的冲突形式变成了道德哲学分析的对象。”(Gadamer, S.181)
但是,伽达默尔也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舍勒改造康德的“失败”:但“这样一种由舍勒正确认识到了的理论必然失败了,因为每种道德都是一种具体的价值形态”。所以“这同一种先天的价值研究的方法要求是相矛盾的。没有什么人的道德体系——即有限的、历史性的有效道德体系——能够一般地满足这种方法的要求。……所以,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尽管区别于康德的形式主义,包含了伦理性的实体内容,但它依然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出路。价值意识的直接性和道德的哲学相互分裂”(Gadamer, S.177)。
但在尼古拉·哈特曼这里,我认为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伽达默尔所说的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和康德道德形式主义的有机结合,尽管这一结论在伽达默尔那里依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只承认这么多:“「尽管舍勒的」这种伦理学明显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尼古拉·哈特曼,这位舍勒伦理学思想的系统改建者,就不会明确地放弃让一种道德的意义伴随价值哲学。价值哲学对于伦理的价值意识有一种助产术的功能,就是说,当它发现有些价值被遗忘或者被误导的时候,它能一再地推动展现出它们的丰富的伦理价值意识。”(Gadamer, S.176)关键是,伽达默尔所批评舍勒的“质料的先天领域”在哈特曼这里通过对“处境”下的丰富价值内容的直接直观被取代了,使得他能够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所要求的那样,不是靠一种先验确立的“先天的东西”来“应用”于经验性处境以取得行为的道德性价值,而是始终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直接的多样化实践行为中“洞见”出德性价值的内容,作为“观念上的应该存在”,从而参与到存在的实体性(正确的逻各斯)造化(生存)进程中,以实现其“价值”。这种价值完全不需要靠“先天形式”来保障其普遍有效性,而是服从于事物本身向善的造化原理。这样既超越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也避免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通常的误解:以为它仅仅是一个普遍正确的逻各斯在一个个经验性处境下的具体运用。所以,一个既克服了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各自论证中被诟病之缺陷又保留了其各自优势,以一个直接的价值内涵之现象学直观所引导的、以主体生命和存在本身的自我造化参与世界的意义生存的这种伦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将古代和现代两个典范推向了一个更高综合的新的典范。

尼古拉·哈特曼的代表作四卷本《存在论》(Ontologie)
德文版(Walter de Gruyter, 1938-1965)书影
对于哈特曼价值伦理学对舍勒的超越并作为一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运动》的作者是如此评价的:“哈特曼的伦理学比舍勒的伦理学有着广泛得多的百科全书式的观念。这种伦理学力图囊括整个历史中的价值,即不仅有古代的基督教的价值,而且有哈特曼在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中认出的那些价值。同舍勒提出的总括一切的先验要求相比,他也表现出一种带有尝试性的和灵活性的精神。”
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的价值论伦理学能够将古今两种最为经典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康德的道义论——进行一种真正的创造性转型,从而使得一种基于价值论的伦理学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也不同于康德的道义论,当然更异于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它确实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形态,而这一价值论伦理学的形态应该也必将得到学界的承认。
文章发表在《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5期。为便于阅读,我们删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引用或进一步阅读,烦请查校期刊原文。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