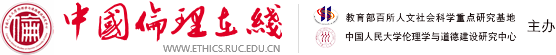电车难题、堕胎实验,我们能从这些思想实验中获得什么?
摘要: 在所有思想实验中, 正如医生们在检视Thomson的思想实验后发现的许多不足之处一样, 比如在经典的电车难题中读者只有两个选择
编者按
中国伦理在线“听哲里”栏目开播了。栏目将以语音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把伦理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口语形式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适合本栏目的素材或者音频稿件。本期是“听哲里”栏目的第一期,以下将和大家共同分享以著名的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和“堕胎实验”为主题的思维探险,请打开录音和主播颜晗一起开启思维的旅程吧!
关注伦理问题,解读伦理经典,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伦理在线语音播客,我是主播颜晗。
我们能否从想象的事件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关于这一点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显而易见的是,分析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们持肯定的态度。至少在他们看来,即便我们选择道德原则的环境是一个假想的环境,这条道德原则依旧是可以推而广之的。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今天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这种讨论,而是先向各位介绍几个思想实验,再把我的观点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引起各位的思考。
在所有思想实验中,“电车难题”大概是最著名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了,它探讨了牺牲小部分的人来拯救电车上更多人性命的可容许性。最经典的电车难题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拉杆?这个思想实验所发展出的变种是如此之多,这些变种涉及了到各种重要的道德元素,各位不妨在确定自己的观点之后再思索一下,如果由你来设计,你会设计什么样的变种?
如果说电车难题因其所可以笼罩的领域甚众且迫切度太高和某些特定情境不符,我们不妨直接由特定情境进入思想实验流程,设计出一个满足情境的实验,就像Judith Jarvis Thomson在1971年提出的,用于维护堕胎权利的思想实验:某天早上,你从睡梦中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背部被插入了一根管道,你惊恐地扭过头,发现管子的另一端连着一位你曾在电视节目中见过的著名的小提琴家。此时爱乐协会的成员出现在你身边向你致歉,原来这位小提琴家患有严重的肾病,需要一位与他配型的健康人与他联通循环系统,借助健康人的肾脏帮助他过滤血液中的毒素,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可以与小提琴家配型成功的,于是爱乐协会的成员绑架了你,在你睡梦中将他的循环系统接入了你的身体。医院的院长告诉你:“很抱歉得知爱乐协会对你的所作所为,假如我们事先知道的话是绝不会允许这类事情发生的,但是事已至此,由于现在你的肾脏承担了他的基本需要,如果你们之间的联系被强行切断,他就会死。不过只需要九个月的时间他就会完全康复,届时就能将你们两个安全分离。”Thomson希望通过这个实验维护堕胎权利,说明即便性命攸关也不能在未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别人的身体,但在医生们接触到这个案例之后普遍感到这是荒谬的,对这些临床医生来说,这个案例在生理学与操作规范上都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必要的细节,比如为什么爱乐协会可以找到一个配型的人?这个手术的执行者是谁?在哪里?除此之外,医生们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优解,比如采用透析或者移植,而这些更优解似乎被Thomson刻意忽略掉了,于是,优秀的医生,不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医生,甚至都没办法发现这是一个怀孕的隐喻,更不用说去发现其中关于堕胎权利的伦理辩护了。
思想实验可以引申的范围越宽广,它对于我们的伦理考量的影响就越大,而这个范围的真正决定性因素是其内含的约束条件,这个约束越大,对某些假设的论证就越贴合,范围越小,对日常生活就有更好的适用性,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只是大体如此。因而有些哲学家认为,控制良好的思想实验可以作出广泛的引申。哲学家James Rachels在1975年构思了两个案例,有关一个人想要杀死他的表弟获取遗产,他利用这两个平行的案例来说明杀人与任由他人死去并没有区别。第一个案例中,Smith在浴缸里淹死了他的表弟,然后伪造成了一场意外,而在第二个案例中,John想要在浴缸里淹死自己的表弟然后伪装成一场意外,结果正当他准备行动时,他的表弟不小心滑倒了,头撞在了浴缸的边缘,倒在了浴缸里淹死了。Rachels表示,杀死表弟与任由表弟死去在道德上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假如两个原本是相同结局的案例中,杀人与任由他人死去并无区别,那这两个行为就没有内在的区别。这个结果看似可以推广到真实世界的道德抉择中来,并且对政策的选择和法律的判断有潜在的影响,但真的是这样吗?
正如医生们在检视Thomson的思想实验后发现的许多不足之处一样,Rachels的案例也可以发现许多反例,最直接的反例便是,一个在战场上想要刺杀敌军将领的狙击手,在扣动扳机前发现瞄准镜中的目标突然由于心脏病发倒在了地上,这个时候这名狙击手还能够被说成是成功刺杀了这一目标吗?但这些类似的反例、揭示和不同路径的提出往往被哲学家们冠上“不善于筛选出伦理要素”的名头,这种回应显然是哲学家们用来说服自己的说辞,它还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之中,我们如何判断那哪一部分在伦理上更为重要?并且为什么,比如在Thomson的案例中,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哲学家能比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更好地判断哪些部分更有伦理上的重要性吗?哲学家们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各篇文章与各类设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隐含的东西:思想实验的诠释应当服从于一个权威的伦理框架,换言之,这一类实验不能够包含其他的什么东西,仅仅可以包含作者的意图,这就像是Lewis Carroll 的语言游戏Humpty Dumpty的概念,这两个单词表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即思想实验的作者为了构造出一个满足自己理论目的的伦理框架而指定好了所有其中具有伦理重要性的元素。这也就是说,思想实验的设计者们有意无意地增加了一个全知者,读者们只可以通过全知者参与情境之中,并通过他来做出抉择,这个全知者给出一张短短的清单,参与者只能在寥寥数个选项里挑选自己更倾向的那个,而这些选择背后又被全知者在事先赋予了特定的心理状态与意图,比如在经典的电车难题中读者只有两个选择:拉下操纵杆,或者什么也不做。
当然,这并不是说思想实验不具有任何价值和作用,道德哲学家们的努力也绝不是一种空想,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思想实验的种种不足并不是使用者的不足,伦理学家们自身也在努力修正或者点明这些不足,以减少它们对我们理论的暗礁险滩式的损害。实际上富有想象力的伦理学家们所做的最多的便是不局限于短小明确的选项清单,他们往往有更加深远的视野,致力于探寻新颖的、可以更好地调节冲突的解决方法,他们在这种语境下拥有的知识越多,他们就越容易做出明智的选择。明智的选择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与社会环境相符合,我们使用思想实验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观察参与者痛苦的抉择,而是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解释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许这种使用方式类似于Daniel Dennett指出的“直觉泵”的概念,即思想实验是一种考虑到各种可能情况的想象来达成说服的工具,把思想实验看作是一类具有说服力的虚构作品并不会消除它们的外部效度,却允许我们对它进行推演。 负责任的思考需要可靠的理性工具,伦理思想实验也许不算是个非常可靠的工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如作家 Iris Murdoch 在1970年所论述的:“我们以一种可以被稳固思考的图景来表现人类的真实境况,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思考的方式。”前理论(Pre-theoretical)的伦理“常识”可以被偏见、权力和许多其它主观因素扭曲,而我们之所以转向道德哲学,正是因为不知如何在前理论层面解决这些模糊不清的伦理问题。伦理思考是困难的,而我们最好的工具也只能做到如此,谦逊仍应是我们的箴言。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