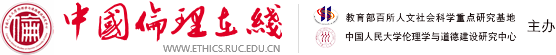刘科丨从“得”到“德”:功利主义导向“绿色”美德的可能性
摘要: 01 美德伦理对功利主义关于 幸福之, 02 功利主义成为一种美德理论 功利主义路径从幸福解释, 在美德伦理的系列批评中功利主义如何导向一种美德主义
从“得”到“德”: 功利主义导向“绿色”美德的可能性
摘要:在当代话语中讨论幸福将会涉及人的生活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道德问题,功利主义在幸福讨论中对此最具解释力。功利主义在对幸福内涵的理解、对幸福观念的构架以及在幸福要素的测量三个方面呈现出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优势,但同时也遭到了美德伦理学的批评。随着功利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推进,它逐渐呈现一种向美德伦理学靠拢的趋势。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中,功利主义加上美德的保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功利主义可以更加关注人的品质和美德的培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绿色美德”,由此后果和美德二者形成了一种开放、灵活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功利主义;美德;绿色;美好生活

作者简介:刘科,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伦理学会理事,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教研室访问学者,从事西方伦理学、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研究。
随着联合国绿色国际会议的召开,全球已经进入绿色时代。尤其是当美好生活把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纳入重要考量标准后,生态环境的有序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人寻求幸福生活的迫切维度。作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幸福在学界探讨通常分为两种进路,其一是功利主义的进路,其二是美德伦理学的进路。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做最好的事情,而避免或尽可能减少事态的恶化,这一原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遭遇了众多批评,但因为它符合人性的基本经验和在现实中的强大解释力,使得种种反对它的声音到最后都不能成功。从一个传统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说,如果要做到卓有成效,一种精明计算是有效的。但是当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一种大规模集体行动出现时,计算就带来诸如霍布斯的契约失灵,人们基于当下个体利益的计算,而放弃生态保护的道德动力。但是晚近以来,随着美德伦理在西方思想界的复兴,功利主义意识到计算行为的局限性,要取代计算行为可能需要非计算行为的增长,如培养个性和品德。随着功利主义的不断自我更新,尤其是从行为功利主义到间接功利主义的演变,使它们呈现出一种向美德主义靠拢的发展倾向。本文将指出在功利主义在幸福问题的讨论上曾遭到美德伦理的批评,但它很快意识到功利主义原则美德化的内在必要性,美德在功利主义立场下对公众合作和个体自律能够产生传统功利主义无法做到的影响;最后功利主义的美德主义在面对“知行分离”的困境,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绿色美德”及情感基础。
01
美德伦理对功利主义关于 幸福之“得”的批评
在当代西方幸福论中,功利主义者以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作为获取幸福过程中人们道德行为的根本规范,尽管它所坚持的方法和理论旨趣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道德的共识,但是当代学界对它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比如,指责功利主义在陈述立场上设立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功利主义在强调后果作为道德行动的正确原则时会违背人基本的道德直觉;以及功利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等等 [1](PP.247-249)。上述批评毋庸赘述,我们更关注于另一重点,功利主义关于幸福的价值论基础到底同美德伦理有何种差异,在美德伦理的系列批评中功利主义如何导向一种美德主义。
具体而言,我将从对功利主义对幸福的内涵、幸福的权重、测量及意义这几个方面看待它同美德伦理的差异。
1、在幸福的内涵上。早期功利主义者以快乐来界定幸福,形成了备受争议的享乐主义(Hedonism)幸福观,经过批评和修正后,当代功利主义者又陆续提出了以欲望(desire)、偏好(preference)等来界定幸福的各种主观主义幸福观,以及以需要(needs)等来界定的客观主义幸福观。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牛津大学的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他对well-being的从边沁的主观主义到当代新享乐主义,乃至于客观主义的发展做了详尽的评析。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以及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对幸福概念的古今演变及争论焦点做了全面的梳理,将“功利”所指向的主观主义幸福观放在平等语境下进行考量。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传统还是当代功利主义的更新,都坚持幸福就是“功利”的增加或者是满足,而从功利主义的当代发展趋势来看,“功利”更倾向于主体的感受和体验[2](P129)。
相比之下,美德伦理学则强调以个人完善以及生活的成就来定义幸福,在这些承续了古希腊传统的思想方法看来,现代规则伦理不是没有“幸福”概念,而是对“幸福”的理解过于单薄。现代英语作者通常用happiness来称谓“幸福”,所以当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原则时,功利就意味这一种感性经验。“尤其是当代行为后果主义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解读过分抽象化和简单化,抽离了其在历史中的真实诉求……”。[3](P152)当然,这似乎是现代性的通病,即便是反对把幸福纳入道德考量的康德,也同功利主义一样,认为幸福仅是单一的主观感受而已。
美德伦理学在幸福的理解同功利主义的本质差异在于,它不是态度上的,而是认识上的,美德伦理学从来把古希腊的“幸福(eudaimonia)”看成是一种最佳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感受,“它意味着行为主体拥有一个完整的、丰满的生活,而比片刻的愉悦和兴奋丰富得多……幸福在更充分的意义上是一个人之为人的充分实现。”[4](P112)这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丰富性是体现在一个人一生的实现过程中的,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美德伦理学所说的“幸福”都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术语来表达人们理想的人生圆满和丰饶,由此我们常见的“well-being”更符合这种解释。其二这种“幸福”概念还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存在论或道德形而上学,即它需要在目的论框架中才能得到解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幸福被规定为人最终的至高目的,在其文中完善(teleios希腊语)一词的词根指的就是目的(telos)[5](P18)。也就是说幸福是一个道德主体在世的终极目的和本然成就,这个主体如果实现了自身目的,也就是完满地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和本性。那么,即使是当代美德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有所发挥,也是在这样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论基础上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从他们对道德主体的论述上,美德伦理所指的“幸福”不是单一的感受和行动的片段,而是关注自我实现的过程如何成为一种长期以来对“本真性”的追求和印证[6](PP.18-19),从而在成为一个人的意义上极具重要性。
2、幸福的结构支撑。由于幸福必然包含各种不同的价值与善,而这些不同的价值与善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功利主义指出幸福在道德行动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此它们采用单一尺度的还原论,将各种特征或价值都化约为幸福。功利主义为了一元论的简化主义能够得到理论支撑,它对幸福结构的配置以及为了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能够被接纳做了较多工作。面对幸福和其它道德价值的结构性冲突,功利主义的幸福架构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二十世纪以来出现的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就分别用不同的立场解释一元论的合理性。行为功利主义所采取的简化论思路即试图把人们关于道德行动的考量全部纳入幸福的问题之下,通过幸福这一最优后果对所有行动做出终极解释。边沁大致算得上是行为功利主义者,他主张功利应该是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考量的后果,最好行动促生幸福最大化这一标准在所有行动理由中是优先的。当代学者斯马特(J.J.C. Smart)等则继承了前人对行动的重视,强调功利主义的具体行动后果就是评价该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
但是,这会导致某些获取幸福的行为陷入道德质疑,如果获取最大幸福将违背基本的人伦和道德直觉时,这种幸福还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幸福吗?因此间接功利主义或规则功利主义接下来要它处理的是,功利主义体系如何把其它道德要素重新嵌入幸福结构。当代规则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勃兰特(Richard B. Brandt)、莱恩斯(David Lyons)、厄姆森(James O.Urmson)大体上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在幸福作为评判的标准上建立至少两种层级的规则,人们在大方向上拥的一阶判断就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总体规则,但是在通常行为中遵循的则是隐含着道德直觉的二阶判断,人们没有必要每时每刻都以功利的标准进行计算,只要在一阶原则的意义上保持功利主义的幸福认同即可。
此外,值得一提还有当代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约翰·哈桑尼(John Harsanyi)的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他认为暂且撇开道德冲突问题,功利主义从社会公正分配的层面上也有必要针对“幸福”结构重新反思。功利主义为的是造就幸福的人和幸福的事,“殊不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使幸福的人数增多,而是尽可能多地使人幸福。”[2](P129)换言之,功利主义自己已经意识到利益总量的最大化忽略了巨大的利益分配不公;利益总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通过人口总量的增加得到实现,但人均幸福却大大减少了。总的来说,无论功利主义怎样在幸福的权重和结构上进行技术性调整,它总能从人类生存及其复杂的行为模式中捕捉到幸福这一界面的优先性,并使它符合人们追求社会整体和长远益处的道德直觉,这正是功利主义始终产生吸引力的奥秘所在。
面对上述演变,美德伦理学一直以来提出的批评就是,尽管功利主义可以把幸福解释为整体利益和长远考虑,但它们在本质上已经走进快乐一元论的死胡同,它们对幸福结构的单向度理解都使它同其它更丰厚、复杂的人类生活产生无法克服的冲突。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幸福结构上采取了一种更和谐包容的设置,它试图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包容多元价值的体系。哪怕在亚里士多美德伦理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两种幸福论的冲突[7](pp.88-90),即内在善和外在善的矛盾,但通过这组矛盾,美德伦理向我们展示了它想要通过更丰厚的幸福观念努力达成生活意义及人之完整性的逻辑自洽。一方面从存在论意义上理解的幸福结构既包含着感性经验又囊括了与人的情感、欲求相关联的外在善的兴旺;而另一方面亚氏又不断强调,幸福的结构可以非常单纯以至于仅仅内求于心,最高的幸福是不假外求的“沉思”的智慧活动。由此可见,美德伦理同功利主义在幸福结构的设想是在不同的层面讨论问题。从而美德伦理对功利主义的指摘能够暴露功利主义理论最深处的隐忧,那就是功利主义的还原论仅限于一种策略,它缺失对幸福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建构依据,在何种意义上幸福是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它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有可能让功利主义在推动更具整体性和长远性的现实需求时显得动力不足。
3、在幸福的测量上。功利主义路径擅长幸福的计算与测量,它又根据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两个维度,进一步形成了福利主义、生活质量等理论,并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协助幸福测量。当哈桑尼提出平均效用主义时,功利主义的幸福理论开始关注个体获得福利的总量,因而,福利成为当代功利主义计算“功利”或“幸福”的代名词,前述所有对“幸福”内涵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来自当代经济学福利主义对福利的不断推进。为了测量的准确和深入,“功利主义对福利进行重新整理,它从单一元素转向多元素组合,甚至产生了各项福利清单。在当代发展中,我们看到功利主义对幸福结构的观察更注重主体的精神和心理动机的复杂性”[8](P105)。加拿大学者李奥纳多·萨姆纳(L.W.Sumner)在《福利、幸福与伦理学》中主张在关注人的真实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更稳定的幸福要素。牛津大学的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 2006)在《理由与善》中指出功利主义对主观感受的强调是在回应传统的批评,它既在主观上产生了“创造性的善”的优越性,又具有客观的对应物。丹尼尔·卡纳曼(D. Kahneman, 1999)的《幸福:享乐主义心理学的基础》通过情感和知觉价值等心理学表现论述了主观状态与幸福之间的关联,揭示了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幸福悖论”的原由。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人类满意度与公共政策》中提出收入和幸福视角之间的关系,同时丝毫不放弃客观维度在社会发展和生活指标上的增进。
总之,近十年来功利主义在幸福测量上的客观倾向是有利于推进包括环境生态在内的数值衡量体系的,但同时也暴露出数值无法体现的缺憾。相比之下,德性伦理学基本上拒绝对幸福进行数量计算,但是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从理智德性和普遍性上进行对个人完善度的推理。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有两种变形都强调了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努斯鲍姆的普遍主义变形、麦克道尔与伽达默尔的明智论的变形。努斯鲍姆通过列举人性的普遍性特征并提出通过“美德”理解人的“能力”,从而确立核心能力清单来框定一种体面生活的基本维度,“德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普遍谋划的能力,它是与人建立联系、形成善好的理解并审慎规划生命的不可或缺的品性和习惯”[9](P16)。同时,明智论强调的是理智德性具有获取幸福的赋值和计算功能,它本身代表的一种价值考量的能力,“它着眼于人类生活的普遍目标,其中包括个体、家庭、城邦的幸福”[10](P131),即明智就是通过合适的手段来选择实现其既定目标的能力。
尽管美德伦理在幸福的内涵、结构以及测量运算的对比三个方面都提出了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但是我们看到二者在计算和测量幸福生活上的某些趋同性。晚近以来美德伦理在当代思潮中卷土重来,其势头似乎能够打破功利主义在伦理学语境下忽明忽暗的尴尬局面,进而有可能再次点亮功利主义为人类福利而努力的价值诉求。
02
功利主义成为一种美德理论
功利主义路径从幸福解释“善行”,将善行纳入幸福内涵;而美德伦理路径偏重从“善行”解释幸福生活何以可能,将品行、德性作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尽管两种路径彼此逆向论证,但两者的当代发展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主体性的视角,即二者不仅一致认同了主体的精神活动和心理动机,而且承认个性和美德之于整体生活的意义,因而功利主义呈现出一种用情感、品性解释行为动机的趋向,那么,功利主义是否能够,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美德伦理理论?
1、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在理路上的相似性
首先,功利主义同美德具有相似性,从消极意义而言,康德主义义务论立场对幸福进行过批判,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美德伦理,义务论皆以道德与幸福无关为由指责它们对幸福的重视偏离了道德纯粹性的方向,甚至是走向了对立的方向。然而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在共同回应康德主义的幸福观时,提出人类身体所具有的“切身性”构成了无可回溯的价值诉求,如果脱离这种身体的和经验的善“就会对人类的道德状况提出一种严重不完备和高度扭曲的理解”[11](P337),也就是说道德必须纳入对幸福的考虑才是完善和健康的。
其次,功利主义尽管从个体趋乐避苦的直观经验为原则整合社会成员的基本行动,但他们仍然希望在一个自由和自我可能成为社会主导原则的情况下,通过诉诸于行为者的性格与品质获取上述规范背后道德价值的安稳感。对于当代功利主义者而言,这一点已经得到解释,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功利主义的评价是,“人们能够自由地为自己做决定也是重要的,即使是糟糕的决定,作为人们发展品德能力的唯一方式,人只能通过持续的实践才能自己获知各种生活的可能性”[12](P28)。功利主义实质上会要求我们保护这种个人的自由,从而形成一种习惯和素养。这种印象尤其体现在密尔的文本中,他并没有否认过亚里士多德对于美好生活以及个人完善发展的论述,甚至密尔对边沁的改进都一一证明了“在达致人性的完美丰饶和自由发展的目标中,幸福不是被直接追求的目标”,他诉诸优雅的教养和学识乃至于一贯的品性[13](P38)。
第三,功利主义在回应有关人的完整性,以及有关道德直觉的批评时,就倾向于从行动的一贯性和人的完整进行辩护。当然完整性本身并不一定是美德伦理的主张,但功利主义在回答追求幸福何以能够造就人的完整性时指出功利主义的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来自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深入“筹划”及“慎思”,在功利主义的牺牲行为之后同样蕴含着主体对于高尚品性的坚持认可,这是建基于对主体一贯性和统一性的认知[14](PP.390-391)。当然,当代功利主义的辩护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承认与完整性的不相容;另一种是阐释自己在何种意义上同完整性是相容的。功利主义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更重视以相容性进行自我辩护,从而功利主义在当代发展中呈现出间接功利主义的倾向[15](P90)。相容性和不相容性虽然是研究者的概括,但是间接功利主义在相容性方面所做的努力的确弥补了传统功利主义忽视性情和动机的不足,总体上推进了向理想的功利主义美德和品质的转向。
功利主义至少在上述三个方面体现了美德的倾向,但功利主义理论体现出美德理论的倾向其独特价值何在?
2、功利主义原则的现实优势与美德的保障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密尔首先都默认了,美德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高于幸福的目的[16](PP.235-239),因为这样理解的美德能够确保某些情感和行为模式,而这种保障所带来的好处则弥补了在德福冲突的特殊情况下可能丢失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利益都出自于得到保证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出自于某些得到保证的行动。我们要阐明的是,功利主义重视美德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为保障行为始终指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确立一种品质上的保障。 首先,功利主义对“幸福”的阐释不仅着眼于空间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其优势之处还在于它能从时间上考察过去、当下和未来利益之间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功利主义原则聚焦于实现最大幸福的普遍性和整体性考量,在这一目标下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应该实现利益总量的最大化。更一步而言,“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推出功利主义的普遍性的、不偏不倚的观察视角……即所有的为行为后果所裹挟到的当事人都应获得同等的顾及。既然不得因为特殊社会关系而有所不同,也不得因效果出现较晚则其重要性就要看成是弱于近期的效果……从一个普遍的视角来看,后代人与当代人已被置于同等的地位。后代人的利益对于一位功利主义者而言必须得到像其同代人利益一样的关注。” [2](P134)由此而言,虽然同美德伦理的解释理路不同,但功利主义从未来利益对人们整体的影响发展出很具竞争力的解释;因此能够从生态和环境对未来人类美好生活的影响出发对当下道德行动做出宏大且恰当的思量。可是,一旦要将这种思路贯彻到人们的具体行动中去,功利主义原则便缺失了为坚持长远利益而一以贯之的行为动力,它们发现如果能够得到美德理论的加持,才能主体的行动中找到合适的动机和性格依托。
其次,相比于道义论和契约主义,功利主义有丰足的理由把环境和生态纳入当代人的道德考虑。处在专业哲学家角色中的研究者们往往都对生态和环境问题保持沉默。首先在当代康德主义,比如考斯嘉德(Christine M. Korsgaard)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构思恰当的道德理论不会考虑行为的后果,它强调的是对个体性和内在性的“善良意志”的探讨。他们对行为如何并不感兴趣,而只关注行为背后的形而上学源泉。同时,契约主义在讨论普遍的环境和生态保护上也存在困难,一方面契约主义很难缔结并坚持大规模的合作契约,另一方面它将所有非相关的契约缔约方排除在首要的道德考虑之外,而我们对环境的多数争论都集中在那些被排斥的对象上——如后代、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婴儿、动物等等。可见,从道德考察的思维和对象而言,功利主义是擅长解释现实问题的,因为对幸福的重视,它在每个新阶段都尽可能地融入了那些影响人们获取美好生活的要素。
第三,面对道义论和契约论所坚守的人权和个体性不容侵犯的普世原则,当代功利主义更擅长通过基本权益之外的主观感受来化解具体文化传统、具体情景同普遍原则的价值冲突。因而功利主义具备了考量人的主体性和外在情景于一体的灵活的思维优势。它在对幸福作为“福利”或者“愉悦”的理解上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功利主义方法的道德智慧:即能直面当代人的伦理悖论和道德困境,尤其是在不断涌现的新科技和应用伦理的新问题下具有明显的解释力。
由此,我们认为如果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行动原则,而是一种习惯和智慧品质的话,那么其理论本身的优势则更能通过美德主义的倾向凸显出稳定性。
03
美德还是伪善?
那么,按照上述要求实现功利主义的智慧思考,这其中的美德是否还具有像美德伦理中的那种同终极目的的统一性?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践行美德并不一定产生最好的结果那又该如何?
1、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在行动中的匹配
既然契约和外在制度都不足以作为一种行动原则的心理保障,那么美德在功利主义中的稳定作用则更加凸显出来。功利主义原则在实际生活的应用中往往同美德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学者对人们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行动的可能性归纳出几类:“(1)行动单独由功效原则的某一版本组成或者以“总体”原则而不是其它的“次要”原则组成;(2)行动包括一套足够全面的次一级准则用来决定每一部分行为所产生的特定案例;(3)包含某些次要准则但不是一种绝对全面的体系。而在第三种情况中,形式可再分为三种情况:3.1均可直接运用功利原则确定;3.2其中一部分可以根据功利原则确定,其余的则无法按常规而定,而是当事人根据自己喜好定;3.3 它们可能都不由常规而定。” [17](P451)在这些情况中,尤其后两者是更为常见的情形,可以分列出准则与美德的多种组合的方式。即便一个功利主义者出于自己的立场,选择了一种最好的行为准则和美德保障的组合来最大化他的幸福,但是仍有一些关于美德的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基于功利主义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功利为原则,那么与之匹配的美德则是因着这一原则培养起来的品质和动机。建立一种美德或品质作为功利主义原则的保障是有代价的,一个人就需要不断发展这种美德,呵护并展现其品质。这一过程中,美德作为个人品质既可能在实施中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从而增加其行动的良好后果,也有可能导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后果,出现跟功利主义原则的冲突。那么,功利主义是否还会运用美德呢?
第二,功利主义运用美德品性在于美德需要情感作为行动者的动机。那么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时产生出自爱的情感是自然的,另一种则是为他人和公众利益而牺牲自己时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后一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不断扩展、涵养和陶冶自己的良心情感,诸如同情心或者大爱等等。那么美德并不是因为个人理性地计算效用后果而激发出来,而是被某种涵养的情感触动而产生。那么,美德则在一些情景下一定会独立于功利主义的最终期待,而无法始终贯彻功利主义原则。
上述两种情况其实涉及到美德和功利主义如何在手段和目的上统一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选择从哪个视角看问题。在功利主义的视阈中,美德并不能算作一种具有终极目的的存在。很多功利主义者对遵循哪种规则和保障的组合对他们各自的社会是最好的这个问题上,已得出结论,“由某些特定美德,尤其如真诚、忠信等美德加以保障是最好的。如果这是结论,那么功利主义者就会做出创造、保存和表现恰当美德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成长过程中获得了这种能力。” [17] (P459)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此刻我们很难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对规则加美德的搭配进行评估计算,一旦美德品性的特征融入功利主义以及次级准则,那么对于整个事态的计算就已经转变为,我们需要计算一下是否要履行美德的问题。如此一来美德依然是作为手段和工具的,除非功利主义用一种长远和整体的眼光来统合美德,功利主义可能接受这种变化,即履行美德的行为之后果从长远来说是一种获得善好的过程。这基于一种心理上的转变,也许人们在追求功利主义主张的过程中把美德当作一种工具,但是因为这种工具在施展它的过程中无一不体会到一种快乐,甚至是超越一般的快乐。那么,美德必然会导向一种信念,即使在行动中能够施展这种品性的情景没有再现,但该信念业已形成一种良好的惯性。
如果从美德作为终极目的的视角来看,功利主义仅仅把美德当作一种良心情感用以推动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在这里则很难得到支持,一个人需要多么强烈的情感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于生命而换取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如果将美德理解为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强大惯性,它能够超越个体当下的情感、欲望,形成一种向善的力量。这取决于一个人长期培养起来的自我克制和美好情操,它的产生不依靠于功利主义原则,带有一种自身的独立性。
2、美德伦理真正的独立性在于如何辨别伪善
然而,我们仍旧担心的是,处于内心的情感和动机难以获得外在的判断,一种行动只有基于其持续的结果才能产生人们对此的信仰。如果某人为了获得他人对自己良好形象的信赖,尤其是在对保护生态环境这样超出个人当下利益,也有可能违背一般行动直觉的情况下,装作真诚地承诺那么实际上就扮演了一种伪善。在功利主义的行动中要真正形成一种美德主义的倾向,美德和伪善是应得到区分的。
按照美德伦理的思路,为了赢得有经验的人的信任,展现稳定的性格状态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一种难以伪装的、持久的品性。明智是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智论作为核心观念的德性能力,他们认为明智不会受到利益计算的行为影响,通常来说,它能够产生足以克服利益动机的强大影响力,它能使美德伦理保持原生品质。需要澄清的是,康德曾经在很早就把明智逐出了道德范畴,他认为明智不过是实现自身幸福的方法和测算能力,并不具有任何道德内蕴。接着马克思·韦伯在对现代性的描述中也着力把明智描述为与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而这一扭曲的理解就掩盖了明智作为美德的价值属性,可以说它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是唯一沟通实践活动和理智活动的心灵品质,它自身属于理智德性,具有反思价值的能力,但同时又能为诸如节制、勇敢、仁慈的伦理德性提供方向性指引。
就其本质而言,明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绝非价值中立的,将它列入伦理学的范畴恰恰印证了明智不仅仅是工具,它的实现过程本身就是人的至善与欣欣向荣的好生活,这一人之为人的卓越性正好决定了明智在价值上的卓越性。著名功利主义学者萨姆纳(L.W.Sumner)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明智的价值性作了进一步发挥。主张在关注人的真实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更好的幸福论,这其中明智代表着人们对多元价值的判断和择善而从的主体性选择能力,这种品性能够对功利主义原则提供最大的补充。
04 功利主义为整体和未来求思 需要成为美德主义者
功利主义从“得”到“德”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如何创造美好生活上针对生态保护、减少人对环境的破坏提出了自己的倡议。功利最大化的主张反过来也意味着在生态和环境保护上对自然施以尽量小的破坏,这在做法上需要依靠人的实践美德和道德情操的培养。
当今时代对于环境和生态的保护积极方面主要依赖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强制;但从消极方面来说,仍有广阔的空间依赖于人们的自觉和自愿,而这一点正是求思于功利主义对美德和生活智慧的普遍关注,“因为最好的结果将产生于将我的行为同众人麻木而常规的集体行动中的脱解出来” [18](P161)。功利主义的优势恰能提醒人们在以个体利益为生活原则的时代中,也许唤起独立于时代的“道德圣徒”是一种妄想,但是为谋求未来更美好生活逐渐培养人们的节制和内在修养却并不是不可行的。
我们在“面对气候变化,臭氧层耗尽和大量物种灭绝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规范我们的行为,对每个关切自然或人类福祉的人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且从传统来说这种担忧也应理解为是接近道德反思的核心的。” [18](P162)我们承认功利主义的这一论述将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纳入伦理考量是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的,并且提出用明智这样的实践智慧对整体生活环境加以综合思量,从而形成人们生活与行动的良性发展,不饬于提供了一种“环保美德”的新品质。若让一位传统功利主义者来看,环保问题要做到卓有成效,可能需要一种精明的计算,但是如果当大规模的“集体环保无意识”出现时,众人基于个体自我的多重博弈之下仍然会陷入利己主义的情感麻木。举目全球,各国之间的气候和环境协议也莫过如此,其导致的就是不合作的恶性循环。
功利主义的深度反思应该能够让我们放弃掉计算,代之以一种非计算的行为增长:个性特征、性情、情感和我们称之为美德与“明智”的东西。我们认为,当面对全球环境变化时,普遍的道德策略应该是努力发展和培养出恰当的美德,而不是促进计算的规则。此处有几点仍需明确:1、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是有必要的,而培养有美德的公民并不同它相互排斥。2、发展集体观念建立环境保护的共识是有必要的,个体需要形成信念在共同行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伦理学的任务仍要关心这些环境保护的意图究竟包括什么,如何产生,以及由什么样的人拥有和在什么情况下采用。3、我同意一些学者的主张,“一种道德美德是一种系统地产生善的性格特征……并且情感在维持行为模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行为模式表达了诸如忠诚、勇气、坚持等假定的美德。” [19](P108)因为如果没有情感的支撑,很难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生物之间会存在怎样的养育、友谊和家庭伙伴关系。这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功利主义的计算之外还是有一个非计算的性格的存在。那么,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如何把美德安置在功利主义原则之中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计算和非计算之间进行权衡。
作为一种在当代发展已经颇为复杂精细的功利主义,当涉及到全球环境变化时,他们既可以是灵活的、道德的环保主义者,但在大多数其他一般领域又可以同时是灵活的计算者。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功利主义在发展中呈现的美德主义倾向,美德赋予他们在后果运算中学会了实践智慧的价值考量。一个功利主义者在当代情景下,从习惯上形成善良的“绿色美德”会帮助他形成一种优雅的人文气息,在日常生活中恰当地减少自己的世俗消费,从而保持对美德和品质的信赖。
作为结论,如果要对生态环境乃至于我们的真正的生活质量承担起责任,功利主义的原则应该从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考量延伸至对整体物种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欣欣向荣生活的重新定位。虽然从美德的角度看,明智并未向我们呈现哪些具体而清晰的价值指向,但是它本质上蕴含着重建人文性的努力、对贪婪欲望的节制,以及对自由个性的运思和创新,这都可能出现新的生长点,这将是功利主义者变成一个美德主义者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江畅. 西方德性思想史概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甘绍平. 伦理学的当代建构[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3] 方菲. 动机、意图与功利主义的阐释[J]. 道德与文明,2018,(4).
[4] Richard Taylor,Ethics,Faith and Reason [M],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85 .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寥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Sarah Conly,“Flourishing and the Failure of the Ethics of Virtue” [100],in Peter A. French et al eds.,Ethical Theory:Character and virtue,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
[8] 刘科. 我们追求的幸福是什么?[100]. 当代外国哲学.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8年.
[9]玛莎·C·纳斯鲍姆.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M].田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 Ron Beadle,MacIntyre and the amorality of management [100],presented to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2001,(07).
[11] 徐向东. 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12] Amartya Sen, Rights and Agency [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2,(11).
[13]John Gray, Mill on Liberty,A Defense [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3.
[14]Shelly Kagan,The Limit of Morality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5]刘佳宝. 功利主义与个人完整性是否相容——论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6).
[16]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 [M],chap.4 in J.S.Mill,Collected Works, ed. J.M.Robson et al,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3,vol. 10.
[17] John Kilcullen,Utilitarianism and Virtue [J],Ethics,Vol.93,No.3,1983.
[18] Dale Jamieson,When Utilitarianism Should Be Virtue Theorists [J],Utilitas, Vol 19,2007,(2).
[19]Julia Driver,Uneasy Virtue [M],New York:New York Press,2001.
注:文章发表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9月第57卷第5期。部分注释有删减,如需引用,烦请查校期刊原文。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