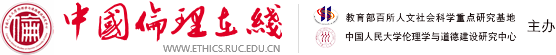疫情应对中的科技治国模式
摘要: 提出以公民驱动(citizendriven)的科技治国模式来应对疫情的观点, 公民驱动的科技治国模式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 中国和欧美应对疫情方式的主要不同在于, 疫情应对中的科技治国模式
此文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2020-05-14 第5版 文化周刊), 原标题为:疫情应对中的科技治国模式。
编者按
新冠疫情全球暴发,Zeit Online成为欧洲哲学家发表观点的热点媒体,德国哲学家、以提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理论著称的阿尔弗雷德·诺德曼在该网站发表“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力来战胜新冠疫情”“你们都只想当一个个小点吗”两篇文章,提出以公民驱动(citizendriven)的科技治国模式来应对疫情的观点。科技治国的主旨是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尤其强调科学地治理社会公共事务。
4月中旬开始,诺德曼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和美国哲学家、SPT(技术哲学学会)首任主席卡尔·米切姆以邮件形式,对抗疫中不同的科技治国模式进行比较性讨论。本报现刊登三人讨论的核心观点,本文由刘永谋译成中文。
公民驱动的科技治国模式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
中国和欧美应对疫情方式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国的目标是努力根除病毒,而欧美包括德国的目标仅仅是“让曲线变平”,即努力控制病毒的传染速度,避免不受控制的感染激增使得医疗系统崩溃。西方人考虑的不是必须“赶走”病毒,而是与病毒共同生活,但它的冲击应控制在公共医疗系统负载允许的范围之内。意大利的系统超载了,而德国控制得很好。疫苗研发需要很长时间,不能因此让社会生活“停摆”。德国抗疫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在不“停摆”社会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
新冠肺炎全球暴发,让我们处于“真实世界实验”之中。实验通常在实验室的封闭空间内进行,在受控的条件下实施有目的的干预。真实世界实验发生在社会中,开始于意外的突发事件。存在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把新冠肺炎当作“大号流感”来简单对待,另一种是迅速执行以隔离为核心的科技治国措施。中国初期采取的严格隔离措施,在欧洲不可能完全复制。德国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科技治国措施,同时努力维持默克尔总理所称的“社会团结”。
然而,我们看到的科技治国模式都是“政府驱动”(government-driven)的,在欧美国家招致公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人们担心政府权力越界。有没有其他的可选方案呢?当今科技发达,社会技术长足发展,“公民驱动”的科技治国路线是可能实现的。
今日德国经济实力雄厚,富有创造力,而且已数字化,民众具备不少相关科学知识,人人均可尝试发挥个人创造力来抗击疫情。尤其是可以通过“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方式,大家分享、汇聚和改进抗疫知识,主动运用这些知识来应对病毒。最近,德国政府征集抗疫办法,48小时内超过28000名参与者提交了超过1500个想法,名为“我们对病毒”的黑客项目创建了新冠疫情追踪程序。
很多德国人用“公民科学”知识来“自我”应对病毒,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离、餐厅必须预订,等等。此类社会技术是公民自发创造和推广的,需要民众参与(常常运用信息和网络技术)创造和实践,而不是由政府强制施行,属于相关科技知识的理性应用,并根据当地情况打上鲜明的地方性烙印。公民驱动模式实现的不是默克尔式的“消极团结”,而是“积极团结”,邻人们不是被完全宅在家里,而是谨慎地走出家门,保持必要距离地共同生活。
在公民驱动模式中,我们不再是人口技术中的统计数字,或者盲目而被动如气体分子般杂乱运动的“小点”,而成为能动性被激发的、训练有素的自我治理者,可以自主思考并且承担责任。
政府驱动的科技治国模式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一定阶段,存在“根除病毒”和“拉平曲线”两条应对路线。长远来看,中国也要与病毒“和平共处”。但是,特效药物和疫苗研发出来后,才能真正实现“不停滞公共生活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在这之前,如果出现大规模死亡、医疗系统崩溃、社会动荡、极端势力,能实现和平共存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抗疫只有一条路线:在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最大限度减少病毒对社会的伤害,包括生命、经济、心理和秩序等各方面的伤害。各个国家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方法实现上述目标。随着对病毒了解增多,各国不断调整应对方法。
欧美有自己的国情: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很多人愿意自行担责,不希望政府过多干涉;最近30年,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盛行,公众不信任科学技术和专家;人民普遍储蓄很少,对国家、政府和紧急状态的不信任,等等。这些决定欧美政府无法采取理想中的严格隔离措施。
如何将科技治国与欧洲国情兼容?诺德曼提出科技治国的公民驱动模式值得关注。有效实施诺德曼模式,需要国民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教育水平和自治能力。国民素质情况不同,实施效果不一样。在普遍科学素养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公众必须要听取专家意见,不能盲目行动。
作为疫情先发地,一开始对新病毒很无知,选择2003年非典疫情类似应对模式很正常,将COVID-19视为类似SARS而非“大号流感”很自然。政府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也有“人命关天”的观点。中国疫情应对成效有目共睹,也是根据国情作出选择的结果。
在中国,科学和专家的位置较高,反科学思潮不流行。在做决策前,政府对科学家意见给予足够重视。不过,政府驱动的科技治国模式在中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社会隔离实施得好,这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中国成功隔离湖北,全国阶段性“停摆”,然后举全国医疗资源帮助湖北。
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模式显然是更高效的,但也需要一些更周全的考量,如做好与社会社群间的沟通与协调、将科技手段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对专家进行伦理和责任教育,等等。同其他国家一样,**踪、“健康码”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并非什么新技术措施,疫情让隐私权保护问题暴露得更明显。
全球瘟疫必须要全球共同应对,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不可能。如果印度和非洲疫情大暴发,其他国家不应袖手旁观,否则肯定会让其他国家疫情死灰复燃。
没有科技治国约束的反智模式

卡尔·米切姆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教授
美国的疫情应对很难理解,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言行,很多人会觉得匪夷所思。虽然显得极端,但他的反应并不很奇怪。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得到了大约35%到45%的公众支持率,这是比较高的。
要理解美国的疫情应对,就要了解它长期的反智传统。美国是数百年前躲避家乡高压统治的欧洲人“人为”创立的,由启蒙思想家勉强将各殖民地拼凑在一起,立法保护白人的个人自由,却拒绝给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同样的权利。立国者深知美国的脆弱,设计了一种由科技治国约束的美式民主制度:表达普通民众诉求的众议院,由精英制的参议院制衡,还要与贵族式选举出来的美国总统竞争,再加上半独立的司法机构,最后成为洛威尔描述的“一架先要自己动起来的机器”。
1828年,特朗普最喜欢的杰克逊总统当选,立国时的科技治国秩序开始被“磨损”,受到个人主义和拓荒者、牛仔文化所固有的反智主义的冲击。一开始,美国就想实现“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可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内战之后与外来移民的嫌隙使之雪上加霜。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只有个人,社会只是一种附带现象。罗斯福“新政”缓和了对精英和专家的怀疑,但极端的反智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美国依旧非常盛行。
美国人没有从病毒手中保护社会的共识。自由主义者保护的是行己所愿的个人权利。持相反观点的人也有,以科技知识支撑自己的立场,得到的支持和力量就很不够——要知道,35%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仅25%的美国人承认气候变化。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新科技的进展,这给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巨大挑战。
不少美国民众反对专家建议,抗议社交隔离和居家法令,要求重开经济和公共生活,高呼革命年代的口号,比如“不要欺负我”“让我自由,或者让我死”,以及“我们有权决定如何保护自己。让威权主义政府滚开”,等等。专家容易轻视特朗普,但他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大师,不需要专家实现效率,只需在推特上呼应上述要求——在推特上高喊“解放密歇根”“解放明尼苏达”“解放弗吉尼亚”。不少美国人迷信个人自由,这限制了公民驱动的科技治国措施在美国的施行。
自由主义在美国导致对专家和科学家共同体的怀疑。一些美国科学家甚至被指责不忠叛国,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此,有的科学家不得不向落后低头,以证明自己的“美国性”,但作用不大,有时候被搞得很感慨:“我们很忠诚,又有用,值得给我们增加研究经费”。冠状病毒研究要求加强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这会让自诩为“真正美国人”的人觉得专家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面对全球疫情暴发,我很怀疑是否真会有有效的国际或全球性合作和协作,尤其是发达国家是否会帮助不发达国家。欧洲甚至不能相互帮助。而对于国内某些州帮助其他州的行动,一些美国人总是很矛盾,甚至比帮助临近的其他美洲国家更矛盾,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建国前13个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即使对外援助的联邦预算数量一直很少,其仍然遭到美国公众的持续反对。某种科技治国方面的全球性的协作和合作从未如此被需要过,但希望渺茫。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