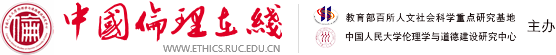避孕技术对家庭道德的重塑:从义务转向权利
摘要: 道德家庭", 要想实现自我就必须离婚 道德家庭规范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技术冲击, 这场冲击从根本上挑战了道德家庭的观念——尊严来自履行义务
家庭是创造归属感的自然单位,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就在家庭的养育中成长。物理上的亲近被关于归属的故事进一步拉近:这些故事把每一代新人都纳入家庭,创造一个"我们"的概念。家庭中关于义务的故事点明责任,其他叙事把我们的行动与结果联系起来。像所有家庭一样,我的家庭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既有英雄也有败家子。
家族的血缘联系使相互对立的信念体系得以互相容忍,但在1945年,有一种信念体系在西方社会几乎是普遍性的,我在此称其为"道德家庭"(the ethical family)。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符合道德的信念体系,它事实上与今天许多家庭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我只是用此来强调当时家庭中普遍长期存在的道德结构。
1945年时几乎每个人都属于这样的家庭,但接下来的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各国,人们开始抛弃对家庭的义务。离婚率飙升,美国于1980年左右达到顶峰,英国稍晚。而随着受教育程度不同者之间出现新的分化,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了。
01
顶层发生的冲击:要想实现自我就必须离婚
道德家庭规范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技术冲击。避孕药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掌控人生的机会:性行为可以不再像以前那样导致怀孕了。这使得寻找合适伴侣更为方便。短期性关系变得不那么危险了,所以"苦寻佳偶"的旧方式被婚前同居的新方式取代,这种寻觅配偶的方式要可靠得多。拉金(PhilipLarkin)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诗就曾写道:"性行为开始/于1963年"。
这场解放始于技术辅助的性行为,但很快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场深刻的思想冲击解放了个人,使我们不必再受道德家庭的许多陈旧规范束缚。对家庭的义务让位于新的对自己的义务:通过个人成就实现自我。人们修改了法律,让离婚变得更容易。而离婚更容易意味着它不再会遭受指责,不再被视为某一方的过错。
不意外的是,这场思想冲击始于大学校园,所以主要影响的是受教育程度高的新阶层。这场冲击从根本上挑战了道德家庭的观念——尊严来自履行义务。新的伦理观用自我取代了家庭的位置;尊严不再源于履行义务,新伦理观认为尊严源于自我实现。吸引女性的自我实现伦理观是女权主义,吸引男性的是《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以前被视为需要抵制的诱惑行为,现在被视为需要把握住的自我实现时刻。许多新阶层家庭的夫妻都发现,要想实现自我就必须离婚。
随着人们接受了这些新规范,精英婚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另一项冲击——大学的大规模扩张——推动了这样的变化。由于大学的扩张,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与女性的人数趋向一致,这又使寻找合适配偶变得方便多了。人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合适的伴侣(目前因网上交友技术改进,这个趋势还在延续)。很快堕胎合法化又加快了这一趋势,堕胎成为避孕之外的又一道保险。以前作为中间一代的夫妻遵循的规范是性别等级制和对上下两代人负有的共同义务,经此变化之后,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规范成了互相鼓励通过个人成就去实现自我。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通过同居和选择婚配结成了和谐佳侣,所以离婚率下降了。事业有成的父母渴望把自己的成功传给后代,所以,过去反映在子女教育中的性别等级,让位于夫妻共同培养子女的做法。
02
底层受到的冲击:丈夫的失业、暴力与消沉
就像硅谷的技术人士预测新形式的社会联系将减少仇恨一样,人们也曾预测避孕药和堕胎将减少父母不想要的孩子。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一半青少年女性的性行为因此大增。1960年代她们中只有5%在16岁之前发生性行为,到2000年已上升到了23%。
但是,只有当事人心怀谨慎的远虑,避孕药才能阻止怀孕,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这种远虑。事实证明,堕胎这种决定尽管与追求个人实现的新伦理信念体系不冲突,却与强调家庭义务的旧体系格格不入,所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更易接受堕胎。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少女怀孕的情况激增,而她们与男方无法结成持久关系。这样的"少女妈妈"有四个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旧模式,嫁给孩子的父亲——奉子成婚有长久的传统。另一种也是旧模式:她和婴孩继续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的曾祖母就是靠这种方式在村子里生活的,没有遇到任何可怕的后果。第三种选择是模仿一些高知女性追求个人实现的新模式,做单身母亲独立生活,父爱主义国家会为她们提供资金支持和社会性住房。最后一种选择是开始一种同居的新模式:与意味着公开承诺的婚姻相比,孩子的父亲往往更愿意同居。当然,不结婚的男女也能维持稳定关系,但大多数同居都不能演变为持久关系;同居关系平均只能维持14个月。
底层受到的最后一种冲击是经济冲击。随着制造业衰落,中年男性失业。许多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从未接受过强调自我实现的新伦理,许多夫妻继续持守道德家庭的规范:丈夫是一家之主,他的权威来自他养家糊口的角色。这个角色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令人难受的看法:一旦在工厂里成为多余的人就意味着在家里也是多余的人了。原本婚姻是相互尊重的紧密网络,现在却变得不对称了;妻子依然保有自己的尊严,但她的存在却会加重丈夫丧失尊严感的情绪。有时丈夫会采取暴力,试图以此恢复权威,有时丈夫则会陷入消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离婚。
03
重建道德家庭
道德家庭的某些方面是权力与欺凌关系的拙劣伪装,扔掉这些东西再好不过。但从中"解放"出来的很多不过是伪装成自我发现的自私。与此类似,一边以功利主义态度关心"全世界的穷人",一边否认对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觉醒,而是为了摆出道德姿态而获得的廉价快感罢了。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通过描绘杰利比太太(Mrs Jellyby)这个人物讽刺了这种态度。
更根本的是,通过个人成就实现自我的伦理观压倒了对家庭履行义务的伦理观,现在从心理学角度看起来具有缺陷。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极具颠覆性的著作《通往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中写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其他人的斗争中"失去自我",以这样的途径来发现自我。自由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新证据支持朋霍费尔和布鲁克斯的观点。我们因缺乏个人成就感到的遗憾与我们因未能履行义务感到的遗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杰出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对人如何获得幸福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他的结论很明确:"假如你只关心成就,你就得不到想要的幸福……密切的人际关系虽不是生活的一切,但却是生活的核心要素。"这样看来,主张“权利的个人”取代“道德家庭”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悲剧。

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 1942- )美国心理学家,著名的学者和临床咨询与治疗专家,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从事习得性无助、抑郁、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方面的研究。
与上面完全不同的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表明,"变弱"可能意味着"变强"。一个人也许有必要放弃一些权力,以便做出可信的承诺,并从中获益。能够做出承诺是开明自利的特征。说得花哨点就是一种"责任手段"解决了"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该技术的发现者们获得了诺贝尔奖。解决通胀问题的责任手段是让央行独立,解决儿童抚养问题的责任手段是婚姻。
在许多西方国家,婚姻与宗教的关系令它染上了污名,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纯粹世俗性的婚姻论。这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新思维:在所有西方国家,基督教化之前就有婚姻,而且宗教与世俗形式的公共承诺可以毫无冲突地并存。这两种情形中,责任手段的力量都源于公开明确地接受相互义务:尊严感和耻辱感是责任手段所凭依的力量。之前说过,责任手段符合其使用者的自身利益。就像前文所举的例子,这也是一种"开明的"自利,也就是说,它为服从注入了使命感。一旦人们理解了能带来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因果链条,共同遵从就会成为理性行为。就像开明自利可以补充和巩固其他互惠义务一样,经济学揭示公共承诺的价值,心理学揭示履行这些义务的价值,它们都具有补充作用。
这两种学科的洞见结合起来可以有力地对抗通过个人成就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有些枯燥的愿望。但这样做不足以应对家庭领域缩小、道德大家庭转变为王朝式核心家庭的新现实。如何应对这些情况呢?幸运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个重大成果可以抵消这一趋势的影响,那就是寿命的延长。家庭虽然在横向广度上缩小了,但在纵向深度上扩大了,许多家庭现在是四世同堂而不是三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里,最年长的一代下面有很多家人。如果每一代人有两个孩子,那么任何一个活着的曾祖父或曾祖母下面的三代里,将有四个核心家庭和二十个家人。这些家长不一定要退出家庭事务浑噩度日。可以让他们发挥重建尊重的力量,监督大道德家庭里的人履行义务。

本文节选自 《资本主义的未来》
作者: [英]保罗·科利尔
出版社: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译者: 刘波
出版年: 2020-7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凤凰网读书,原编辑:杏花村;主编:魏冰心。原标题:避孕药对家庭道德的重塑
责任编辑:张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