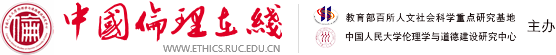卞绍斌:走出自然状态:康德与公共法权的证成
摘要: 着眼于权利在自然状态下不可避免的无保障性和暂时性特质,康德以源初契约理念证成进入公共法权状态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经由共同意志确立普遍法则和可辩护的理性法庭,进而以合法的强制要求各方承担基于公共承认的道德义务,乃是保障并确证每个人的所有权并实现平等自由价值的根本条件。联合的意志、相互责任和平等自由成为确立公共法权状态的规范性前提,也是康德自律观念公共性价值向度的鲜明体现。在此意义上,公共法权的康德式证成路径与传统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存在诸多差异,成为不可或缺的政治思想资源。
Leave the State of Nature: Kant and Justification on the Idea of Public Right
作者简介:卞绍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道德发展研究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1189)。
关 键 词 :康德/公共法权/意志/责任/平等自由/自律/Kant/public right/will/obligation/equal freedom/autonomy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康德式基础究”(18BZX112)的阶段性成果。
导 论
在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部分第42节,康德给出了一个关于公共法权(öffentlichen Rechts)的公设:“在一种你无法避免的共处的关系中,你应当与其他所有人一起离开自然状态,进而进入一种法权状态(rechtlichen Zustand),亦即一种分配正义的状态中。这一公设的理据可以从关于外在关系的法权(相对于暴力)概念分析性地加以阐明”[①]。
该论断至少存在三个难点需要继续追问:一是,走出自然状态的根本缘由是什么?二是,公共法权状态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克服自然状态的缺失;三是,如何理解公共法权作为“公设”的意旨及其可以从法权概念“分析性”地加以阐明?概言之,三个疑难可以归结为:如何理解并证成公共法权观念的客观实在性?
上述疑难同时与康德法权观念本质的界定(自然法还是社会契约论)、康德法权学说与其道德法则(定言命令)的关系以及私人所有权的证成等重大课题相互关联,也是学界对康德法权学说诸多争议的源头。比如费希特在其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②]一书中,尽管基于他对康德《永久和平》一书的理解而认为彼此分享许多相近的观念和理路,尽管其确立自然法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理性存在者具有的绝对自由(自我设定自身的能动性),但在进行法权概念的推证时,却认为“这个演绎与道德法则毫无关系”,进而主张“有形的强制力量,而且只有有形的强制力量,才能使法权概念在这个领域得到认可”[③]。
黑格尔同样否弃了康德法权学说的基本思想立场,认为其基于实践理性和立法的意志确立法权观念并不能呈现普遍的、实体性的精神价值,而和卢梭(费希特亦然)一道沦为基于个体任性而非绝对合理性确定根本法权规范的社会契约论阵营[④]。当代政治家比如罗尔斯虽然在《正义论》中主张一种康德式的证成方案[⑤]。但是自1980年代的“杜威讲座”开始,罗尔斯不断远离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预设,认为其主要强调的是个体自律(Individual Autonomy)而非公共自律(Public Autonomy),进而把康德实践哲学归入完备性的道德学说而无法为公共性政治证成提供根本价值指引[⑥]。
即使在康德学界内部,对其公共法权的阐释和定位依然存在不少分歧。比如瑞普斯坦更为强调康德公共法权论证中所具有的公共性、权威性及其强力性质,进而能够消解自然状态下单边行动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履行政治责任进而获得权利保障的基本缘由,而康德提出的“无法进一步证明的”法权公设主要表明其持有的表征个体自主(Self-Master)性价值的先天(A Priori)证成方式,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普遍法权原则[⑦]。盖耶则持有不同主张,认为康德的公共法权观念得以证成的基本前提在于保障和提升根本的自由价值,唯有在此基础上公共权威才具有正当性和与合法性,他同时对康德的分析性命题和公设概念做出了有别于瑞普斯坦的阐释,认为两者的客观现实性均需要进一步推证,从而才能明晰康德一系列法权(普遍法权原则、私人法权和公共法权)公设所蕴含的道德和理论指向[⑧];奥妮尔则从阐释康德源初契约(Original Contract)观念出发,强调公共法权得以确立的规范性诉求的模态性质而非基于假定的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从而明晰康德与传统社会契约论者的重大差异[⑨];瑞雷则赋予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在康德确立公共法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与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相比)康德作为最为充分的社会契约论者的重要思想特质[⑩];马尔霍兰则坚持认为康德归属于自然法阵营而非社会契约论者,进而强调康德整个政治哲学建构乃是奠基于道德责任观念之上,公共权威不过是人们道德责任的保障体系,这也构成康德公共法权观念的根本特质[11]。
因此,厘清相关问题不仅对于呈现公共法权观念的康德式证成路径至关重要,而且也能够有助于对康德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把握和理解,进而回应相关批评和诘难。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康德不同时期的思想文本,首先阐释公设概念的理论和实践指向,并在呈现自然状态下所有权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阐明公共法权得以确立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关注其中蕴含的基于公共承认的道德责任、全体性的立法意志和公共自律的价值旨趣,进而以更鲜明的规范性道德视角为政治证成的康德式进路辩护。在我们看来,基于源初契约理念和全面意志构建法权状态,进而以合法的权威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及其所有权,乃是康德公共法权观念得以确立的根本价值基础,也是公共正义得以可能的前提性条件,正如康德所言,“法权状态乃是人的相互关系,其中包含唯一能使每个人享有其权利的条件;而基于一个为每个人确定法则的意志的理念使得这种权利享有得以可能的形式性条件,称为公共正义(öffentliche Gerechtigkeit)”[12]。
一、公设、先天综合命题及其推证
我们先澄清康德公设概念的基本内涵。在《逻辑学讲义》中,“公设是一个实践的、直接确定的命题,或者是规定一个可能行动的原理,对于这个可能行动来说,前提条件为:实施它的方式是直接确定的”[13]。在阐释公共法权公设之前,康德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其它两个公设:一是基于外在自由公理引出的普遍法权原则公设[14],从而加于每个人的外在自由行动以责任要求,尽管这一行动规则并非如伦理行为那样乃是为了责任这一动机而得到践行,但是无论法权义务还是伦理义务,都是对自由价值的保护和提升[15];二是为了论证私有法权(获得性法权)而引出的实践理性的公设,亦即“实践理性的一个先天预设:把我的任性的每个对象都当作在客观上可能的我的或你的某物来看待和对待”[16],康德又把这一公设称之为实践理性的许可性法则,这一公设表明每个人均有资格或能力去占有外在对象并有权迫使其他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而为证成理知占有并最终确证所有权概念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康德认为,与私人法权状况相比,公共法权公设并未添加更多的人类义务或质料性内容,而仅仅是提供了新的法权形式,亦即公共正义法则[17]。
综合康德给出的三个公设,我们不难发现三者之间侧重点及其价值指向上的差异。普遍法权原则公设主要从总体上确证外在自由行动的合法性,以及行动各方应当承担的法权义务;实践理性公设关注的是外在自由行动以及占有概念得以确立的理知前提,强调的是一种道德人格能力,从而为外在获得或所有权的推证奠定基础;而公共法权公设更为关注公共权威(国家)得以确立的合法性前提,以及进入公共法权状态并履行政治责任要求的正当性。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三个公设之间实际上也是互为前提、彼此支撑的关系,共同构成康德法权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枢纽,普遍法权原则公设乃是确证人性内在法权的充分条件,而实践理性公设和公共法权公设则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权、契约关系和国家制度建构。归根到底,公共法权公设确立的根本价值基础依然是对于普遍自由这一人性根本法权的保障,这一价值基础也是外在自由公理的体现,更是康德法权论得以确立的根本旨趣,正如他指出的,“法权乃是使一个人的任性得以与他人的任性基于普遍自由法则相联合的条件的总和”[18]。
简而言之,康德诸多法权公设的总体意图在于确立履行法权义务并保障平等自由价值以及衍生的所有权的合法性条件,而这些条件唯有得到正当性证成,才能具有加于每个人身上并强制人们履行的权威性,这也吻合康德关于法权概念的最初界定,基于外在自由的公理(每个人均有独立于他人任性的自由)以及不矛盾律,运用权威的力量阻止对自由的阻碍就是正当的,在此意义上,法权就与运用强制的合法性权威紧密相关,只要此强制性乃是立足于普遍法则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正如康德所言,严格的(狭义的)法权乃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基于与每个人的自由共存的普遍法则而运用外在强制是可能的”[19],换言之,根据普遍法则来限制每个人的任性并使之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相一致的强制力是正当的,在此意义上,“法权与运用强制的权限是同一个意思”[20]。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康德指出,基于外在自由的公理和不矛盾律,普遍法权法则乃是“无法给出进一步证明的公设”[21],并且同样断言公共法权公设可以从法权概念中“分析性地”得到阐明,但是正如盖耶所言,康德法权学说的三重公设概念及其分析性说明无一例外均需要进一步推证进而呈现其规范前提。在他看来,康德的公设概念具有道德和理论双重面向,亦即“源于基于绝对自由价值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运用的最高道德原则”[22]。换言之,康德法权义务观念发端于其先前《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确立的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均是为了保障和提升每个人的自由价值。在留存的课程笔记(1793年)中,康德再次声称其着力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主旨是“基于法则规范的人类自由意志的使用”,而“基于自由法则的行动的必要性构成义务”。 [23]在此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内涵伦理义务(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两大组成部分。
具体到上述三个公设,康德并非仅仅给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断言,而是源于更为根本的道德法则概念并应用于关于外在自由行动,亦即通过实践理性能力确立法权原则,进而给出每个人的自由行动与其他任何人的自由行动并行不悖的规范性条件。在此意义上,与费希特的观点相反,康德的法权学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前的道德论证,亦即先行确立无条件的自由价值以及具有普遍立法能力的道德自律人格理想[24]。
这也吻合康德在与《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同时期发表的《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中论断,“为了从一种法权形而上学(它抽去了一切经验条件)达到一个政治原则(它把这些概念应用于经验场合),并且凭借这个原则达到依照普遍法权原则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哲学家将给出:(1)一个公理,亦即一个确定无疑的命题,它直接源自外在法权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与所有人的自由基于普遍法则契合一致);(2)一个公设(亦即作为基于平等原则所有人联合的意志的外在公共法则的公设,没有平等也就不会有每个人的自由);(3)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得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中还按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保持协调(亦即凭借代议制)”[25]。从中不难发现,康德关于公共法权的公设可以从法权概念中分析性地导出的论断,实际上需要进一步探询并呈现其中蕴含的根本价值指向,亦即通过确立公共法则来进一步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这一外在法权的公理性设定。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需要探询如何确立公共法权法则来为政治制度的建构奠基,进而保障每个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法权。
这也是康德在《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行不通》中强调的公共法权得以确立的先天价值原理,并且更为明确地指出公共法权和外在自由法则的相互关联及其蕴含的价值关切,“既然一切法权只是基于普遍法则条件来限制其他人的自由与我的自由共同存在,而(一个共同体中的)公共法权只是符合这一原则并与强制相结合的现实立法的条件,由此人们才在一种一般法权状态中作为臣民而归属于一个民族,也就是说,人们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而互相限制任性的相互作用上的平等状态(亦称为公民状态),因此就强制每一个其他人的权限(使其自由的运用与我的自由的运用相契合的界限之内)而言,每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生而具有的法权(亦即先于任何法权行为的法权)就是彻底平等的”[26]。
康德公设概念的意旨其实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得到阐明。如果说法权公设的理论和价值意图在于确立保障平等自由的普遍法则条件的话,那么对于理论哲学而言,康德确立“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的意图在于,经由模态诸原理表明关于经验对象的判断(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如何与认识能力相联结的条件,亦即“客体(连同它的一切规定)与知性及其经验性的运用,与经验性的判断力,以及与理性(在它应用于经验上时)处在怎样的关系中”[27]。康德同时指出,公设抑或模态概念并非无需辩护和推证,而是“如果在一物的概念上先天综合地加上一个规定,那么就必须赶紧对这样一个命题即使不是添加一个证明、也至少是添加一个对它加以主张的合法性的演绎”[28]。关于此公设的演绎,实际上也是对主体认识能力及其经验性运用的前提条件(合法性)的探究。
经验性思维公设的推证,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乃是为信仰留出了地盘,从而为后来道德哲学公设(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确立了价值前提,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中心任务。虽然先天的自由观念作为公设乃是先行给定的,不过当同时具有理知能力和感官偏好的行动者在运用其实践自由时,如何通过其道德人格力量履行道德法则(义务),则是一个并非不证自明的综合命题,因为理性存在者不可能始终必然地遵循普遍性的道德法则[29]。在此意义上,先验自由理念作为公设需要进一步确证,唯有通过理性行动者的纯然实践理性(普遍立法的意志)确立行动法则,进而才能够保障实践自由得到确证并生发出道德价值,正如康德所言,“自由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法则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而一切其他的、作为一些单纯理念在思辨理性中始终没有支撑的概念(上帝和不朽),现在就与这个概念相联结,同它一起并通过它而得到了持存及其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个理念通过道德法则而揭示出来”[30]。与理论哲学中引入公设概念的意图在于揭示一种全新的知性能力相对应,康德实践哲学的诸公设同样乃是为了阐明实践理性这一道德立法能力和人格力量,进而使得自由理念能够基于普遍法则这一前提条件得到最终证成。作为公设的自由概念经过系列推证而与道德法则(定言命令)、道德义务、目的王国和自律等观念相互契合,呈现出具有突破性的道德价值取向,这也是罗尔斯与伍德所分外关注的具有“自尊与互尊”的康德式伦理意向[31]。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康德的公设概念确立的意图在于探明公共法权得以证成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康德所言的“这一公设的理据可以从关于外在关系的法权(相对于暴力)概念分析性地加以阐明”?从字面上看,康德关于公共法权的公设似乎可以直接导源于法权概念亦即外在自由的公理,并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推证或演绎,而这显然不是康德的理论初衷。在给出这一论断之后,康德紧接着详尽阐明了其中蕴含的更为深渊的价值旨趣:一方面,所谓分析性地阐明主要意旨该论断并非基于经验性的事态或行为来证成具有强制性的法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真的经历了惨痛的暴力伤害这一事实才明白加于每个人强制性法则的重要性,而是基于先天的理念就能够确知,先于法权状态,无论个体、民众还是国家都将无法避免彼此不法或暴力的伤害;另一方面,唯有走出仅仅依附于个体自身判断的自然状态并与其他所有人进入公共法权状态,才能获得经由公共法权承认的有保障的每个人的权利[32]。
实际上,《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部分的一个重大课题亦是难点便是对公共法权的合法性权威进行推证,而根据法权概念可以分析性地阐明这一公设仅仅是对其合理性最为初始的呈现,更为艰难的任务在于:公共法权观念作为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33]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止步于分析性概念的字面含义,而是需要越出经验性占有的界限,进一步呈现康德公共法权公设理论在维护和保障所有权[34]问题上的客观必要性(实在性)。
在为《道德形而上学》写作而做准备的草稿中[35],康德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破解该难题的思想路径。在其中康德表明,基于分析的原理,每个人的自由的外在运用能够与任何人的自由共存,无论运用自由去做什么;不过,无论何人的自由任性一旦需要通过普遍法则而限制他人同样任性行动的行使,则是一个综合原理[36]。也就是说,在限制(强制)他人的自由任性进而行使某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意义上,包括涉及获得物品、履行契约以及处理家庭共同体中的法权问题时,均需要通过加于各方以法权义务才能真正确证所有权,这也就需要给出通过法则限制各方任性的理据,而寻找这一理据正是表征了公共法权的推证过程。而在康德看来,唯有确立公共法权状态,法权义务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来源,而这一能够加于各方限制条件的权威只能存在于与该自由法则相一致的综合性的共同意志之中[37]。
所以正如盖耶所言,尽管基于分析判断的定义,谓词包含于概念之中,但是并不意味着该判断(命题)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成。当康德指出分析判断(或分析命题)依据形式逻辑为真的时候,并没有给出其客观有效性的断言,更不能由此推断该命题不能经由根本的源泉推导出来。无论在《纯粹理性批判》还是随后的著作中,康德一直主张,如果不去证明相关概念和判断的“客观有效性”,那么即使是分析判断也无认识论价值。换句话说,即便是严格的分析命题也必须以先天综合为前提,即使该命题有着恰当的定义并且给出了一个分析证明,但是这样的证明并无真理性,除非对该定义的建构被证成,因此需要对其客观实在性进行严格推证。与此相关,当康德给出若干实践理性或法权公设时,也并不能由此推断该公设是无需推证的断言,而是需要经由根本道德原则及其义务性要求确证其客观实在性[38]。
同样,公共法权的公设可以分析性地从法权概念中引申出来,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该法权公设进行推证进而证成其正当性。任何公设都着眼于一定的目的要求,并且围绕具体的目的进行相应的条件设定。当我们基于保护和促进每个人所具有的平等自由价值出发证成道德法则(定言命令),并且应用于外在自由行动时,法权概念也就得到了根本价值上的确证,在此价值前提下,公共法权的公设才能够进一步基于法权概念、外在自由的公理、普遍法权原则以及实践理性的公设获得其根本价值诉求,而唯有进入公共法权状态才能真正确保每个人所享有的普遍自由价值,亦即对每个人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性法权(私人所有权)做出更进一步保障和确证。归根到底,唯有在法权状态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的权威保障并实现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这一根本目的。
同时,这一推证的根本性质乃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它们所探询的乃是权利得以确立的合法性前提而非占有得以产生的事实问题[39]。在此意义上,马尔霍兰认为,“关于法权的公设既表明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表明以道德义务为前提的综合性的理论命题”[40]。也就是说,尽管康德表明一系列法权公设可以分析性地得出,但是其内涵指向并非自明地体现于外在自由公理和生而具有的人性法权,而是呈现为先天综合命题,需要给出道德和理论的双重推证,康德在其笔记与手稿中也时有提及,“法权乃是相互性的人格关系,意指一个人的自由通过基于普遍性的法则条件相契合的任性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如果(行动的)对象外在于我的话,这一限制依赖于一个综合的自由法则:如果是内在于我,则是分析的”[41]。由此康德试图表明,当每个人的外在自由行动与其他人的自由行动基于普遍法则相契合时,这是一个分析性的论断,而当一个人外在自由行动需要通过普遍自由法则加于别人的自由行动以限制时,亦即一旦涉及到确证某人关于外在物的所有权时,或者基于外在自由行动产生所有权冲突时,则将扩展人所生而具有的权利概念或内在自由范畴,进而关涉如何经由先天综合性的获得性法权和公共法权原则来规范每个人的外在自由行动,也唯有提供相关获得性法权和公共法权的推证,才能最终确定每个人必须承担的法权责任[42]。
于是,康德法权学说关注的是,如何经由先天综合性的普遍意志确立法权法则,进而规范特殊的任性行为在涉及物品使用上产生的权利。而关于公共法权观念康德式推证的难点和核心环节在于:自然状态下缺乏合法的公共权威,从而无法保障各方具有恒久性、确定性的所有权,唯有联合意志才具有普遍立法功能并经由确立公共法权才拥有合法的强制权限,由此能够加于每个人对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行动基于公共承认基础上的相互责任或法权义务,这是本文接下来要呈现的内容。
二、自然状态:困境与出路
如前所述,康德法权学说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是证成一个既有强制力又有合法性的权威,而所谓合法性,乃是能够确立能够保障平等自由及其衍生权利的普遍法权规则。康德把这种吻合合法性强制规则的状态看做法权状态或公民状态,这也为后来的国家制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判断准绳和理念指引[43]。而康德之所以不断强调人们必须离开自然状态而进入法权或公民状态这一法权公设,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在于自然状态下缺乏能够保障所有权的基本法权法则,进而也就无法实现最大化自由价值这一人类理想,甚至沦为无政府状态、专制主义或野蛮状态,进而不断走向强制与自由契合一致的共和主义理想[44],这也是康德为何把法权体系划分为自然法权(私人法权)和公民法权(公共法权)而非自然法与社会法权的缘由所在。在康德看来,主要关注固有法权的自然法观念一旦涉及到关于物的所有权争端时,其与社会法权一样,依然缺失能够确证所有权的最终合法机制,从而始终处于围绕所有权问题展开的纷争或冲突中[45]。具体来说,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权利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是,单边的任性行为不具有公共权威资格,因而无法确保相互性的法权责任,进而无法在权利产生分歧时有合法的强制力进行裁决。而这也引出康德法权学说至关重要的论断:唯有先天联合的意志而非单边的意志才能确立普遍性法权规范,以此才能产生约束不同人格之间的相互性责任亦即法权义务,也唯有在此状态下才能保障基于法则的普遍自由。正如康德所言, “就一个外在的因而偶然的占有而言,单方面的意志不能形成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强制性法则,如此将会损害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所以,唯有一种促使每个人处于责任要求之下、因此是普遍的(共同的)并且有强制力的意志,才能够向每个人提供保障”[46]。单边的意志无法确定合法的强制力并迫使人们承担相应责任,而唯有公共法权状态(公民状态)才能够实现立法意志、普遍法则、强制力与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的协调起来。换言之,一旦发生关于外在物所有权上的纷争,唯有迫使每个人进入法权状态才是解决争端的基本条件[47],康德又把这种最终赋权(laid down as right)的公共正义法庭作为公共法权状态得以确立的根本表征[48]。
这也是为何康德把公共法权状态称作分配正义的状态的缘由,缺少公共裁决机制,纷争必将演化为暴力,尽管对此自然状态我们并非一定要亲身体验或通过经验去证实,每个人也有权基于法则强制要求他人进入该状态。在一个无法状态下,尽管每个人依据自由任性来行使权利,如果他们之间相互攻击似乎并非不法,因为根本无法可依,也无法裁断并分别对错,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但是在此状态下“每个人都无法面对暴行来确保‘他的’,这却是在最高程度上行不法”[49],因为这消解了法权的任何效力而把一切交给了野蛮的暴力,而在康德看来,无法的自由乃是世界上“最为恶劣之事”[50]。在《走向永久和平》一书中,康德依据此法权概念来建构世界主义层面上的国际联盟,通过合法的强制性法则消除国家间的战争状态亦即野蛮的、无法的自由状态[51]。这同样是其在《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中讨论国际法权时强调的基本立场:自然的自由亦即无法的自由状态乃是一种持续的战争状态[52]。
所以,在自然状态可能导致战争和暴力这一结果来看,康德大体认同霍布斯的基本判断,而同时也与霍布斯一样,主张走出自然状态并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权威来保障相关合乎自然法的协约得到执行[53]。不过康德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远离了霍布斯的思想路径:
(1)具有强制力权限的来源。康德主张,合法的强制力只能源于保障普遍自由的法权原则,因而这一原则只能经由联合的意志的自我立法才能得到确立。而对于霍布斯而言,权威源于全体臣民缺乏相应的手段来保障其安全和福祉,因此出于慎思理性而把一切权利让渡给主权国家[54]。所以正如瑞雷所言,在霍布斯那里,政治合法性乃是源于意愿性的同意,这也是一些协定的本质,在此意义上,霍布斯缺乏康德式的纯然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具有法则能力的意志行动概念,从而也就消解了政治责任以及其它道德观念[55]。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国家乃是基于人性基本事实(比如保全自身)而得以确立,离开自然状态乃是一种意愿行为;而康德则强调的走出自然状态乃是基于法权规则的必然性价值取向,这是康德早在176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的理论关节点[56]。
(2)确立强制的根本价值取向。康德与卢梭共同主张,强力或国家权威乃是以保障普遍自由互为依归,“强迫自由”乃是康德与卢梭共享的基本价值理念,其意图在于以合法的自由代替野蛮的放任状态[57]。也就是说,进入法权状态“所放弃的无非是野蛮的、无法的自由,以便在一种法则的依附性中,亦即在一个法权状态中一点不少地重新获得自己一般而言的自由,因为这种依附性产生自他自己的立法意志”[58]。而在霍布斯那里,基于保障和平和安全等福祉来证成公共权威所具有的无限强制力,很可能最终以消解每个人所具有的平等自由为代价。在康德看来,霍布斯式的安康与幸福“在自然状态中或者甚至在一种专制政府下也许能够有更适意、更如愿的结果”[59]。所以在专门回应霍布斯的论著中康德指出,“最先应该考虑的公共福祉乃是合法的宪政,由此基于法则保障的每个人的自由”[60],这也是康德分外强调的基于联合的意志以及原初契约观念确立法则所蕴含的道德价值[61]。
二是,尽管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所有权,比如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性权利,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具有暂时性特征而无法得到最终确证。尽管在自然状态下,依据实践理性的公设(许可性法则),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属于他的所有物,但是这种对物的所有权仅仅基于经验性的、有形的占有行为,虽然这一获得是一种真实的权利事态,但是假使没有共同意志确立法则进而使得私人占有得到法权的恒久保障,则我们对外在物只是暂时性地获得,因此,“唯有在公民状态中才使一切获得成为最终的获得”[62]。也因此,康德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基于其人性尊严而拥有自由、自主这一自然法权或源初法权,另一方面则超出传统自然法的思想视域,提出获得性法权及其确证问题[63],这也是后来他花很大力气加以阐明的理知占有概念。
理知占有的核心要素乃是基于联合的意志确立法权原则而实现的真正占有,即使占有的对象是某个物,但是康德依然把人与物的关系(占有的感性条件)抽离出来,强调先天联合的意志确立法权法则所要解决的是不同人格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基于人格关系法则而得到确认[64]。康德进一步强调,唯有经由联合的意志确立的法权原则才具有权威性,在此意义上,卢梭的“公意”学说带有更为强烈的“综合性”特质,也就是说,联合的意志(公意)所确立的法权原则乃是人们主张所有权时不可回避的必然义务[65],也因此才能真正实现对物的所有权,亦即从暂时性拥有到最终占有。
这也正如爱丽丝所揭示的,康德关于暂时性法权的论证,与“最低限度的契约主义者”(Minimalist Contractarians) 存在根本差异,后者把把私有财产作为契约执行者在前政治状态下进行博弈时应该先行考虑的因素,在此意义上,在确立政制之前,所有权已然构成特定人格的基本要素,而走出自然状态、基于同意建立政治社会或政府的根本缘由乃是保障每个人先行具有的所有权。康德思想进路与此相反,在自然状态下,所有权仅仅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和次要地位,只能通过进入法权状态(公民社会)才能得到最终确证[66]。在讨论国际法权时,康德也同样强调,自然状态(战争状态)下国家间采取武力扩张的方式获得权势只具有暂时性,无法保障国际关系处于持续和平状态,唯有进入法权状态(建立普遍的国际联盟),不同国家才能最终且真正享有和平及其所带来的成果,这同样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应当[67]。
瑞普斯坦在阐释自然状态的缺失时,基于康德的法权概念可以“分析性”地得出进入公共法权状态这一公设这一论断,认为公共法权状态的证成乃是基于先天的而非经验的前提。在我们看来,这并不完全吻合康德的原意。在康德那里,进入法权状态固然是先天的实践理性要求和义务,是一种“道德应当”,但是该道德命令并非建立在一个空洞的概念演绎基础之上,而是具有很明显的现实内涵。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如果不经验性地先行具有暂时性的获得性权利,各方也就没有任何动力加入公共法权状态(建构公民宪政和国家),因为他们不会产生权利的纷争,也不担心会失去什么。正如康德所言:“因而必须假定先于公民宪政(或者不考虑它)的属于我的和你的外在物是可能的”[68]。 正是由于这一每个人都先在的对于外在物的共属于你的和我的这一权利前提,才进一步使得基于法权的制度建构成为必要。这也是康德在讨论源初获得的诸要素时,强调并区分对外在对象的占领(Apprehension)、标明(Bezeichnung/declaration)和归己(Zueignung/appropriatio)的意图所在[69]。在此意义上,对于一片土地的身体上的占有亦即持有已经是一种物权,尽管对该行为还没有做出所有权上的确证并使其获得其客观现实性[70]。
另一方面,康德明确指出,公共法权状态与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诉求实际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诉求在根本上也是正当的,只是两者提供的确证该诉求的形式存在重大差异,而唯有在法权状态下各方通过合法的强制才能最终确证所有权。所以康德一方面指出进入法权状态不可能就此剥夺了先天的自然法权[71];另一方面强调,“如果人们在进入公民状态之前,根本不愿意认定任何获得是合法的,连暂时性认定都不愿意,那么公民状态本身便是不可能的。因为依据形式而言,在自然状态中关于所有物的法律所包含的,正是在公民状态中的相关法则所规定的同样的事情(就公民状态仅依据纯粹理性概念而被设想而言);只是在公民状态中,使这些法律得以执行(根据分配正义)的条件被提出来。因为,如果在自然状态中,一种外在的所有权连暂时存在均不可得,那么也不会有任何关于这种所有物的法权义务,因而也不会有任何要求人们脱离这种状态的命令”[72]。
所以,在康德那里,暂时性的法权乃是证成公共法权的经验性的前提,若无此前提条件,则所确立的公共性条件将是空洞无物的。据此,凯尔斯汀的观点并不贴切,在他看来,康德的自然状态学说并不关涉人类学意义上人之生活状况,因而是一个思想实验,“其旨在提供证据,证明有关与生俱来的自由权以及有关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理性法原则根本上不足以和平地解决潜在出现的冲突,也不足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法权上的安全”[73]。实际上,康德曾多次指认,其公共法权得以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和战争所导致的危机,由此才使得确立公共法权并使人们享有权利不仅具有规范性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正如其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提出的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立场,正是意图强调确立公共法权的人类学前提,“大自然迫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仅就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而言”[74]。不难看出,康德对于人性的虚荣、权力欲和贪婪甚至野蛮的一面有着深刻的洞察,甚至感叹“造成人类的那么曲折的材料里,是凿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的”[75],进而认为放弃野蛮的自由(盲目的偶然性)实现合法的自由(公共法权状态)乃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艰难的课题。
所以我们更为认同伯德和赫鲁施卡的论断,“对于康德的法权学说而言,所有权获得和拥有是最为重要的,这也是进入法权状态的根本理由,理念中的国家由此具有模态的意涵”[76]。这也正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特别强调并论证的“概念无直观则空”的基本理念在法权领域中的体现,这也是康德式先验推证的思想特质所在[77]。瑞普斯坦据此认为,康德关于所有权的证成模式与其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篇的思想路径相近[78]。不过在我们看来, “先验分析”篇最多相应于法权学说中的“经验性”占有及其有限性的论断,因为其中需要感性直观(经验性)要素,但是却无法契合康德的“理智占有”观念,后者只能是在实践理性框架内才能得到清晰阐明,亦即通过实践理性确立自由法则才能最终确证占有及其合法性。从而对于康德法权学说而言,实践理性的证成模式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也是实践理性公设得以确立的根本理论和实践意图所在,其根本理论旨趣在于以实践理性的理念亦即确立基于法则的普遍自由作为确证所有权的根本规范性要求,“实践理性通过其法权法则所要求于我的是:不是根据感性条件来运用‘我的’或‘你的’到外在物上,而是撇开这些条件,因为这涉及根据自由法则对任性的一种规定,这也就要求我如此这般来思考关于物的占有,因为唯有一个知性概念才能被归摄在法权概念之下”[79]。
综合以上论证,在康德看来,之所以需要进入法权状态,根本缘由在于,自然状态下我们无法通过正当的权力机制来裁决权利上的争议和冲突,而此悬而未决的权利争议将使得每个人的外在自由无法得到根本性保障。同时在自然状态下,解决相关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各方个体权力的多寡,从而导致不正义。换句话说,在自然状态下,我们无法拥有合法化的法权强制力[80],在此意义上,强迫每个人都进入法权状态,乃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的需要,这是法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公共法权可以“分析性地加以阐明”的内涵指向,由此也衍伸出来基于法权的契约和外在获得原则。脱离此状态,我们只能暂时性地对某物拥有所有权却无法得到持久的保障,因为不存在一个正当的公共权力来最终确证该权利。
进一步,唯有基于联合的意志确立公共法权原则进而建构公民社会,才能有相应的权威加于所有人应当承担相关于每个人所有权的责任和义务。或者说,唯有在此公共法权状态下,各方对于外在物的所有权主张才能基于法权原则受到的限制,并在相互承认并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得到最终确证,而这也是破解所有权问题上一切争端的规范性前提[81]。因此康德指出,“这一命题‘某人必须离开自然状态’意指某人能够迫使每个人与我们或我们所属的共同体一起进入‘公民状态’”[82]。在维吉兰特乌斯所做的康德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课程笔记中,康德借助罗马法学家乌尔皮安关于法权的一般分类,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自然状态的缺失以及进入法权状态的必然性,他指出,自然状态下,个体对其所有权的只能依据其自身的力量或私人意志,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公共正义体制来获得并保障各自的所有权,因此这就需要普遍法权规范以及交往正义原则,同时,只有在法权状态下,才能对违反法权的任何人做出最终的裁决或判定,这也必然要求基于分配正义原则的公共正义法庭,在此理性法庭面前,“使你自身服从于公共司法体制,或者服从于基于公共法则所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状态中”[83]。
三、进入法权状态:公共承认、相互责任与联合的意志
与瑞普斯坦等人强调法权状态所具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最终确定性特质不同[84],在此我们更为关注康德提出进入法权状态的要求所蕴含的具有强制约束性的责任/义务指向。进入公共法权状态(公民状态、公民宪政)乃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这是康德证成公共法权的重要思想创造。不同于单纯的依据强力及其达至的福利(共同善)来说明公共法权的充分必要性,康德强调主张法权的各方首先考虑的是应该承担基于公共承认的相互责任,所谓公共承认的基础在于要求各方经由联合的意志而非单边的意图确立公共法权原则,该原则也是构成公民状态的前提条件,也由此才能保障/确证每个人与其它所有人一样享有平等自由价值。
因此,经由公共承认理念,康德最终实现了平等自由、道德责任和普遍立法意志的紧密契合,这也正是作为纯粹理性的源初契约观念的根本价值旨趣,而这同时也与其先前提出的道德自律理念相互印证。所以正如康德所言,“既然一切法权都仅仅在于将每个他人的自由限制在能够与我的自由按照一个普遍法则共存的条件下;而公共法权(在一个共同体中)仅仅是一种符合这个原则并且与强力相结合的现实的立法状态,由此所有属于人民的人都作为臣民处在一种一般而言的法权状态之中,亦即处在一种根据普遍自由法则相互限制的任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相等的状态中(这就叫做公民状态),因此每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中的固有法权(先于任何法权行为的法权),就其有权强制每一个其他人使之始终停留在其自由的运用与我的自由相协调而言,是一律平等的”[85]。
而这也就引出康德所有权主张的另一个重大关键点,那就是所有权问题的实质并非是人与物的关系,在根本上乃是不同人格之间的关系与相互责任的确证。公共法权作为规范性前提,其目的并非为了解决特殊性的人对于物的权利主张(康德称之为感性状态下的占有)并以此达至个体或总体福利的最大化,而是对于权利各方责任义务的约束和确证,这种约束和确证并非剥夺每个人对于外在物的所有权,而是更好地保障所有人基于法权状态而非基于个体偏好的所有权诉求。所以,寻求所有权(获得性法权)的正当性前提问题实质上就转变为探询如何处理不同人格关系的规范性基础问题[86]。
康德表明,当我宣称对于某物的所有权时,也就把他人置于一种不能剥夺我对该物的权利的责任要求之中,而如果没有一种公共法权原则来维护我的主张,则他人也不会承认我对该物的所有权并履行不侵犯我的所有权的责任[87]。康德随即指出,当我如此要求别人所应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也必须反过来基于同样的公共法权原则承担对于别人的所有权的责任,正如其在《奠基》中把道德义务表征为对于普遍法则的尊重和履行,如此基于内在自由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88],以及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再次强调尊重道德法则的义务动机作为崇高的人格理想[89],在此法权学说语境中,康德把我们应当承担的相互性责任同样表征为对于普遍法权原则的遵循和法权关系的确证,尽管遵循此原则并非必然要求内在的义务动机[90]。
换句话说,我对于他人的所有权的承认的一个基本前提依然是存在一个普遍法权原则,由此才能要求他人也同样不侵犯我的所有权。责任的相互性乃是法权原则所具有的普遍性特质的重要价值缘起,在此基础上才能确证彼此对于外在物的所有权。瑞普斯坦据此认为,康德式的法权责任观念阐释优于洛克/黑格尔式的思想路径[91]。在同意这一论断之余,我们还试图强调另一个关键点,亦即与洛克和黑格尔式思想路径相比,康德式的公共法权及其相关的政治责任论证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方案[92]。弗里克舒通过比较康德与洛克的理论,认为洛克主要关注的人与外在物的关系,以及一种经验获得意义上的单边行动(投入一定量的劳动),而非康德式的基于三重关系的所有权论证进路,亦即关于外在物的主体间关系,由此康德也更为关注基于法权的责任观念[93]。爱丽丝持有相近的论点,认为“对于康德而言,所有权的可能性意味着有必要确定一个条件,在其中能够普遍践行尊重彼此自律的相互性责任”[94]。而马里克斯则以此区分在所有权论证上的两种思想进路: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私人生产”(Private Production)路径;二是康德所主张的“公共承认”(Public Recognition)路径[95]。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走出自然状态是一种法权义务,但是康德所界定的法权义务的目的取向有其特殊性。这在他对胡弗兰德的自然法观点的评论中做出了明确说明。胡弗兰德持有沃尔夫式的思想进路,亦即立足于完善论的立场进行伦理探究和相关责任的界定。在他看来,履行法权责任的根本意图在于寻求每个人自身的完善这一伦理责任,这也是通过威权运用强力来捍卫法权得以执行的理据。尽管康德赞赏胡弗兰德所作的努力,但是不满其基于寻求完善这一伦理责任来推证法权的思想进路,认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个体权利无法得到平等保障。所以胡佛兰德混淆了法权的恰当基础与完善论的伦理诉求,相对,康德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基于何种前提条件我能够运用强制力而不与普遍法权原则相冲突”[96],唯有在公民状态中才会提供相关法权确证,亦即在承认一方法权的同时始终加于另一方以相关责任要求。由此,康德公共法权学说蕴含着特别的责任性目的取向,那就是通过要求每个人履行契合于普遍法则的法权义务来实现每个人的外在自由权利,这也是康德具有鲜明规范性特质的政治责任理念,正如其所言:“一切公共法权的终极目的乃是一种状态,唯有在其中每个人才能够最终拥有其所得”[97]。
于是,康德与费希特的法权观念在出发点上存在诸多偏离,尽管康德同样强调法权概念所包含的强制特征以及共同意志在确立公共法权中的作用,但是康德并不会认可费希特关于“(强制力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的效用性”[98]的论断,康德更为强调基于公共承认的法权规范加于权利各方的道德义务,在此意义上,法权规范乃是经由具有主体间性且能够普遍立法的联合意志得以确立,这构成了政治义务和法权的强制力特质的基础性前提,而对这一前提的忽视可能是导致费希特走向完善论而非康德式自由主义的关键思想缘起[99]。不过,许多学者并未认真对待康德学说中蕴含的这一主体间性理论指向,在处理相关课题是更多援引费希特和黑格尔而非康德[100]。
奥妮尔强调康德公共法权观念得以建构的模态性质而非假定的社会契约论,其理论意图也在于此。在她看来,康德的公共法权并非基于假定的同意得以确立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模态特质,体现了经由纯然实践理性理念确立定言命令的规范性道德诉求,最终导向基于一定历史发展条件的共和政制理想。据此,她不认同瑞雷关于康德是“最充分的社会契约论者”的论断,认为康德其实“放弃了实际的或假定的契约或同意类型的社会契约观念,而是把它单纯看作非社会性却彼此关联的理性存在者普遍同意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构建必要条件”[101]。这与康德的文本相互印证,“这个民族籍以将自己建构成一个国家的行动根本只是国家的理念,而唯有根据这个理念,国家的合法性才能被设想;这便是源初契约” [102] 。也就是说,具有立法能力的共同意志(亦即普遍立法的意志)基于纯然理性或源初契约理念确立公共法权法则,吻合此法权理念的制度建构才具有合法性,进而能够通过相关体制设计并实践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地位与功能,以此保障普遍自由价值的实现[103]。瑞雷虽然与奥妮尔在康德的社会契约论观点的界定上存在差异,但是同样强调康德源初契约理论对于公共权威的确立所具有的规范价值诉求[104]。这也吻合康德的基本价值理念:集体意志(Gesammtwillen)乃是任何公共契约的最终基石[105]。
因此,康德式的社会契约观念的根本意图在于确立评判政治权威(统治者)和体制(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标准,因而是一种规范性的理性理念。该理念一方面依据正当性的法权法则来赋予主权者使用强制的权限,另一方面又强调唯一的、最高的立法者只能源自联合的意志确立的源初契约。由此,立法者、主权者和普遍联合的意志互为表里,共同成为构建可辩护的公共法权法则的基本源泉,康德由此认定,“经由一定的行为一群人成为一个民族,经由该联合已经构成一个主权权力,人们进而通过法则转加于其他人(以强制力)。因为契约乃是法则并且已经预设了立法权”[106]。也在此意义上康德才说主权(人民联合意志)权力既是普遍的、不可逾越的,也是不受限制的且不会做不义之事。源初契约及其含有的联合意志作为纯然理性的理念,之所以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实在性和基础性地位,主要在于它是以普遍法则之下的自由精神为旨归,各方也有道德责任构造契合此价值理念的政制形式,而若现存的制度形态无法一蹴而就实现此价值理想,则各方也有责任通过持续的改良,不断使之与共和主义的法权理想相契合[107]。
基于共同意志确立源初契约的人民的联合,由此基于普遍法则确证并分享彼此固有的以及获得性法权,这不仅是公共法权的根本价值旨趣,同时也成为康德法对家长制和专制主义的基本缘由。专制主义把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个不受限制的单个人,也就为其依据自己的任性和偏好行事埋下伏笔,进而将会侵犯他人的意愿或外在自由行动。所以康德非常注重法权原则所具有的普遍性、相互性和全体性特质,这些特质彰显了法权原则所要保障和维护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平等自由权利这一更为深层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价值。或者说,康德法权意义上的责任概念虽然有别于伦理义务(比如在《德性论》部分所阐释的作为义务性的目的),但是两者的源初性价值前提实际上是切近的,亦即均是通过具有交互性特质的义务体系来保障和确证所有人的平等自由,这也是康德法权学说蕴含的根本的价值旨趣,也是与家长制和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108]。
由于共同意志和人民的联合乃是为了分享根本法权基础上的普遍自由,因而源初契约理念也同时与完善论的权力观相对立,前者源于合法性的、可辩护的理性理念,而后者则基于国家的繁盛;前者的根本意图在于确立一个理性的法庭,进而评判现实的和理想的国家政制,而后者则意图追寻一种事态和福祉[109]。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断言康德对于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一方面,康德法权论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法权原则的初始根据,另一方面,康德把最大程度的普遍自由看做公共法权或国家建构甚至整个人类的最高福祉。无论是法权得以证成的基本方式还是价值取向看,康德式的政治证成路径都与功利主义的国家权力观大相径庭,这在康德发表的一系列历史哲学著作中有同样鲜明的体现,在其中,康德把确立基于公共法权的国家联盟和世界主义联合体作为可能的普遍世界历史目的,由此抑制战争并走向永久和平[110]。
康德从而指出,“一部按照使每个人的自由可以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那些法则的有关人的最大自由(而不是最大幸福,因为后者已经可以自行推出)的宪法,却至少是一个必要的理念,我们不仅在最初拟定一部国家宪法时,而且甚至在一切法律那里,都必须把这个理念作为基础”[111]。康德的意旨在于,唯有基于正当性法规的保障,每个人才可以自由寻求无论何种样式的幸福生活图景。当然,他也曾指出,尽管宪政基本原则并非依据公民的幸福而是权利得以建构,但是全体人民的福祉依然是保障其法权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们应该给予穷苦阶层更多的关照,修建学校并教育好儿童[112]。在此意义上,基于联合的意志所建立的公民社会和国家,也就有正当权力比如通过税收、建立基金会等方式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为人民谋取福祉同时也是对其基本人格尊严权利的保护[113]。
所以,归根到底并非个体的幸福而是公共正义乃是康德法权的根本切入点。在此意义上康德指出,公共法权所确立的基本规范并非立足于全体人的实际同意,亦非建基于臣民的福祉,而是基于理性的理念的源初契约。这一理性理念表达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确定的事态,亦即确立评判政治正当性的基本价值尺度[114]。正是基于这一纯然实践理性的视角,康德彰显了公共法权状态得以确立的道德人格力量,而每个人所具有的普遍立法意志以及由此形成的联合的意志,乃是确立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法权,也是确证其合法性的根本道德基础,康德称之为“任何契合于法权的公共法则的拱顶石”[115]。
不难看出,康德的源初契约理论与卢梭更为切近而与格劳修斯和普芬道夫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存在更多差异。卢梭的基本关切乃是缘于联合的意志确立保障人们根本价值的正当性的主权权威,所谓正当性的基准在于公意的“目的和本质上是公正的:它必须来自全体,才能适用于全体。如果它倾向于某个个别的和特定的目的的话,它就会失去它天然的公正性”[116]。正如罗尔斯指出的,所谓“来自于全体”,其意旨在于公共意志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所有人都应该追寻普遍目的和最高善,由此确立的法则也才能保证公平性进而“适用于全体”,因为基于平等的自由这一根本价值,每个人才能在公共法则的约束下去追寻各自的合理性善[117]。卢梭的意图在于,公共意志所确立的社会契约乃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根本利益而建立具有合法性和公共性的道德人格(国家),或者依据斯瑞尼瓦桑的解读,卢梭的公意概念意指作为契约式构建起来的道德联合体,在其中,个体的慎思受制于一定的限制条件[118]。
无论从发生源泉和价值取向上来说,我们都可以断定,卢梭的公共意志学说都成为康德法权学说的重要思想缘起,这可以从康德自1760年代阅读卢梭的著作留下的诸多笔记、草稿和反思性片断中得到印证,对卢梭思想的理解也成为康德实践哲学诸多基本概念(比如善良意志、共同意志等)的思想缘起[119]。在其中,康德明确表明,经由对卢梭的阅读,使他“学会了尊重人”并且致力于“确立人性的法权”这一价值目标[120]。而实现此目标的重要思想理路也是出于卢梭,那就是唯有从公共性亦即普遍意志的视角来呈现人所具有的基于道德法则的自由价值,这也成为康德后来构建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石[121]。康德的相关论断所指的正是此价值向度:“卢梭以综合的方式并以自然人为出发点;而我则以分析的方式并以文明人为出发点”[122]。以文明人为出发点的分析的方式,核心的任务乃是确证法权(包含公共法权)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化和良序社会的前提条件,而这是需要进行系列推证的异常繁复的工作[123],呈现其中蕴含的规范性道德诉求乃是重要一环。
康德随后的一系列法权哲学笔记也表明其受卢梭的广泛影响,诸如强调法权乃是基于所有个人的意志而非功利而得到规定,法权义务所表征的乃是基于外在法则的自由,舍此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将无法持存,这也为确立源初契约进而构建国家法权奠定价值基础,康德在其中也广泛涉及到主权、刑罚、国际联盟以及战争等论题[124]。
经由汲取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念,康德逐渐远离传统的自然法学派。与格劳修斯和普芬道夫相比,康德并不主张存在一个历史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形态(初始共同体)以及初始占有的自然法原则,认为这是一种虚构的思想进路[125],而是强调唯有确立公共法权法则才能确证所有权的最终归属问题,源初契约表达正是一种逻辑先在性的理性法规理念,这也是其理知占有观念所要破解的难题。也因此,康德式的源初共同体表征的并非财产权的共同占有,而是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基于联合意志确立法则的基本规范性价值理念诉求,这也是规定所有权最终得到确证的根本前提[126]。
需要注意的是,康德所言的“源初契约”观念与“自然状态”或“原初状态”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伯德和赫鲁施卡在其《评注》中谈及康德与霍布斯、普芬道夫以及阿亨瓦尔等人在自然状态和公民社会的理解上的差异,其中特别强调康德把对市民社会(区别于法权状态)的讨论与人的行动能力联结起来,并且通过公共立法理性、公共市场的参与者以及公共法庭的裁决者确立公共正义进而超越自然状态或私人法权状态的重要地位[127]。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源初自然法权(固有法权)与其提出的原初的或初始的自然状态观点并不契合,换句话说,源初自然法权(固有法权)只能基于法权状态才能得到最终确证,而并非存在于(原初)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权利,在此意义上自然状态并非讨论自然权利的恰当场所,这不仅是康德与阿亨瓦尔的区别,也是康德与格劳修斯或普芬道夫等人自然法观念的重大差异所在。吴彦先生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差,特别是其把原初状态、自然状态和法权状态分别对应于保护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并非是对康德法权学说的恰当理解[128]。因为康德曾明确指出原初状态(status originarius)和偶然状态(status adventitius)均归于自然状态[129]。同时伯德和赫鲁施卡不仅模糊了相关观点,也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康德法权状态三个向度的相互联结[130],相比之下,瑞普斯坦则看到了固有法权与公共法权观点的相互支撑关系[131]。
公共法权状态正是表征了意志的普遍立法能力及其合法性权威,由此才能通过合法性的强制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基于普遍法则相互共存,而所有权正是外在自由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为何需要从法权概念过渡到私人所有权,进而唯有通过确立公共法权状态才能最终确证每个人所享有的法权的客观实在性。这也吻合康德关于法权概念的基本界定:法权所欲表达的正是与普遍自由法则相一致的交互强制的可能性[132]。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确立正当的、可辩护的公共正义的法庭。
在康德看来,唯有联合的意志才能确立公共正义(分配正义)的法庭,在此法庭面前各方给出各自可辩护的理由,而最终的判定和裁决由该法庭实施。他认为,“在一个法庭面前什么是正当的,亦即根据法权确定什么是正当的”[133],乃是澄清法权概念的重大课题。在“法权论”的第41节,康德进一步强调确立着眼于分配正义(区别于保护性正义、交互性正义)的法庭的重要性[134],其意图表明,唯有先行确立公共正义法庭,各方才能按照法权规范确定各自的权利主张,这也是康德遵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皮安关于法权划分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所表明的内涵所在[135]。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乌尔皮安法权观的修正也正表明其与自然法学派的差异所在[136]。也唯有在公共正义(以及分配正义)的法庭下,原先的公共法权公设才最终具有了客观实在性亦即必然性[137],这也是康德特别强调“据于法权” (Rechtens)而非仅仅关注“自在的法权”(recht)和“合法的”(rechtlich)的根本缘由[138]。这也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外强调的确立裁决争端的理性法庭的具象化,从而达到基于法治的和平状态,在其中“把我们的自由只限制在他能够与每个别人的自由相共存、并正因此而能与共同的利益相共存的范围内”[139]。
结语:作为道德人格理想的公共自律
弗里克舒借助康德关于“任性”和“意志”的区分,认为自律主要关涉内在自由以及行动法则的确立,归属于伦理法则,而公共法权则关乎外在自由且通过普遍联合的意志(General United Will)加以确立,在此意义上“普遍联合的意志基于先天的法权确立法则,这些法则并非自律式(Non-Autonomously)订立的且每个公民均服从的自由法则”[140]。我们不同意这一论断,而是认为弗里克舒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康德《奠基》中的自律概念,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普遍性和公共性思想旨趣。换句话说,康德的法权观念和道德法则共同源自于具有规范意义的纯粹实践理性理念。这也是康德多次强调的“积极自由”观念,亦即“纯粹理性自身即是实践的能力”[141],康德又称之为立法意志能力,亦即确立自由的(实践的)法则能力。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公共法权观念与其定言命令公式紧密契合[142]。
在我们看来,这以具有普遍性立法能力的联合意志(公共自律)正是在康德政治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一个关键要素,舍此观念也就难以理解康德法权观念的根本价值旨趣,亦即唯有通过普遍立法意志确立普遍法权原则,才能保障每个人和其他所有人所享有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一切平等自由权利;同时,这一立法意志及其确立的公共法权,也是每个人都应当承担的尊重他人所有权的道德责任。于是法权语境中的共同意志与康德先前阐明的普遍立法意志在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在《奠基》中,康德分外强调理性存在者能够按照确立普遍法则的意志理念而行动[143],在我们看来,这一自律的道德人格理想成为证成定言命令的根本价值前提。同样,在其法权学说中,源初契约或理性理念所欲表征的正是共同意志所具有的普遍立法能力,公共法权也唯有通过此公共自律的道德人格力量才能获得其客观实在性。这也正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知性概念先验演绎”环节,康德通过阐释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能力(我思)来确证关于经验对象知识的客观实在性,所以“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的客观条件”[144],唯此自我意识才具有客观的而非主观的统一性。当然,这种知性能力所欲寻求的乃是自然必然性,而法权语境中的公共自律能力则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
奥妮尔通过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理性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对康德自律概念的公共性向度和道德规范内涵作了精彩呈现,从而回应当代自律概念的偏狭和缺失[145]。格瑞格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论证康德的法权观念得以确立的道德规范基础,并认为“基于康德道德自律这一基本概念,联合的意志的存在仅是为了使得法权法则成为道德法则或纯粹实践理性原则得以确立的条件”[146]。
也就是说,康德法权学说与其伦理学说共享这一根本性的道德自律观念,这也是康德分外强调的普遍联合意志在确立所有权和公共法权中的地位的缘由所在,可以说,自律乃是康德公共法权观念得以确立的一个核心要素。实际上,康德公共法权得以证成的三个核心要素(道德责任、立法意志和平等自由)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公共自律的价值取向,这也是理解其政治证成的重大关节点,正如康德在谈及基于法权法则而得以建构的国家权威时指出的,“国家经由三种不同的强制力(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而拥有其自律,也就是说,基于自由的法则而形成并保持自身”[147],康德把这种契合自由法则的状态看做我们应当趋向且是理性(经由“定言命令”)加于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于马尔霍兰的看法,在他看来,康德的普遍意志(联合的意志)赖以奠基的是自然意志观念,“这种自然意志就是为了意志联合成为共同意志,而假定所有人格具有的理性意志的基础”[148],也就是说,自然意志以及由此确立的自然法在政治证成中具有更基础性的地位,马尔霍兰进一步认定康德更切近于自然法理论家而非以同意论者或社会契约论者,他也在无形中忽略了康德源初契约理念与普遍意志的深刻关联性,特别是康德式的契约理念所蕴含的公共自律特质和相互性责任内涵,这与传统社会契约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亦并非能够归入自然法阵营。康德在1792年底给好友埃尔哈特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自然法理论家常常主张,公民社会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可欲性基础之上,但是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非正义状态。由此,进入公民社会状态乃是一项法权义务”[149]。
我们因此也与伯德的观点存在差异,在他看来,康德占有理论主要基于“许可性法则”这一实践理性公设,而并不需要于社会性的赞同和承认[150]。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具有规范性的联合的意志及其普遍立法能力,所表征的正是基于公共承认的相互性道德责任,也是造成一个合乎法权的社会或共同体所必需的价值基础,这正是伯德和赫鲁施卡所阐明的“规范赋予能力”的关键所指[151]。
以此观之,黑格尔对康德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康德明确反对基于个体意志和私人利益确立社会契约,亦非着眼于现实的真实的同意来构建公共法权,而是基于联合的、共同的意志来确立保障全体自由价值这一源初契约,一切现实的政治和权威也必须以此先天的法权理念来反观自身的合法性[152]。实际上,康德与黑格尔关于占有和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观念并非截然对立,黑格尔也同样把所有权问题看做“无时间性的、根本性的自由关系”[153],并且强调对物的占有的单个人意志唯有得到承认才构成所有权[154]。这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法权责任乃是康德共同意志和源初契约观念的重要价值内涵,由此,进入法权状态、承担法权义务才成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应当”。
柏恩斯虽然认同康德的法权学说在政治证成问题上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亦即以具有实践理性的自由平等的道德存在者的人格理想作为证成和评判政治制度的规范基础,进而与传统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相比,呈现了平等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价值关切,但是他同时认为,康德的基于严格区分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的思想模式导致其政治理论建构产生了一系列困境,具体体现为意志与任性、正当与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等一系列二元划分,他进而认为,“如果人们希望保有康德作为法权原则规范基础的非工具性的实践理性观念这一见解,就需要解决一旦我们否弃康德的形而上学前提对公共和私人领域如何做出区分”[155]。而在他看来,罗尔斯特别是哈贝马斯以交互主体性观念更好地克服了康德批判理论的缺失[156]。
我们认为,康德共同意志及其蕴含的相互责任理念可以很好回应相关疑难,成为走出对康德实践哲学二元对立理解误区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公共证成的康德式进路为理解道德自律与公共自律的关联性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方案[157]。基于共同意志确立公共承认的正义法庭,乃是为了表达作为纯粹理性理念的源初契约观念,在此意义上,康德法权哲学语境中的联合的意志、源初契约、纯然理性和相互性责任等观念具有共通的思想内涵,共同表征具有公共立法能力的道德自律理想。正如伍德所言,依此理想确立的公共法权,才能够成为评判政制(国家权力及其行使、特定的法律或体制安排等)合法性的根本准绳[158]。这种观念论政治证成路径也成为破解所有权难题的钥匙,进而使之区别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思想路径,同时也使得康德式理路在应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困境时依然具有启发性,比如在处理国家与个体自由关系时,康德式理路警醒我们,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全体自由为依归,而勿以此威权谋取少数人的特权和私利,从而造成社会等级差异,这是康德法权学说包含的平等自由观念的根本体现,也是该思想进路的独特价值所在[159]。
[①] Immanuel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07, pp. 451-452. 主要参照剑桥英文版《康德全集》,并同时给出德文科学院标准版《康德全集》卷数和页码以及英文版页码。译文参考了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张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康德:《道德底形上学》,李明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该书第一部分(导论和前16节)于1796年3月出版,第二部分(17-21节)和两个附录于1797年9月出版。
[③] 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文集》,第2卷,梁志学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10-311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255页。另参见该书第71节、75节、81节讨论所有权和契约时关于共同意志的论断,主旨在于说明卢梭与康德式的普遍意志依然与特殊意志(个别意志)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中。
[⑤]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1-227.
[⑥]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Samuel Freema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0.
[⑦] 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5-181, 355-388.
[⑧] Paul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in Mark Timmons (ed.),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 pp. 23–64.
[⑨] Onora O'Neill, Constructing Authorities: Reason, 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s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70-185.
[⑩] Patrick Riley, Wil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 Hobbes, Locke, Rousseau, Kant, and Heg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5-162.
[11] Leslie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8-281, 308-310.
[1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06, p. 450. 同参阅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1, p. 455; 8:383, pp. 348-349.
[13] 康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14]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1, p. 388.
[15] 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法权义务与伦理义务共享基本的规范性前提,相关论证参见拙文:《法则与自由:康德定言命令公式的规范性阐释》,《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16]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46, p. 406.
[1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06, p. 451.
[1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0, p. 387.
[1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2, p. 389.
[2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2, p. 389.
[2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1, p. 388.
[22] Paul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p. 64.
[23] Immanuel Kant, “Vigilantius’s lecture notes”, Lectures on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480-481, pp. 251-253.
处i'chu莦﷽﷽﷽﷽﷽﷽﷽﷽﷽﷽﷽﷽﷽.
处i'chu莦﷽﷽﷽﷽﷽﷽﷽﷽﷽﷽﷽﷽﷽.
[24] 我们曾基于“融贯论”的解读方式,论证康德法权学说及其蕴含的强制性特征直接源于普遍性的道德命令和人自身即是目的这一价值旨趣,进而回应“分离论”观点。参见拙文:《强制与自由:康德法权学说的道德证成》,《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2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429, p. 614.
[26]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2-293, p. 293. 译文参照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7-198页,稍有改动。
[2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A219/B266,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2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A233/B286,第210-211页。
[2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4:440, p. 89.
[3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5:3-4, p. 139.
[31] 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99, p. 256. Allen W. Wood, Kantian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4.
[3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07-308, p. 452; 6:312, p. 455-456. 阿伦特在其关于政治哲学讲稿中,试图呈现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判断力”官能所蕴含的政治哲学向度,亦即强调通过公开性、共通性和可交流性这一人的社会属性在保障自由价值上的重要作用,进而表明达成任何判断均需要反思两个基本理念:一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原初协定”的理念以及由此推导出的人性观念;二是“合目的性”的理念。参见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贝纳尔编,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33] 康德在论证私人法权时,指出基于经验性占有的法权命题是“分析的”,而他试图确证的乃是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占有的所有权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命题”。相关论述参见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49-250, pp. 403-404。
[34] 康德的所有权(私人法权)概念包含对物、对人以及对人格性的物三重指向,不过其法权学说对物的所有权证成着墨最多、内涵最为丰富。
[35] 这份草稿大约210页,篇幅仅次于康德为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的草稿和《遗著》,其中法权学说占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收录于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第23卷,参见Immanuel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246-359, pp. 233-341.
[36]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3:296, p. 298.
[3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9, p. 420.
[38] Paul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pp. 23–64.
[39] 这也是康德在进行纯粹知性概念的推证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立场,在其中他也以法权隐喻表明先验演绎的根本特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4/B117,第79-80页。
[40] Leslie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p. 245.
[41]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3:273, pp. 277-278.
[42]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3:295-300, pp. 297-301.
[43]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04, p. 37.
[44] 参见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4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8, p. 394; 6:242, p. 397.
[46]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6, p. 409.同参见6:264, p. 416.
[4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6, p. 451.
[4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97, p. 443.
[4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07-308, pp. 452.
[50]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7:1320, p. 82. 同参见该书15:644, p. 9; 19:180, p. 17; 19:243, p. 18; 19:476, p. 87; 27:1338, p. 104; 27:1382, p. 164.
[5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356-357, p. 328.
[5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43, p. 482.
[53]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7:1382, p. 164. 同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752/B780。
[54]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4-105页。
[55] Patrick Riley, Wil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 Hobbes, Locke, Rousseau, Kant, and Hegel, pp. 142-143.
[56] Immanuel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100, p. 419.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康德写信给友人预告其已经着手写作道德形而上学基本原则,甚至在1768年给赫尔德的心中提及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应该会在年底完工。参见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74, p. 94。
[57]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
[5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6, p. 459.
[5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8, p. 461.
[6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8, p. 297.
[6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4-295, p. 294-295.
[6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4, p. 416.
[63]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7-238, pp. 393-394.
[64]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8, p. 419.
[6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9, p. 420.
[66] Elisabeth Ellis, Provisional Politics: Kantian Arguments in Policy Contex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0-64. 相反的论证参见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6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50, p. 487.
[6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6-257, p. 410.
[6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8-259, pp. 411-412.
[7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1, p. 405.
[7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6, p. 409.
[7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2, p. 456.
[73] Wolfgang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Immanuel Kants Rechts- und Staatsphilosophie, Paderborn: Mentis, 2007, S. 258. 同参见Wolfgang Kersting, Politics, freedom, and order: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Paul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55-356.
[74] Immanuel Kant,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20, p. 111. 同参见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2-313, pp. 455-456.
[75] Kant,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 8:23, p. 113.
[76] B. 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60.
[77] 参见Jill Vance Buroker,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3-135.
[78] 参见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pp. 373-88.
[7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3, p. 407.
[8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2, p. 456.
[8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5-256, p. 409; 6:267, p. 418.
[82]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303, p. 36.
[83] Immanuel Kant, “Vigilantius’s lecture notes”, Lectures on Ethics, 27:528, p. 289. 同参见 “Mrongovius’s lecture notes”, Lectures on Ethics, 27:631-633, pp. 246-248; “Collins’s lecture notes”, Lectures on Ethics, 27:280-282, pp. 74-76.
处i'chu莦﷽﷽﷽﷽﷽﷽﷽﷽﷽﷽﷽﷽﷽.
处i'chu莦﷽﷽﷽﷽﷽﷽﷽﷽﷽﷽﷽﷽﷽.
[84] 参见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pp. 145-181.
[8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2-293, p. 293.
[86]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8, p. 419.
[8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5-256, p. 409.
[8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4:400, p. 55.
[8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5:86-88, pp. 209-211.
[90]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5-256, p. 409.
[91] 参见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pp. 149-150.
[92] 邓正来先生认为,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架构的阐释存在两种方案: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参见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见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120页。我们讨论过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变革,亦即从市民社会批判和人类解放的视野给出关于人类社会的新观念路径(参见拙文:《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解读》,《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实际上,康德关于公共法权的论证思路对于理清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显然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为此需要另文加以阐发。
[93] Katrin Flikschuh, Kant and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8.
[94] Elisabeth Ellis,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A New Look at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3), 2006, p. 545.
[95] Reidar Maliks, Kant’s Politics in Con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3.
[96]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127-130, pp. 115-117.
[9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41, p. 481.
[98] 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文集》,第2卷,第416页。
[99] 相关阐释参见Gunnar Beck, Fichte and Kant on Freedom, Rights, and Law,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129-184.
[100] 参见Allen Woo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Studies on Freedom, Right, and Ethics in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Kenneth Baynes, The Normative Grounds of Social Critic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韦尔默试图呈现康德式伦理学的对话维度,参见韦尔默:《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罗亚玲、应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101] Onora O'Neill, Constructing Authorities: Reason, 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s Philosophy, p. 185.
[10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5, p. 459.
[103] 参见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7, p. 296; 8:311, p. 307; 6:291, p. 438.
[104] Patrick Riley, Wil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 Hobbes, Locke, Rousseau, Kant, and Hegel, pp. 125, 162.
[10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42, p. 481.
[106]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11, p. 39.
[10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40, p. 480.
[10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0-291, pp. 291-292.
[109]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04, p. 37.
[110] 参见Kant,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 8:27-28, pp. 116-11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357, p. 328.
[11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A316/B373,第272页。
[112] 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60, p. 50.
[113]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25-328, pp. 468-470.
[114] 参见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03, p. 36; 19:504, p. 37.
[11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7, p. 297.
[116]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5页。
[117] 参见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9-248.
[118] Gospal Streenvasan, “What Is the General Will”, in Thom Brooks(ed.), Rousseau and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 2005, pp. 3-39.
[119] 这些关于实践哲学的笔记、草稿和反思性片断大约写自1764年,直至1790年代康德写作《道德形而上学》时期。
[120]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2:216-217, p. 7.
[121]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2:243-252, pp. 15-21.
[122]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p. 3.
[123] 早在1765年底给兰波特的信中,康德就已表明手头已经累积了许多材料且准备发表关于“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系列短论(参见Kant, Correspondence, 10:56, p. 82)。不过,直至20年后(即1786年)康德才完成第一部分的工作,而后一部分的工作规划几经变更,待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已历经30年了。相关研究文献参见Manfred Kueh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deferral”, in Lara Denis(ed.),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9-27.
[124] 参见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pp. 14-72.
[12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1, p. 405.
[126] 参见Robert B. Pippin, “Mine and thine? The Kantian state”, In Paul Guy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and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16-446.
[127] 参见B. 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pp. 33,44-51.
[128] 参见吴彦:《法、自由与强制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0-236、293页。
[129] 参见Kant, Lectures and Draft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27:1338, p. 105. 同参见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50, 251, 258.
[130] 参见B. 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p. 51.
[131] 参见Arthur Ripste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p. 176-181.
[132]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1-232, pp. 388-389.
[133]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97, p. 375.
[134]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08, p. 450.
[135]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37, p. 392-393.
[136] Kant, Lectures on Ethics, 27:280-282, pp. 74-76; 27:526-528, pp. 288-289; 27:631-633, pp. 246-24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27, pp. 392-393.
[137] 参见B. 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pp. 67-69.
[138]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67, p. 418; 6:306, p. 450; 6:297, p. 443.
[13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752/B780。
[140] Katrin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in Lara Denis (ed.), Kant’s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p. 59.
[141]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14, p. 375.
[142] 参见Allen D.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0-81.
[143]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4:421, p. 73.
[14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8。
[145] Onora O'Neill, Constructing Authorities: Reason, 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s Philosophy, pp. 103-150.
[146] Mary J. Gregor, Laws of Freedom: A Study of Kant’s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Metaphysics der Sitte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p. 63.
[147]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318, p. 461.
[148] Leslie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p. 279.
[149] Kant, Correspondence, 11:399, p. 448.
[150] B. Sharon Byrd, Intelligible possession of objects of choice, in Lara Denis (ed.)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pp. 93-110.
[151] B. Sharon Byrd, Joachim Hruschka,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Commentary, pp. 103-106. 需要注意的是,该书依据形式性与实质性界定公共法权的不同面向并不严谨,特别是其中认为康德公共法权具有实证法向度存在诸多偏差,相关论述参见该书第1章“法权状态与公共法权公设的理念”。康德的法权学说与自然法具有更多亲缘性,强调的是先天的具有强制特质的合法性要求,进而规范每个人的任性行动(参见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6:224, p. 379).
[152] 关于黑格尔对卢梭“公意”观念的误解以及康德对卢梭思想的承接,参见邓晓芒:《从黑格尔的一个误解看卢梭的“公意”》,《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黄裕生:《论意志与法则——卢梭与康德在道德领域的突破》,《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153] Hegel, 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First Philosophy of Right, Peter C. Hodgson (trans. and e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2.
[15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59页。
[155] Kenneth Baynes, The Normative Grounds of Social Critic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47.
[156] 在此无法充分回应伯恩斯的论断,特别是其中关于康德自律观念的公共性内涵揭示,及其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慎议民主等观念的比较。基于康德的规范性立场批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公共理性概念的缺失,参见Onora O'Neill, Constructing Authorities: Reason, Pol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s Philosophy, pp. 137-150.
[157] 参见Oliver Sensen(ed.), Kant on Moral Aut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8] Allen Wood,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rman Idealism, Matthew C. Altman(ed.) ,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76.
[159]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8:290-297, pp. 292-296; 6:316-317, p. 460; 6:323-325, pp. 466-468. 同参见Allen Woo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Studies on Freedom, Right, and Ethics in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pp. 11-12. Allen D. Rosen, Kant’s Theory of Justice, pp. 15-39.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