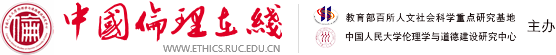朱贻庭:“伦理”与“道德”之辨
摘要: 长期以来,伦理学界将“伦理”与“道德”视为“相近相通”,并“互相替用”。然史实并非如此。在古希腊“伦理”与“道德”就有区别,黑格尔更将两者“严格分开”;在中国古代,早有“伦理”(“人伦”)与“道德”这两个用词。“伦理”是既亲亲又尊尊的客观人际“关系”,“道德”是由“伦理”关系所规定的角色个体的义务,并通过修养内化为德性。
作者简介: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近一年多来,我再一次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研究做了回顾与总结,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六对范畴做了梳理,集成一本小书——《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这本小书出版后,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范畴,何为“伦理”?它与“道德”究竟是何关系?首先要声明,这个问题不是我首先发现的,我只是后知后觉者。①如果说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对于总结古典中国伦理学和再写中国伦理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也许只有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从学理的层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和道德的特点,我们才能把握中国传统道德的真实状况和固有特点,才能逻辑地梳理出属于中国传统伦理学自己的一套概念话语系统。也只有辨清“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才能为论述“天人之辨”、“心性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辨”等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问题提供逻辑的和经验的根据。现实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阐明“‘伦理’与‘道德’之辨”,也就找准了中国伦理学的对象,因而也是再写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伦理’与‘道德’之辨”是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个理论范式。
一、“伦理”与“道德”是两个内涵有别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们的伦理学教科书都将“道德”(morality)与“伦理”(ethics)这两个用词,视为“相近相通,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互相替用”,似乎无须作出区别。因而一般都提“道德”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其一般的论述模式是,由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直接推出“道德”,而不讲“伦理”这个重要的环节。这可能是受了前苏联“伦理学”教科书的影响。然而,至少对于中国来说,不重视“伦理”这个本属于中国伦理学的范畴及其与“道德”的关系,就会从起点上陷入前苏联伦理学所固有的研究模式,后来建构的有些教科书虽掺入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还是未能跳出固有的“模式”,从而丧失了中国伦理学本有的特点,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一句话,缺乏“家园感”。我以为这是长期以来我们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说得直白一点,不讲“伦理”,所谓“道德”就失去了“承担者和基础”。
其实,在古希腊,“伦理”与“道德”两词还是有区别的。我请教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陈村富教授,他认为:古希腊也是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古希腊是先有ethos这个名词,意为“符合人伦关系的习俗”。由部落联盟发展到城邦后,研究治理城邦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政治学”;而研究城邦之自由民即公民应符合城邦人伦的学问叫伦理学(ethica)。另有希腊文arete,相当于中文“善”、“好”。凡“物”、“动物”、“人”尽其本性,发挥最好的功能,就叫“其对象应有的arete”。对人而言,就是“有德”,“有品位”。作为公民,在待人接物之方方面面的具体规范就叫“德性伦理”,“道德规范”。但到了古罗马思想家、希腊文拉丁化的代表西塞罗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用拉丁文mos(意为习惯,习俗)译希腊文ethos,同时又用mos的复数第一格mores译“德性伦理”,“道德规范”。于是“伦理”与“道德”就被后人等同使用了。这种情况的产生,自有西塞罗的责任,也有语言形式方面的原因。因为古典拉丁文的名词有五种变格法,近代西方语言深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影响,所以出现了ethics与morality两个混用的英语词汇。二者之关系就成了一个学术问题。
此后,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将“道德”与“伦理”做了区别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黑格尔。正如贺麟先生所指出:“把道德与伦理严格分开,这是黑格尔伦理思想的特色。”②不过,将“道德”与“伦理”做概念上的“分开”,并不妨碍两者在现实中的统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自由”的“客观精神”发展过程归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在“抽象法”阶段,人的“自由”只是外在的、抽象的;在“道德”阶段,人才取得了自身的内在精神,才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即具有了对自由的自我意识,但这时的人的主体性“自由”还不是现实的,因而必须进入到“伦理”阶段。黑格尔认为,法和道德单就本身来说是没有现实性的,它们“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才具有现实性。就是说,作为主观的内心自由意志的道德,既须以伦理为自身客观内容,又在客观伦理关系中成为现实的。所以“伦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现实的“实体”。在黑格尔那里,“伦理”作为“实体”,体现为三种形态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道德”正是在“伦理”实体中才获得了现实性的存在。恩格斯指出:“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③它反映了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诚如高兆明教授所转述——“伦理是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秩序,而道德是主观精神操守,不是主观精神决定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秩序,而是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秩序决定道德(主观精神)的内容”④。黑格尔关于“伦理”与“道德”的思辨,与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伦理”和“道德”不仅思维形式有别,而且在内容上也不尽相同。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实体的三种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是宗法性的,社会又是“家国一体”,没有所谓“市民社会”。但他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及其统一的思辨,对于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的“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早在黑格尔前2000多年,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有了“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而正是“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及其统一体现了古典中国伦理学的特点。我认为,区别这两个概念用词及其关系,对于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认识“伦理”与“道德”既区别又统一,是破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切入点。而要再写中国伦理学,明确中国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必须将这两个概念用词区别开来。
二、中国古代“伦理”与“道德”关系的内涵和特点
在中国古代,“伦理”实际上是建基于“礼”这一宗法等级制的人际关系及其秩序之上的。孟子首提“人伦”,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孔子的弟子子路称“长幼之节”、“君臣之义”为人之“大伦”。“伦”和“理”连用,首出《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⑤汉初贾谊在《新书》中又做了明确的表述:“祧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⑥《说文》释“伦”,一曰“同类之次”;一曰“辈也”。同类之有次序,有辈分之不同,辈分次序就是一种秩序,其中就有“理”在,因而“人伦”也曰“伦理”。结合上述儒家所言,所谓“人伦”或“伦理”,就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关系及其秩序。一般来说,“伦理”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秩序。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关系”有其特殊的内容:一是指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以及朋友之间具有双向义务的关系,也就是双方各以对对方的义务而成为“伦理”关系。所谓“慈”、“孝”,“良”、“恭”,“仁”、“忠”,“惠”、“顺”,“信”等则是诸种双向义务的规范形式;二是指这种双向义务关系的构成以亲情、友情为纽带和基础,所谓“君臣”关系则是“父子”关系的延伸。《孝经》有言: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也”,“故以孝事君则忠”⑦;第三,除了“朋友”一伦,其他以亲情为纽带的关系都不是平等的,而是有上下尊卑等差的,体现了传统“伦理”既亲亲又尊尊的宗法等级性特点。由此可见,“伦理”作为一种“关系”的实体存在,不是任意的、“拉郎配”式的。没有血缘亲情关系就不构成家庭伦理,没有友情关系就不构成朋友伦理。但在中国古代,虽有血缘亲情关系,如没有上下、尊卑之别,也不构成“伦理”关系。传统“伦理”的这种结构,其实就是“礼”。所以春秋时齐大夫晏婴直言:“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很明显,“人伦”或“伦理”也就是“礼”。“伦理”是“礼”的实体内涵,“礼”是“伦理”的制度形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礼”制,是以宗法性的家庭或家族为基础的一种等级制度,而正是这样一种“礼”制型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和秩序,即所谓“人伦”或曰“伦理”。对此,儒家学派首创体系化“礼论”的荀子就有明确的论述。在荀子那里,“礼”就是指“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⑧,它是“正国”之制。他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⑨其作用之奥秘就在于型定了“人伦”。他在说到“礼”与“人伦”的关系时说:“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⑩也就是所谓“礼以定伦”(11)。“礼”等级制度型定了并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上下、亲疏、远近的人伦关系,规定了维护这种等级人伦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伦理”秩序——“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12),即所谓“五伦”“十义”。而这一“五伦”“十义”的“伦理”秩序正是中国传统“礼制”的实体内涵。据此,我借用梁漱溟先生的用语,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以“伦理本位”为社会结构的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
“伦理本位”是梁漱溟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概括。然细看梁氏《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他对“伦理本位”之“伦理”的界定,本人不尽苟同。梁氏否定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因而他不同意如陈独秀所认为的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13),因为在梁氏看来,“只有宗法社会可说是家族本位”。他明确认为:“我们应当说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他解释“伦理”说:“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逐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所以中国之“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所谓“伦理”,就是“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因而在梁氏看来,“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14)。这是对“伦理”关系的一种狭义的理解,抹杀了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有等级差别和等级对立的一面,显然有悖于基于宗法等级制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们还是认同“伦理本位”这一用语。为了区别于梁氏的“伦理”和“伦理本位”之说,作者特以“宗法伦理”和“宗法伦理本位”来表述自己的观点。
我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之“伦理本位”的“伦理”,首先是指具有宗法性的“家庭”、“家族”,由之而延伸为一个等级有分的社会关系及其秩序,借用黑格尔的话也就是一个“伦理实体”。但与黑格尔的家庭“伦理实体”不同(当然也不同于梁漱溟所界定的“伦理”)。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伦理实体”是宗法性的,是既亲亲又尊尊的人伦关系及其秩序。而正是这样的“伦理实体”,规定了处于这一宗法伦理实体的各个角色的各种规范形式的道德义务,从而成为宗法“道德”的基础。朱熹注释孔子“志于道”说:“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15)而能行“道”(义务或规范)就是“有德”。黑格尔在谈到“伦理”与“有德”的关系时说:“一个人必须做些什么,应该尽些什么义务,才能成为有德的人,这在伦理性的共同体中是容易谈出的;他只须做他在的环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白的和他熟知的事就行了。”(16)可见,研究中国传统道德,首先要从人际等级关系结构这个“人伦”入手。这里的“人”只是作为“伦理”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独立的、孤立的个人。这就是说,等级有分的人际关系规定了处于不同等级地位的人的角色义务,而行为符合等级角色义务要求的就是“有德”。但这里所说的“有德”是指行为之符合“伦理”所规定的规范要求。而真正之有“德”,还在于得之于“心”。朱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17)。所以“道德”的重点在于“德”——德性、品德。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他说:“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18)有道德或有德,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心中稳定的德性。因而,为了尽自己所应尽的角色义务而有“德”,就应正心、诚意、修身,这才有了道德修养问题,才有道德践履问题。但这里的道德主体不是作为原子式的独立的、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伦理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而有德,因而通过“修身”而达至“身修”,也就能“家齐”;“家齐”而后能“国治”、“天下平”。就是说,伦理角色之“有德”也就稳固了“伦理”关系,稳固了“礼”的社会结构和秩序。
这样,据“伦理”而论“道德”;为有“德”而论心性修养;通过修养心性而“成人”;“成人”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一个“各安其分”、“各得其宜”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伦理由此而“和”,达至古人所梦想的“国泰民安”。而追究到道德哲学的层面上,即为了论证“伦理”的合理性和崇高性,以及论证成就德性即“成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于是就有了“天人合一”、“心性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辨”等道德哲学(19),从而形成了古典中国伦理学的基本的理论进路、理论构架和话语体系。
可见,在古典中国伦理学中,“伦理”一词主要是指称客观的宗法等级“关系”范畴;道德、德性属于“伦理”中角色个体的内在精神。但“道德”离不开“伦理”,不能将道德从伦理关系中抽离出来、孤立起来,否则就搞不清“道德”为何物;作为现实的角色个体来说,也搞不清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是什么。荀子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0)认为只有明白了“礼”(宗法伦理关系),行为角色主体才能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伦理”关系中做一个有道德的“角色”人。犹如董仲舒所言:“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21)在实践上,唯有通过“礼”这一伦理实体才能让个体明白自己所当遵循的“道德”;在学理上说,唯有通过“礼”这一伦理实体才能把握中国古代的“道德”之为何物。而没有了角色个体之“有德”,所谓“伦理实体”也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这表明“伦理”与“道德”的统一性。所谓“伦理实体”,是人际客观关系与个人主观精神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就是宗法等级制度下客观的人伦关系与作为人伦中角色的个人的主观精神的统一。黑格尔指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22)无疑,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原子式的“个人本位”社会,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道德时,就应“从实体性出发”,即从宗法等级的人伦“关系”这一实体性的存在出发。
中国古代语境中“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方面与基于“上帝本位”的宗教伦理和基督教道德有别,一方面又同西方近代基于原子主义的“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伦理和契约道德不同。中国文化突出了“伦理本位”,讲道德不离世俗的人伦实体关系。即朱熹所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也”。只有在宗法等级“人伦”关系中,才能认识道德规范的内涵及其实质——人们在等级角色对应关系中确立了各自的道德义务,如父慈子孝,长惠幼顺。对此,可以称之为“角色道德”。当然,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这个“角色道德”的“角色”是不具个人独立性的“依附人格”,其“道德”是与个人权利相分离的“义务”。
由于“伦理”与“道德”的统一性,因而儒家所提出的“道德”既具有伦理的普遍性又具角色的特殊性。“仁”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在实践中又依据不同语境和在伦理中的“名分”角色展开为多样的实践样式,借用朱熹的话,就是“理一分殊”。而由于伦理实体中等级角色的特殊性,又往往凸出了“仁”的分殊性一面。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如“三纲”,就凸出了“忠”、“孝”、“节”。显然,“仁”是有差等的。所谓“爱人”,当以伦“理”为准,即所谓“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23)。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4)的“恕道”,即所谓“推己及人”,后《大学》称之为“絜矩之道”,同样要服从“伦理”等级关系。朱熹在解释“絜矩之道”时说:“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25)同理,不欲子之不孝于我,则必以此度父之心,而也不敢以此不孝事父,显然不是一条基于人际平等的“底线伦理”。传统伦理学讲道德是为了维护社会人际的等级结构及其伦理关系和秩序,达至各等级的和谐、安定,即所谓“各安其分”,“各得其宜”。朱熹说得明白:“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26)荀子称之为“义分则和”。荀子又说“明分使群”,“明分”就是划分等级名分,也就是“礼”,以此来治理社会各个等级群体,使各等级角色各自遵守自己在“伦理实体”中等级地位的“角色道德”,以维护整个社会的“人伦”秩序,于是社会也就“和”了!所以称“礼”为“群居和一之道”。而一旦人伦关系混乱,道德也就没有了依存和方向;如父子伦理关系混乱甚至颠倒,哪里还有“孝”这个美德的现实存在?
由上可见,在中国古代,“伦理”是宗法等级关系的实体存在,而“道德”是这个“伦理实体”中角色个体的内在德性,是以“伦理”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有“伦理”才有“道德”可言。“伦理”正则“道德”兴,“伦理”乱则“道德”衰。人们常说的“道德失范”,其实正在于“伦理失序”。不讲“伦理”而只讲“道德”,是本末倒置。我同意高兆明教授的观点:“社会成员的道德养成,关键在于建设一种‘好的’现实社会生活及其秩序。”如果一个人际混乱和伦理失序的社会,“不是首先注重客观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建设,而是首先诉诸个体行为,不是首先注重社会精神,而是首先诉诸个体品德,那么,就是本末倒置”(27)。提倡一种以至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如果不明确或根本没有其“承担者和基础”的“伦理”,那就不具现实性,是不可行的,如同虚假的“广告语”一般。
据上论述,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人们一直探索的这样一个问题——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态”究竟是靠什么?我们从分析传统的“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中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就是靠基于稳固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具有结构性的情理交融的稳定的“礼俗”关系,也就是作为社会“本位”的“伦理”的稳固。所谓“族规”、“乡约”就是这种情理交融的“伦理”的制度化体现。唯其这样,所谓“家教”、“家训”、“族规”才能产生实际的作用和起到“化”的效果。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得以长期稳定的文化“密码”。这种情况,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尤其是前六章)中有生动而如实的描述。所以他在小说的开篇就写有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三、再写“中国伦理学”要处理好“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既定的“伦理”秩序从何而来?它是永恒的吗?就中国传统“伦理”而言,古人有自己的回答。一种主流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其宇宙论形态,我称之为“宇宙结构的伦理模式”。由《易经》始发,经董仲舒的“天人合类”论而到宋理学的“天人本一”的“理本论”,认为“人道”来自不变的“天道”,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就是指伦理“三纲”之道。(28)另一种观点由荀子提出。荀子的《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29)前者是“天命论”;后者有合理性,但将“礼”(“伦理”)的产生最终归为“先王”的意志,终未脱“圣人史观”的窠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伦理秩序的产生是经济、政治和文明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古代,由原始氏族而直接进入宗法等级社会,而宗法等级制度实际上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特有的结构。就整个社会而言,如荀子所说:“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30)就一个家庭而言,就是父家长掌握全家的经济大权,即所谓“同居共财”。而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原有的既定的社会“伦理实体”必将随之变革。就其变革的内因而言,在于“伦理”自身的“内在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按照黑格尔的解释,就是存在于伦理实体中的角色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反思批判精神。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会有某些角色个人不满于既定的“伦理”关系而“敢倡乱道”(如明末、明末清初的李贽、黄宗羲等)。黑格尔称这种人为道德“天才”,我称之为道德的“先知先觉”者,或曰“道德先锋”。正是这样一些道德“先知先觉”者和“道德先锋”在外在的社会变革力量推动下,对旧质的既定的“伦理实体”发起了冲击,发动了“道德启蒙”。而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伦理变革”,建构起一种适应新的经济关系的新的“伦理秩序”,从而使个别的新的道德观念普遍化。近代的所谓“道德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伦理”变革。就是说,由“道德革命”而最终构建起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并在新的“伦理”关系中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就是说,变革旧“伦理实体”才能建立起新道德体系。
总之,“伦理”规定了道德;而自由意志的“道德反思精神”又激发了“伦理”的内在否定性,从而冲破旧的“伦理实体”,通过变革实践的批判与继承,建构起新的“伦理”关系和新的道德。这就是“伦理”与“道德”的历史辩证法。可见,今天我们要再写中国伦理学,搞清楚“伦理”和“道德”之关系,应是必不可少的首要议题。也可以说,“‘伦理’与‘道德’之辨”应该成为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个“理论范式”。
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伦理”?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要建立的“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什么才是应该肯定和倡导的可以推进新的“伦理”建构的新的道德和道德观念?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实证的经验和材料进行理论的分析和归纳,将传统“伦理”文化中以“情”为基础的双向义务即情理交融的伦理模式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并在实践中建构为社会所认同的现实与理想相统一的“伦理”,即“‘好的’现实社会生活及其秩序”和新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这是包括伦理学、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十分艰巨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报告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一论断,从伦理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建立已经使得作为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社会基础的宗法等级“伦理实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代之而立的应是适应于“人民民主”的新的“伦理实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然而,“飞跃”后要走的路依然十分艰辛、曲折而漫长。
新中国建立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了新的深刻变革。宪法规定的社会成员的很多个人权利逐步得到了实现。人们的独立、自由、权利意识,以及社会平等、公正的诉求不断增强,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又使得契约关系在人伦关系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这些都为建构新的“伦理”关系提供了许多以往所没有的新的特征,为构建新的“伦理实体”提供了新的条件。然而,毋庸讳言,旧中国原有“伦理实体”所具有的宗法等级特性所造成的“官本”意识、特权意识、宗派主义、“关系”文化、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不良传统,由于“路径依赖”还在时时作祟,败坏着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伦失序、道德失范、腐败成风,社会上出现了焦躁不安的情绪,人们找不到可以安顿心灵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建构怎样的“伦理”关系,进而形成“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德性和德行,成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如怎样构建新的“家庭伦理”、“师生伦理”、“医患伦理”、“企业伦理”、“公共伦理”、“政治伦理”、“网络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还有人类已经面临严峻挑战的“人与智能机器人伦理”。这些都有待于非常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但是贯穿于各种人伦关系,总有一个统帅着整个“伦理实体”的“伦理精神”。这是需要首先厘清的。
近代“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曾明确提出,真正创立“民主共和”,不在于器物变新,也不在于行政制度之改良,其根本之道,是要确立“自由,平等,独立”之“道德政治”。为此,就必须革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就是实现“伦理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1),这是许多先贤的设想。如今,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明确地写上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总结,也是百年探索的珍贵的成果。在我看来,其中“平等”二字是关键所在,也是传统伦理向现代转化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传统伦理的伦理精神是等级之“和”,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那么,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无论是怎样的关系结构,其价值目标也应该是“和”。但这里的“和”不是传统伦理那样的尊卑、贵贱有等的“和”,而是经由“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达至的“和”。其中,人际“平等”又是达致“和”的最为关键的一项。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中国“伦理”的“伦理精神”,与其说是“和”,不如说是“人际平等”。
在中国古代,基于尊卑、贵贱等级的这种“伦理实体”的“和”,在学理上是通过伦理角色双向“义务”而体现的。但由于所谓的君臣、父子的双向义务结构,即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是有上下、尊卑等级差别的,因而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下对上、贱对贵、卑对尊的单向的“服从”;下者、贱者、卑者对上者、贵者、尊者,只能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极端的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此所达至的“和”,是不平等的等级之“和”,是权力威势下的“和”,这样的“和”实际上是适应于“封建专制政治”的“专同”。经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再讲“和”,其内涵就不一样了,其实质是指人际平等的“和”。所谓“和而不同”,在现代,社会的个人和人群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不应再是上下、尊卑、贵贱有等的等级身份之“不同”。于是“和”这个传统的伦理精神,就需要转化为“人际平等”。我们拒绝西方的“个人本位”伦理,但这不等于要排斥伦理关系中的“个人权利”和“权利平等”,相反地应该确立并尊重个人的权利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而只有实现“个人权利”和“权利平等”,才能达至“社会公正”,才能达至“社会和谐”。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由各种不同的“伦理实体”所构成,那绝不是传统社会的那种“伦理本位”的“伦理”,它必定是一种体现了“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的“伦理实体”。恩格斯曾说:“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32)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有了“平等”才会有“人际正义”、“社会公正”,才会有“生态正义”,也才能实现传统“贵和”、“重义”、“民本”和“天人合一”的现代转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设和培育健康良好的道德,社会才会达至伦理之“和”。因而,抓住了“平等”这一伦理精神,也就把握了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魂”,或者说把握了当代中国“伦理实体”之“魂”。
再写中国伦理学,对于传统伦理学来说,是总结;对于现实的中国伦理学来说,是重构。先总结,后重构;重构比总结更难,更复杂!
这里,我主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了“伦理”和“道德”的区别及其关系。但要真正写好“中国伦理学”,任重而道远,要靠大家的努力!
注释:
①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就提出“社会伦理关系”与“个人道德品质”既区别又统一的观点和论述,见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第七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近年来又有宋希仁、高兆明和樊浩等著名学者提出并著有论作。可见高兆明:《道德生活论》,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高兆明、李萍等:《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秩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宋希仁为该书写的“论伦理秩序(代序言)”。樊浩及其学术团队以大量的社会调查材料为据,提出并论述了“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及其关系。
②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载[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③[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
④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页。
⑤陈戍国:《礼记译注》,长沙:岳麓书店,2004年,第273页。
⑥贾谊:《新书》,方向东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页。
⑦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页。
⑧⑨⑩(11)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页;第144页;第97页;第187页。
(12)陈戍国:《礼记译注》,第159页。
(13)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1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2页。
(15)(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第94页。
(16)(1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8页;第173页。
(19)朱贻庭:《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
(20)(23)梁启雄:《荀子简释》,第8页;第341页。
(2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谢秉洪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4页。
(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3页。
(24)(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2页;第10页。
(26)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08页。
(27)高兆明:《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页。
(28)朱贻庭:《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第27-34页。
(29)(30)梁启雄:《荀子简释》,第253页;第251页。
(31)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6-14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