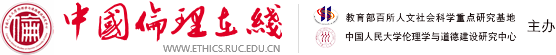姚新中: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思考
摘要: 智慧处于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①。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
作者简介: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莉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 键 词:智慧/比较研究/早期儒家/犹太—基督教
智慧处于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①。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然而,智慧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涉及宇宙、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本质、终极意义和隐蔽的“模式”,一般称之为“理论智慧”“先验智慧”或“大智慧”。无论冠以什么名称,这种智慧或者表现为对于似乎不可知的事物的一种近乎直觉的理解,或者表现为一种穿透事物的表象并领悟存在的本质的洞察力,或者表现为对于人们的好运或不幸和事务的好坏结果的预言性结论。它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知识。它与生活经验相联,但又常常需要超于经验之上。它渗透在宗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事务中,但又常常并不明显,而是隐藏在人们或事物自我运动的某种近似于神秘的模式中。虽然智慧有“较高”与“较低”层次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实践的或理论的,表面的或深层的,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并未涉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仅关涉实践中的问题,更关涉到根本性问题。它是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类作为种族和个体具有连续性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包含在儒家典籍和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文献或篇章,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一、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兴起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源头,从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文明在卡尔·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达到顶峰②。尽管“轴心时代”的界说也许对于我们绘制不同的智慧传统的形态图是适当的,我们对智慧的探究却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期,而是延伸到这一时期之前并扩展至稍后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智慧更像一条穿越时间和空间永不停息的河流,流经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些时间区段中有些相对比较关键,有些则比较平常。但它们都是智慧长链中的组成链环。正是通过这些链环,人类得以形成连续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得以逐渐形成。要理解人类历史、哲学和文明,我们必须研究人类探询智慧的源头、特性和共性。
本文所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两种不同源头的两种特殊传统。即早期以色列传统和早期儒家传统③。这两种传统都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④。现代学术往往明确地把宗教与哲学、神圣的与世俗的分割开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古以色列传统中的智慧主要是宗教的,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狭隘理解。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适合古代欧洲或亚洲的思想体系。在古以色列或古希腊,并没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与宗教相对应的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术语一以贯之地与拉丁文中的religio或英语中的religion相对应”⑤。古汉语中也没有一个对应于religion的特定词。而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同的方面:‘宗’将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联系起来,‘教’指对古代教义的传承,而‘道’则指其神秘的本质或深奥的学说。所有这些词并没有将宗教的与哲学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道德的与习俗的割裂开来,而是反映了运行于历史与文明之中的作为整体的同一个系统。如同儒家传统一样,以色列传统中的讨论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哲学的思索又是宗教的规则。
大部分儒家和以色列的智慧课本的作者也是最初的教育者。关于智慧的教学起源于教育。许多学者将儒的起源追溯至周朝(公元前1045?~256)的政府机构(司徒之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其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伴随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宗教崇拜行为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众多的儒不再从事官方指派的职业,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儒以其在国家的宗教仪式和在官学与私学的技能而著称。汉字“儒”也逐渐扩展为一个用来指特定人群的专用术语,这些人具有宗教礼仪、历史、诗、音乐、数学和箭术的技能,并依靠其对各种礼仪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而生活。关于古以色列是否存在一个智慧运动以及智慧文本是否由宫廷教师著述而成?当代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然而,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所罗门王和他的朝臣所起的作用,并推测在国王的赞助下,正式的持久的由“明智之人”组成的团体经久不衰。犹太教智慧文献中的智慧箴言就以此为主要背景。事实上,二者都是官方的或民间教育的产物,就此而言,儒学智慧和犹太教智慧的起源看起来是一致的。通过使用或收集来自宫廷教育的原材料,后来的儒家和犹太教师们构建或改造了对智慧的理解。将智慧教义的教育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各个社会阶层。通过编辑和阐释,他们创造了一个或口头或书面的“新”的智慧传统,使之既适用于正式教育又适合于大众学习。
只是在约近几十年之前,圣经旧约文献中的智慧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关于圣经文献的研究者逐渐形成对智慧的浓厚兴趣,并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的层面上,开展了对智慧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Gerhard von Rad可以说是这一新兴趣的始作俑者。他在其著作《以色列的智慧》(Nashville: Abingdon, 1972)中开创了对圣经的智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随之有Roger N. Whybray的著作:《〈旧约〉的理性传统》(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1974), James crenshaw的《古以色列的智慧研究》(New York: Ktav,1976)和《〈旧约〉的智慧:导论》(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98),和Roland E. Murphy的《智慧文献:〈旧约〉文献的形式》(Volume XIII, Grand Rapids: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81);《智慧和知识:帕宾纪念文集》(ed. by J. Armenti, Philadelphia: Villanova Press, 1976)。一本名为《(圣经旧约中)智慧文献研究综述》(Dianne Bergan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很好地概述并精细地评论了许多对这一领域提出来的新论点和假设以及一些其他有关的出版物。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的知识,并扩展了我们对古以色列智慧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作为一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传统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对儒家典籍的带有详细注解的不同翻译版本使西方学生和学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儒家大师的智慧。尤其是《论语》和《孟子》(刘殿爵英译),《述者和作者:关于《论语》的中国注释者及注释》(by John Makeham,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4),《荀子全集》(tr. by John Knobloc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s. 1-3, 1988-1994),《大学和中庸》(tr. by Andrew Plaks, Penguin Classics, 2003)。对早期儒学进行精深研究近来也取得进展,许多著作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早期儒学的智慧维度。以下是对传统儒家中的智慧进行研究的一些有特殊价值的著作:《儒学之道的变迁》(John Berthrong, Westview, 1998);《儒学导论》(Xinzhong Y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儒学百科全书》(ed. by Xinzhong Yao, Routledge Curzon, 2003);《中国的神秘主义和王权:中国智慧的核心》(Julia 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儒学传统的发展动力》(ed.by Irene Eber, Macmillan, 1986);《儒学之道—中国哲学之研究》(David Nivison, Chicago: Open Court, 1996);《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对后传统思想的突破方面的一个重建》(Heiner Roetz,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美德之路:古老的孔子智慧之现代转型》(James Vollbracht, Humanics New Age, 1997);《通过孔子思考》(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和《孔子与论语:新论文集》(Bryan Van Nor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我们打算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智慧。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早期传统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影响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传统。早期以色列传统成为后来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西方世界,而早期儒家思想和理念则成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影响东亚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其次,两种传统都留下了丰富的智慧资源,这一资源涉及宗教信仰、哲学推理和心理情感,由信仰、知识、理性和情感的经验积累而来。第三,在其智慧观中,两者都显现了一种宇宙伦理的倾向。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把智慧与知识以及宇宙论分割开来。这并不适合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的智慧观。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与知识、经验紧密联系。换言之,它们都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蕴涵着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沉思和体验。从这一视角出发,智慧可以被定义为知识、能力/技能和洞察力。也可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之路。它来自人类对世界、自然或社会的观察,也是人类对那些只能通过事件结果和社会习俗的作用才能显露的潜藏法则的反思。
二、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智慧文献
每个传统是否存在一组可以准确定义为智慧的文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选择犹太智慧文献是当代圣经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存在一类特殊的人群(职业)“智者(hakam)”,他们的社会功能有别于先知和牧师。这些智者的成果就是留存下来、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智慧文献的书籍。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从文字风格的角度划清界限:以智慧为核心的特殊的文献类型。另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那些涉及非宗教启示的言辞和经验才属于智慧文献。我们并不打算介入这样的争论,而只考虑那些已经普遍接受为早期犹太传统中论述智慧的文献典籍。我们将主要从所谓的《圣经》智慧书中汲取资源,尤其是《箴言》、《约伯记》、希伯来传统的《传道书》、作为伪经(对于犹太教徒和清教徒而言)或双权威书(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一部分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这些文献构成所谓的古代犹太的智慧书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献收集了一些早期特殊的教义,指导人们在面对宗教、社会、个人问题时应当如何思考、行为;另外的原因则出于智慧(hkw)的希伯来语词根,该词根在《旧约》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了318次”,《希伯来圣经》中“一多半(183)是发现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中”,而在两部双权威╱伪经书中“希腊文字sophos或sophia出现了超过100次”⑦。《圣经·旧约》中保存的其它文献如《诗篇》、《列王记上》和《雅歌》也将被参考以补充上述五本书的论述。
早期儒家对智慧的理解,我们可以追溯到《论语》、《孟子》、《荀子》、《易经》、《中庸》。这些著作是在所谓的经典儒家时代产生或编纂的,并通过解释传统而阐释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新观点。儒家经典中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诗经》、《尚书》、《礼记》,这些在或早或晚时代成书的文献对于儒家智慧的解释也非常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也将作为参考。然而与早期犹太传统的智慧文献不同,这些书或文献从来没有明确地定义为“智慧书”。它们是儒家传统经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它们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儒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智慧观。尽管如此,它们与早期犹太智慧书十分相似,因为它们也记载了儒家圣贤们的言行和教导,其中有一些包含了格言,贯穿了对来自更古老传统的谚语和语录的系统论述。
早期以色列的智慧文献和儒家典籍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认识智慧开启了一条道路。通过阅读这些来自互不相关的两种历史传统中的文本,我们确信圣经的智慧和儒家的智慧都试图为知识的探索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的旅行者揭示一条路径。
三、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智慧观的比较研究
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智慧的探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对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孔汉思将世界宗教划分为不同类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预言式的宗教,而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宗教则是智慧的宗教。但他也强调在所谓预言型宗教中存在丰富的“智慧文献”,而智慧型宗教又具有“某种类似于预言式的特征”⑧。在把哲学和宗教理解为“教义”的基础上,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都是“智慧或智的传统”,并由此确定其比较研究的框架,尤其是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两种传统中,智慧显然是东方和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宇宙哲学和伦理蕴涵尚待进一步研究。通过比较这些智慧传统,考察其独特的表达智慧的方式,我们将能更好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智慧”这个概念表达了什么涵义?智慧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这两种哲学一宗教体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古中国和古以色列的哲学思考和宗教践行中,智慧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这两种传统中就有“大智慧”和“小智慧”之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智慧的实际运用的重要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如儒家的《论语》和基督教《旧约》中的“箴言”等典籍中所包含的格言和谚语中。这些智慧的并常常是幽默的谚语几千年来一直在起作用,至今,依然有许多人用之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与现在关于智慧的研究不同,我们的智慧研究不能仅限于实践问题。为了充分领会其“智慧思想或传统”,我们必须考察较高层面的智慧,即“大智慧”是如何形成、运用和推论的?又是如何成为有关形而上学、伦理道德和政治事务的世界观的主旨,并引导着中华民族和以色列人民探求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
(一)智慧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根据如包含在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智慧文献,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而对儒家智慧的研究就薄弱得多。就《旧约》中的智慧的性质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经验为基础的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规律的实践性知识”⑨,“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或一个思想系统”,或“先验理性”⑩。关于智慧的起源,要么认为来自“按照关系来探求对自身的理解”(11),或“源自试图发现人类生活秩序的努力”(12)。这些学术性观点试图将圣经的智慧置于人类理性或人类对上帝命令的响应之中。以色列思想的典型特征即充满了救赎的历史和由耶和华创造的针对以色列祖先的教义。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西奈山圣约都是叙述上帝的诫命以及如果背叛上帝将遭受的灾难或惩罚的警告。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拯救历史的其他文本中的主题相对比,智慧文本中缺乏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主要针对个体生活的日常事务。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由于以色列人从一个关于智慧思考的更为宽泛的范围继承了其智慧思想,其记载教规的文本更多地表现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特征。然而,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与被强调的其他类型的希伯来经文相比较,在智慧文本中,神的介入是隐性的,在此意义上,这些文本并没有脱离救助叙述的背景,而是巧妙地将这一背景渗入对实践问题和日常事务的解决方法之中。它注重的是“世俗世界的领域”。在此,人更为独立地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从成功与失败中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古以色列智慧文献中显示出来的这一特征使其尤其适合与儒家典籍进行比较。
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思想”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智慧的本质。智慧是什么?来自何处?它在圣经传统中起什么作用?许多学者已经尽力去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犹太—基督教的学者并没有太关注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或一种传统或一种思考方式的智慧,就优先性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书,以及耶稣基督的古老预言的实现和基督徒的行为准则。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智慧可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首先,智慧是一种思考方式,思考、研究和分析人与外在世界,人与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其他人,以及人与精神权威之间的关系。智慧明智地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并预见好的或坏的结局,在此基础上探求处理生活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智慧区别于其他的思考方式,而成为行动的指导方针。第二,智慧是一种存在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传承之中的传统。智慧传统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得以丰富。智慧被具体化为法律规则、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是影响个体行为方式选择的戒律性和强制性力量。在此意义上,智慧传统明确规定了生活之路。第三,智慧是一种以浓缩的形式理论地反映智慧思想并记录智慧传统的特殊文献或文本。智慧文献通常是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他们收集、编辑和汇编现存的素材,表现为一种或松散或系统的箴言汇集。被用来作为教育的教科书或作为公众的一般读物。把智慧划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考虑,事实上,这三种形式是相互交叉的,应视为智慧整体的三个方面。因此,要理解智慧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智慧存在和产生作用的内容和背景。从这种观点出发,智慧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使智慧富有意义和具有可能性的世界秩序的反映,一种产生于内在智识和外在探究的理性积累。一种人与世界、社会及其精神权威之间关系的丰富和扩展。
(二)智慧的内容和背景
1智慧: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奇妙。这些是对原初宇宙秩序的反映吗?如果有这样一个秩序,它为什么形成?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以及搜索如何应对繁杂世界并使之为人类所用之道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探求智慧的推动力。智慧是一个集合词,它包含了人类知识、技能、洞察力和能力的许多方面或维度。它可以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人因此而成为“明智”的。它蕴涵了特殊的技能和能力,一些人因此可以更迅速、更灵巧、更成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或存在,智慧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在宇宙,在一系列事件,在发展或演化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秩序和模式。如果洞悉了这些秩序或模式,就能确定规章制度。通过遵循规章制度,人们会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发现秩序的人被称为智慧的导师,巧妙地确立和使用规章制度的人被称为“圣人”或“圣王”。于是,规章制度得到道德上的正当性论证并成为道德的、正义的、公正的,并要求人们遵循和贯彻这些规章制度。然而,生活并不总是显得如此简单,往往那些遵循善的规则的人并不总是能有圆满的生活,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承受着不该受的惩罚。反而是那些漠视规则的人可能享有财富、权力和名誉。这就触及了世界秩序意义的第二个层面,那些试图思考“混乱的秩序”或“不公平的正义”的人能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发生,他们的发现因此而公认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同社会和文化形成不同的探究方式和使规则形式化的不同方式。由是形成不同形式或类型的智慧。然而,所有潜在的形式都是一种解开世界和生活之秘密、发现或了解控制世界的秩序的尝试。通过希伯来经文和儒家典籍中的概念和段落,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基本信仰:相信存在一个世界秩序,存在一个自然界事件的秩序,存在一个人类日常行为的秩序。对这一秩序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洞察看起来紊乱的事物和事件。并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圆满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些著述的作者强烈地反对当时在生活中盛行的失序,他们严重关切其所处时代中占支配地位的混乱与分裂,他们将智慧视为对世界秩序或对恢复世界秩序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这一秩序可以被充分领悟或遵循吗?犹太教的智者们和儒家大师们基于不同的理由都相信秩序是可以被认识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其中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尽管一些儒者将道或命归为超出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不可知之物,他们中大多会承认最终可以“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对一些以色列智者而言,这个问题对其解释智慧具有更强烈的影响。一些智者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否“领悟”上帝的目的,能否认识秩序的最深处,并最终承认“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约伯记》36:26)。
2.智慧:人类的理性
要较好地理解秩序,必须有优良的理性。通过儒家和犹太教的论述,智慧已成为一种活着的传统和一种文献的载体。这一传统由“导师”或智者所驱动,是一种对真实的特殊理解,并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宗教的也是理性的。就前者而言,无论其称谓是上帝或上帝的创造,天或天命都是外在的,激励着人类去探求和发现,而后者是人类对秩序或道的反思和遵循。在此意义上,智慧是对已经找到宇宙秩序和协调之人的一种奖赏。
智慧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献,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特殊的生活阅历。源于对人类经历的理性反思,并以语言为媒介得以表达。生活和语言都是多方面的,智慧亦如此。众所周知,在欧洲传统中,智慧在希腊文中指理性、道德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而且都被导向理性。Sophia指那些投身于追求真理的哲学家的天赋,Phronesis,可以译为实践智慧,指的是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使其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不受激情的驱策和感官的欺骗。Episteme则指某种形式的科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只有那些深悉事物本性以及控制行为的原则的人才能发展起来(13)。在希伯来文中,也有许多词对应于我们所称的“智慧”:binah(理解,理性),hakam(明智,教导),hokmā,hokmoth(智慧,技巧),sakal(成为明智或理性)(14)。收集在《旧约》中的希伯来圣经中常用的词根是hkm,R.N.Whybray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天生的智能”(15),和“表现为多样的能力或技巧”,具备这些技巧的每一个人都可“视为明智”(16)。古代中国则形成一种根本不同的书面语言系统,它起源于象形文字的象征,试图使内在概念与外在事物及生命之间相互关联(17)。在后来已经充分发展的先知骨的碑铭中,(约公元前15-13世纪),并没有发现与智慧相对应的汉字,而是由一个与知识相对应并也发音为zhi(知)的词来表示。Zhi由一支箭(矢)和一个口(口)组成,象征着人们像飞驰的箭一样迅速地获得知识。《说文解字注》中给“知”下了一个定义:“智慧指知识,有智慧的人指无所不知之人”(18)
3.智慧:一种关系
认识是为了产生联系,明智是理性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联系。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也只有处在关系的背景中才有意义。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中,关系主要由我们试图领悟的三个客体来阐释:智慧指向的第一个客体是外在世界(宇宙、万物、自然界等等)。在这层关系中,智慧探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起源、性质和秩序。在有神论传统中,世界秩序也许指创造物的秩序,在其他类型的传统中,或许指自然的或道德的法则。无论是否带有神性的特征,这些传统都相信世界的所有现象都以某种秩序或法则为基础,人们必须遵循它们。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和洞察也许应称为宇宙智慧,是对最基本、最深切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智慧的第二个客体是社会,包括政治的、司法的、伦理的和团体的各个方面,这本质上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此,我们获得所谓的社会智慧,常汇集为伦理规范、道德命令、法律制度和政治机构,并通过这些而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要遵循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人类探询的第三个客体是个体自身即人类的内在世界,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使我们能获得“个人的智慧”,即关于特殊个体如何思想,如何被激发,在面临选择时如何明智地回应,在日常生活中作什么选择,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个体性格。正如世界、社会和个人不能彼此完全分离,智慧也包含了或洞察力或知识或直觉中上述三个方面,是我们理解、解释和调整我们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其他个体以及我们自身关系的有效工具。
(三)智慧的四种类型
在James Crenshaw对《旧约》中的智慧的论述中,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智慧的定义即“是对关于人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自我理解的探求”(19)这一自我理解可通向智慧的四种类型:自然的、实践的、法律的、神学的。按关系来划分智慧,还有其他的方式,而每一种划分方式对探求智慧的性质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下面我们将阐述存在于早期儒家和犹太教箴言和教义中的智慧的四种类型。
1.自然智慧
自然智慧产生于人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对自然事件和现象的知识使人能够利用自然并导向美好生活。在“列王纪上”(4:33)中提到,除了作箴言三千句之外,所罗门王也“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说明自然智慧、自然知识是智慧的一部分。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也是儒家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论语》中的格言主要论及社会、政治和个人事物,但这并不表示孔子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他曾经想知道为什么“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他也观察了表现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的自然秩序。荀子引入了“天”的概念,他认为宇宙的神秘都能由自然事物的序列来解释。我们从这些自然界的知识中获得控制气候、洪水等自然现象的智慧。
2.实践智慧
智慧在行为中具体化,并能通过实践而获得。然后形成某种习惯性态度,这被称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通过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来对生活进行的可操作性管理,很可能在古以色列和古中国得到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在几千年来塑造了民族的特质。实践智慧处理日常生活事物,包含应付生活需要的技巧和能力。技巧是一个有许多涵义和意义的词,它指处理复杂情况如态度、道德取向和灵巧的方式等所谓“软”技巧,也指用来克服困难并完成工作的“硬”技巧。孔子同时注重这两个方面,并教导其弟子学习这些技巧以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的一位弟子称赞他不仅是一位圣者,而且“又多能也”,孔子解释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为了说明如何为仁,孔子用了一个工匠为例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犹太教的文献中也将技能作为实践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箴言不仅强调技能可以使人避开危险,也建议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能够建造房屋(箴言24:3)。
3.法律和政治的智慧
法律和政治的智慧来自对与民众相关的统治实践的衡量的思考,并用来解决法律和政治难题。这一类智慧的核心是如何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确保和平与协调。如何良好地治理是儒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儒学主要在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给统治者提供建议。儒家倡导德治并主张如果适当运用道德来影响秩序则和平自然会实现。关于如何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古以色列的政治智慧主要关系到如何处理司法案件,以确保明智之人有好的结果,而愚蠢之人会自食恶果。因此,如何维持社会正义成为犹太教法律智慧的核心。所罗门对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的案件的审判,就体现了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智慧(20)。
4.超越性智慧
第四类智慧来自对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关系的反思。可称为“神学智慧”或“超越智慧”。在古以色列,这主要关系到自然神学的问题,面对盛行的不义和混乱,如何维护耶和华的正义?如果一个人遵循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他应该拥有好的生活、受到保护、富有、健康等等,而一旦违背耶和华和他的律法,就应受惩罚。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当善良的人承受痛苦而作恶之人享有舒适生活时,智慧的思想者,尤其是“约伯记”的作者,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阐明了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并在希伯来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玄思的智慧。在中国的同一历史时期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即善良之人承担来自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后果,《诗经》中的一些诗记载了这些沉思。在这些诗里,人们抱怨天不关心他们遭受的不义待遇。然而,尤其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产生的理性主义改变了大部分儒家大师的思考方向。使他们从询问天是否公正转向考察人之道:“天道远,人道近”。儒家探究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合,而不是阐述关于神的正义的形而上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儒家典籍没有对人与超越之间关系的玄思。儒家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时,概述了神学智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人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天赋予的使命(《论语·子罕》);不可欺骗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为儒家智慧提供了一个宗教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实践其他的人类关系。
(四)智慧的神圣性
智慧的神圣性问题在希伯来文献中体现为智慧与上帝的关系,在儒家则体现为智慧与天的关系。对早期儒家大师和以色列智者而言,智慧与他们对宗教或神性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对神性的解释方式也许相差很远。智慧教义与神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智慧具有一层深刻的“神圣”意蕴。早期儒家和以色列传统都认为智慧有宗教层面,在其文献中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智慧的宗教层面。以色列的智慧观是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智慧教义有其独有的特性,并呈现为一种对上帝的信仰的证明,“敬畏上帝”仍是以色列传统的根基,也是其智慧文献的中心,如“神有智慧和能力”(约伯记12:13)。我们不否认这些讨论本质上是宗教的,因为其基本主题是“敬畏上帝”(箴言9:10),其意义和内容也是由对上帝的创造和行为的理解来决定:“信男人和女人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性,信人类和他们行为的相似之处,信或隐或显支撑着人类生活的秩序,信使这秩序得以有效运行的上帝”(2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以色列思想家有意地将一般性质上的理智推理和哲学讨论排斥在智慧论述之外。正如许多其他古代传统一样,在早期以色列传统中,信仰和知识是一体的,神圣的体验也就是尘世的体验。作为一种活的经验密码,智者的箴言记录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洞察力。把智慧理解为一种“生命之道”(箴言10:17),使以色列人的智慧观和他们的伦理思想联系起来。当一些以色列智者谴责作恶者享受荣华而正直的人却遭受厄运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详细阐述了一种赏善惩恶的正义补偿。在以色列的思想家看来,智慧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于耶和华并作为神圣的创造物赐予人。因此,神圣来自神性并主要指“圣洁”(22)。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也有其“神圣”的层面,“神圣”与“天命”相联系,这使人类的理解力可能超越暂时之物。然而,儒家智慧的神圣主要地并不根源于此,而是源于知识的深远处,源于祖先教义的传承和人类理性与宇宙性质之间的神秘关联。在此种意义上,儒家智慧和以色列智慧对于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以色列传统中,尽管智慧与上帝关联,并是世界创造物的一部分。但包括人类在内的创造物都没有神性,所有的事物、事件和东西,不管它们显得有多重要,都只有当它们在神的意义上被创造时才成为神圣的。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源于人性与使人可以认识表面“不可察觉”的世界本质的宇宙万物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天地人这三个领域的所有现实事物都部分地或整体地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的本性。要理解儒家的智慧,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儒家大师们为我们描绘的从道德上解释世界的情境之中。世界由天地人所组成,并以某种“道”表现自身,智者通过观察和辨别这些“道”,而能够为人类确立必须遵循的“法则”,而特定的个人能否发现这些“道”并遵循“法则”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和实践。
智慧不能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智慧与人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可能对早期以色列教师而言没有特殊意义,却是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在儒家典籍中,人性既是一个心理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环境问题。要以对人性的探究为个体智慧的起点,我们将考察智慧是否包含先天因素,人由于其自然禀赋的差异是否可以划分为聪明人和愚笨人这两种,以及智慧是否在生活阅历中起作用?接下来涉及到智慧的认识论问题,智慧是一种知识吗?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传承或教导吗?它是如何世代传递的?毫无疑问,智慧存在于知识的形式中,但许多传统根本否认知识在智慧中的作用。这也许预示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异。我们还必须考察知识的实践层面,即它的有效性。它对于指导生活、形成生活的特定方式的意义和价值。智慧必须具备技巧和能力,古以色列和儒家智慧文献都表明一个缺乏实践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智者,而一个很明智的人肯定精通实践事务。智慧不仅是一种狡猾或机灵,更是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德性。在儒家的理解中,智慧的德性层面是最为基本的,在犹太教传统中这一层面也很重要,并依次与智慧在社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运用紧密相联。在这些领域里,明智的人与愚蠢的人处理问题、作出选择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古以色列和古中国的理想人物就是犹太教的所罗门王和儒家的如尧、舜这样的圣君。最后我们将到达智慧旅程的最后一站。在此,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都将完全理解世界和生活的秘密和神奇。在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人的有限性而进入神的创造过程,并因此而达致永恒。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思想家和儒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以色列人认为人类不能通过自身而成为先知—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并赋予其神的智慧。犹太先知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智能而洞悉世界和历史的神秘。而儒家的圣人则不同,在成圣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神秘的成分,但大多数儒者都能通过对美德和知识的学习而成圣。就是在这一差异中,我们将发现早期以色列和儒家传统中的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我们的研究表明圣经中的智慧和早期儒家的智慧都在试图为知识寻求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旅行者揭示出一条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实质上是一种旅行,或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旅程,或者是一个特殊个体的个体旅程。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个体,都需要通过智慧的旅途来揭示和实现其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智慧旅行是通过不断克服张力来实现的。这一张力存在于人与超自然之间,也存在于经验的与神秘的之间,而克服张力就意味着获得特定的智慧(23)。这也是使人类从自然的赠与到完成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旅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个体在理性和精神方面的逐渐丰富,不断成熟的旅程:始自知识的经验性积累和使人类可以应对生活技巧的拥有,之后是对规则、法律和原则的掌握,最后到理性和精神的圆满,使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是一个从知识到超越的发展过程,使每一个致力于这一发展的人都达致理想人格,即儒家的圣人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这就是包括儒家和犹太教—基督教在内的中外所有智慧传统的本质意义和终极目的。
注释:
①Xinzhong Yao and Yanxia Zhao: Chinese Religion: A Contextual Approach, London: Conitnuum, 2010, p. 173.
②卡尔·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
③根据《旧约》中“创世纪”32:28,“Israel”是由耶和华授予雅各的称号,意思是“与神较力的人”。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他们后来成为12个以色列部落的首领。我们在本书中所用的“Israel”并不指这个意义,也不是指后来建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两个王国(犹太和以色列)中的一个。而只是表示被记载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的“以色列人民的传统”。在本文中,早期儒家指的是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2世纪追随儒家之道的儒家学者们所阐发的世界观。
④英文中的“Philosophical”可以有多种含义,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狭义来解释,即认为只是从古希腊到现代形而上学哲学理论的分析传统。这里,我们从更为一般的性质上来理解哲学,即指以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对真理的理性探究。而英文中的“religion”也有多种意义:“信仰上帝或神”、“宗教礼仪体系”、“寻求生命中的神圣意义”,但在本文中,它主要标志某一特殊文化的观念、理想和行为之综合体,特别是指一种寻求突破人之有限性的生活方式。
⑤Paul J. Griffiths:《宗教多样性的问题》,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 3.希腊文中通常用来表示敬畏上帝的祭祀或仪式行为的词是thrēskeia,尽管当用来表示异教徒或可疑的教徒时,这个词的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词eusebeia指“虔诚”,指敬畏上帝和他所维护的社会或道德秩序。这个词转换成箴言(1:7),即:“敬畏上帝”。
⑥如何划出圣经中智慧文献的范围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将之扩展到《旧约》几乎所有书中,如《创世纪》1-11,37-50,《大流散记》32,《申命记》,《阿摩司书》,《弥迦书》,《以赛亚书》,《约拿书》,《哈巴谷书》、《以斯帖记》、《撒目耳记下》9-12,《列王记上》1-2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试图为这种探求确定一个界限。即使承认其他圣经文献包含类似于五本书中所发现的词汇和观点,我们也将不会容许自己陷入这场争论之中。
⑦《铁锚圣经词典》(主编:大卫·诺尔·弗里德曼),达波迪出版社,1992年6卷第920页(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Editor-in-chief: David Noel Freedman, Doubleday, 1992, volume VI, p. 920.)
⑧孔汉思,秦家懿:《基督教与中国宗教》,New York:Doubleday an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第xv, xvi页.
⑨Gerhard von Rad:《旧约》神学,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 418.
⑩Whybray, 1974, p. 72, 7.
(11)Crenshaw, 1976, p. 484.
(12)John G. Gammie, Walter A. Brueggemann, W. Lee Humphr-eys, James M. Ward, eds:以色列智慧:纪念Samuel Terrien的神学和文学论文集Missoula, Montana: Scholars Press, 1978, p. 35.
(13)Robert J. Sternberg(ed)《智慧: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剑桥大学出版,1990, p. 14.
(14)Robert Young:《圣经注释索引》,London: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 Lutterworth Press, eighth edition,1939, pp. 1059-1060.
(15)R. N. Whybray:《〈旧约〉》中的理性传统,Berlin: Walter deGruyter, 1974, p. 7.
(16)Dianne: Bergant:《他们对智慧文献有什么观点》New York/Ramsey: Paulist Press, 1984, p. 7.
(17)据许慎(30?-124?)的《说文解字》(中国汉字的第一部词源学字典),最初的汉字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模仿:“天空中的形象”“地上的图形”“鸟和兽的图形”(《说文解字注》,(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l, p. 789.
(18)同上p. 227.由于将智慧等同于知识,在大多数早期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本中,智慧的zhi(智)并没有与知识的zhi(知)区分开来,这表明在古中国人的思想里,智慧主要源于知识。这一词源学证明表明中国的智慧观有很强的知性趋向。
(19)James Crenshaw:《古以色列智慧研究》,New York:KTAV, 1976, p. iX.
(20)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列王纪上3:25-28)
(21)Gerhard von Rad:《以色列智慧》,Nashville, 1972, p. 62-63.
(22)在希伯来文中,d(holy)的基本语义是“分开”。它特指上帝,和上帝自身的性质(John L. McKenzie, S, J. 圣经字典,伦敦—都柏林: Geoffery Chapman, 1965, p. 365)。“holy”主要与耶和华及其创造物相联系。耶和华被视为“以色列的圣者”。由于他们由耶和华挑选而来并属于耶和华。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因此圣洁是神的礼物或奖赏:“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11:44; 19:2; 20:7, 26)。意识到在英语的习惯用法中,“holy”和“sacred”都指献身于上帝并或多或少地有意义重合的方面。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区分这两个词:“holy”指与世俗的适当的分离,根本上是与“精神的他在”相联系,而“sacred”则指通过伦理、宗教和精神的途径加于世俗的神圣庄严的意义和价值。
(23)在探讨《旧约》中的智慧文献的范围时,Dell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张力是理解智慧的中心点,智慧以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张力为特征。(Katherine Dell:《得智慧,得见识:以色列智慧文献的研究导论》)Macon: Smyth & Helwys Publishing, Inc., 2000, p. 6.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