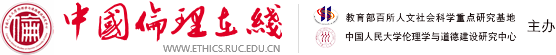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利他主义(下)
摘要:
作者:Richard Kraut
译者:王宝锋
来源: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altruism/
当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自己以外的人的利益,通常被描述为利他主义。这个词与“自利”、“自私”或“利己主义”相反--这些词适用于完全出于为自己谋利的动机的行为。“恶意”指的是一个更大的对比:它适用于那些仅仅为了伤害他人而表达出伤害他人的愿望的行为。
然而,有时这个词被更广泛地用于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这种广义的利他主义可能被归因于某些种类的非人类动物--例如母熊,它们保护自己的幼崽不受攻击,并在这样做时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如此使用,并不意味着这种成年熊“为了”它们的幼崽而行动(Sober and Wilson 1998: 6)。
本文将讨论前一种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即为了其他个体的利益而故意采取的帮助别人的行为。关于利他主义有大量的、不断增长的经验文献,这些文献询问人类的利他主义是否有进化或生物基础,以及非人类物种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这些问题在关于利他主义和生物利他主义的实证方法的条目中有所涉及。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利他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呢?利他主义是否一定令人钦佩?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着想而行动?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事实上是出于利他主义而行动,还是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是自利的?
目 录
1. 什么是利他主义?
1.1 混合动机和纯利他主义
1.2 自我牺牲、强和弱的利他主义
1.3 道德动机和利他主义动机
1.4 福祉与完美
2. 利他主义是否存在?
2.1 心理利己主义:强和弱的版本
2.2 心理利己主义的经验论证
2.3 心理利己主义的先验论证
2.4 饥饿与欲望
2.5 欲望和动机
2.6 纯粹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
2.7 利己主义是否存在?(上期结束)
3. 自我和他人:一些激进的形而上学选择
4. 为什么要关心他人?
4.1 幸福主义
4.2 不偏不倚的理性
4.3 内格尔和非个人立场
4.4 感性主义和同胞情感
5. 康德关于同情心和责任
6. 重新审视感性主义
7. 结语
3►
自我和他人:一些激进的形而上学选择
许多人对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动机的一个假设是,后者比前者更难证明,或者前者不需要证明,而后者需要证明。如果有人问自己:“为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做任何事情的理由?”我们很想回答,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也许是因为不可能有答案。可以说,自我利益不能被赋予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相比之下,由于其他人是其他人,似乎需要给出一些理由来建立一座从自己到其他人的桥梁。换句话说,我们显然必须在别人身上找到一些东西,以证明我们对他们的福祉感兴趣,而一个人不需要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些东西,以证明自我关注。(也许我们在别人身上找到的证明利他主义的东西是,他们在重要的方面与自己一样。) 值得一问的是,这种证明自我利益的正当性和证明利他主义的正当性之间明显的不对称是真实的还是只是表面的。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这种不对称是虚幻的,因为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是人为的,是清晰思考的障碍。人们可以通过注意到在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人”的内心生活中发生了多少变化,来开始挑战自我和他人之间区别的有效性或重要性。一个新生儿、一个儿童、一个青少年、一个年轻的成年人、一个中年人和一个接近死亡的老人的思想--这些人的差异至少和那些传统上被算作两个不同个体的人一样多。如果一个20岁的年轻人留出钱来为他在老年时的退休生活做准备,他是在为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储蓄。为什么这不应该被称为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为什么称为为自己的利益或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有什么关系呢?(见Parfit 1984)。
对自我和他人之间区别的有效性的另一种挑战来自于大卫·休谟的观察,即当我们审视内心并清点我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时,我们没有认识到任何实体可以为“自我”一词提供参考。自省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感觉、情感和思想的事情——但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拥有这些感觉、情感和思想的某个实体的经验。这一点可能被认为是拒绝常识性观点的一个理由,即当你提到自己,并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时,有一些你正在谈论的真实的东西,或者在你和其他人之间有一些有效的区别。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动机之间的普通区分是被误导的,因为不存在自我这样的东西。
第三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是这样的:人类不能被逐一理解,好像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和完全真实的个体。这种对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没有认识到我们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深刻的方式。你、我和其他人在本质上都只是某个更大的社会单位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类比,人们可能会想到人体和诸如手指、手掌、手臂、腿、脚趾、躯干等身体的部分。它们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更不可能正常地运作。同样,也可以说,单个人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的碎片。因此,我们不应该使用“自利”和“利他”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概念,而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对我们所属的更大社区的成功和良好运作的贡献者(见Brink 2003;Green 1883)。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搁置这些非正统的替代常识性的形而上学框架,我们在思考自利和利他的动机时通常会预设这些框架。研究它们会让我们走得太远。我们将继续做这些假设。首先,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存在,即使该个体的精神生活经历了许多变化。第二,当一个人谈论自己时,有一个人在指代他,尽管不存在我们内省检测到的名为“自我”的对象。而我们通过内省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对象,这并不是怀疑在自己和他人之间所做区分的有效性的理由。第三,尽管某些事物(胳膊、腿、鼻子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但没有人在本质上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部分。拒绝这些想法,我们将继续以常识来假设,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这样一个东西,即什么是对这个人好的;而“什么是对我好的?”、“什么是对那个不是我的其他个体好的?”这些问题是不同的问题。因此,一个理由是自利的,而另一个理由是利他的(当然,同一行为可以由两种理由支持),这是一回事。
那么,假设这些动机之间的区别是真实的,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是利他主义的?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被激励是否需要一个理由?利己主义的动机是否比利他主义的动机更可靠,因为它不需要理由?
4►
为什么要关心他人?
在道德哲学中可以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法将自利的动机作为根本;它认为我们应该利他,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这种策略通常归功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见Annas 1993)。
在现代,第二种方法脱颖而出,它建立在道德思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不偏不倚和非个人的概念上。它的基本思想是,当我们从道德上思考该怎么做时,理性以上帝之眼为视角,把我们通常对自己有利,或对朋友圈或社区有利的情感偏见放在一边。在这里,康德(1785年)是一个代表人物,但功利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是1789年的Jeremy Bentham,1864年的John Stuart Mill,以及1907年的Henry Sidgwick。
第三种方法,由大卫·休谟(1739)、亚当·斯密(1759)和阿瑟·叔本华(1840)倡导,赋予同情心、怜悯心和个人感情——而不是不偏不倚的理性——在道德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它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中存在着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当道德仅仅或主要从非个人的角度和从上帝的角度来理解时,人类生活的特点被忽视或扭曲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自然而然地在情感上对他人的利益和不幸做出反应;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寻找这样做的理由。(本条目中标有“感性主义”的各种观点是由Blum 1980;Noddings 1986;Slote 1992,2001 2010,2013;以及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松散地衍生出来的。这个词有时适用于一系列元伦理学观点,这些观点将道德命题的意义或理由建立在态度而非与反应无关的事实之上(Blackburn 2001)。在这里,相比之下,感性主义是一个关于人类关系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基础理论。它可以与元伦理学的感性主义相结合,但不必如此)。
这三种方法很难说是对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利他主义的所有说法的详尽调查。一个更全面的处理方法将考察基督教的爱的概念,正如中世纪的思想家所发展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是在利他主义的框架内工作的,尽管他们也受到新柏拉图式的影响,即把可见的世界看作是神的善的丰盛的流露。就天堂的奖赏和地狱的苦难在神学框架中的作用而言,对于那些需要的人来说,有工具性的理由去关心他人。但也有其他原因。像慈善和正义这样的其他美德是人类灵魂的完善,因此是我们世俗幸福的组成部分。基督教哲学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神圣的存在没有道德品质,不对人类生活进行干预。上帝是一个爱他的创造物的人,人类高于一切。当我们为自己而爱别人时,我们模仿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刘易斯1960)。
4.1 幸福主义
哲学家们经常用“eudaimonism”这个词来指代希腊和罗马古代所有或主要哲学家的伦理取向。“Eudaimonia”是他们适用于最高善的普通希腊语词汇。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头所观察到的,每当我们行动时,我们的目标是某种善——但善并不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较低的善物是为了更有价值的目标而进行的,而这些目标的追求又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善。这种价值层次不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生活必须有一些终极目标,一些本身就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更好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承认,这个目标应该是什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用“eudaimonia”这个词来指称这个最高的善。(“幸福”(Happiness)是标准的翻译,但“福祉”(well-being)和“繁荣”可能更接近希腊语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一个人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自己的福祉(eudaimonia)而不是其他人的。相反,他认为公共利益(整个政治社会的利益)要优于单个人的利益。尽管如此,研究古代伦理学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古代其他主要道德哲学家的假设是,一个人的最终目标应该只是自己的福祉。
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假设吗?这是许多现代道德哲学体系的指责,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希腊和罗马的伦理学归结为对自私的极端认可。看到这将是不公平的一个方法是认识到我们为他人着想而爱他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和第九卷中对友谊和爱的长篇讨论的一个关键内容。在那里,他认为(i)友谊是美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ii)要成为某人的朋友(或至少是最好的朋友),就不能把他仅仅作为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快乐的手段。他对(ii)进行了阐述,补充说在最好的友谊中,每个人都因对方的优秀品格而钦佩对方,并因此而使对方受益。那么,很明显,他明确地谴责那些把他人仅仅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人。因此,即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个人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自己的福祉(而不是其他人的),他也把这一点与否认他人的利益应该仅仅作为自己的手段来重视结合起来。
在这一点上,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上文第1.4节中对(i)什么构成福祉和(ii)什么是实现福祉的必要手段或前提条件所做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的福祉是由一个人的理性的出色运用构成的,而诸如正义、勇气和慷慨等美德是一个人的善所包含的品质。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或更大的社区采取公正和慷慨的行动时,这对他自己来说是好的(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好的——事实上,一个人的行动部分是出于为其他人谋福利的愿望。如果按照其他伦理美德公正地对待他人仅仅是实现自身福祉的一种手段,那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框架将是令人反感的自律,而且它很难在不矛盾的情况下认可我们应该为他人着想而造福他人的论点。
我们应该回顾在第1.1节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利他主义行为不需要涉及自我牺牲,即使是出于混合的动机,其中一些是自利的,它们仍然是利他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利他主义应该总是伴随着自利的动机。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假设道德动机必须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没有任何自律的污点,那么他的实践思想体系就会被一概否定。否则,它就不能算作道德。这种想法有一定的流行性,它经常被归结为(正确或错误地)康德。但仔细想来,它是可以质疑的。如果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为他人着想而为他人谋利,同时也有第二个充分的理由,即这样做也会使自己受益,那么假设一个人不应该让第二个理由对自己的动机产生任何影响,这将是不可信的。
尽管如此,如果前面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第1.2节中,我们注意到,如果一个人总是以“除非这样做对我最好,否则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这一原则为指导,那么他将受到批评。这样的人似乎不够利他,不够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做出妥协。他(使用前面介绍的术语)从未在强烈的意义上利他。可以说,如果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最终应该为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行动,那么他的基础就会更牢固。(为了公平起见,他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他确实说过,善待他人永远不会使自己变得更糟)。
如果希腊和罗马的道德哲学所进行的项目是以一个不容置疑的假设开始的,即一个人的行为永远不应该违背他自己的利益,一个人的最终目的应该只是他自己的幸福,那么它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反对意见,即在这个基础上,它将永远无法对他人的利益给予适当的承认。这种反对意见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直接关注他人:一个人所做的行为对他人有利,这已经可以提供一个进行该行为的理由,而不需要伴随一个自利的理由。在古代伦理学中找不到任何论据——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意在表明,要证明拥有顾及他人的动机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呼吁拥有这些动机对自己的好处。
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断然否定这些作者所做的努力,即事实上,一个人拥有利他主义动机确实会带来好处。一旦理解到做一个好人可能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达到私人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人做一个好人是好的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道德上没有任何攻击性。如前所述(1.4节),某些类型的卓越被广泛认为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那里使用的例子是艺术、科学和体育方面的卓越。但在道德生活方面的卓越也是一个合理的例子,因为它包括发展和锻炼认知、情感和社会技能,我们为拥有这些技能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在任何情况下,关闭我们的头脑,拒绝听取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中发现的论点,即伦理美德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人的福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斯多葛学派来说是唯一的组成部分),这将是纯粹的教条主义。
4.2 不偏不倚的推理
我们现在来谈谈一个现代伦理学方法的核心思想,即当我们进行道德思考时,我们会从一个不偏不倚的或非个人的角度进行推理。道德思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然,我们都有一种情感上的偏见,对自我利益特别重视,而且我们常常偏向于我们特定的朋友圈或我们的社区。但是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看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试着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框架放在一边。以上帝之眼看待事物,我们问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什么对我或我的朋友有好处。我们仿佛忘记了把自己定位为这个特定的人;我们从正常的自我中心视角中抽象出来,寻求任何类似的不偏不倚者也会得出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在古代伦理学中找到这种思想的预言或类似物——例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中,政治共同体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个阶级或派别的利益服务;在斯多葛派的信念中,宇宙被一种天意的力量所支配,它为我们每个人分配了一个独特的角色,我们通过这个角色不仅为自己服务,也为整个世界服务。在柏拉图共和国的理想城市中,家庭和私有财产在精英阶层中被废除,因为这些制度干扰了对所有个人的共同关注的发展。目前还不清楚如何使这些想法符合幸福主义的框架。如果只有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人的最高目的,那么社会的利益怎么能作为评价的最高标准呢?看待伦理学历史的一种方式是,现代伦理学挽救了古代伦理学中偶尔出现的不偏不倚主义,并正确地放弃了从先前对自我利益的承诺中得出利他主义的理由的尝试。当然,当代利他主义者会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例如,见Annas 1993;LeBar 2013;Russell 2012)。
到目前为止,不偏不倚的概念被描述得非常笼统,重要的是要看到有不同的方式使其更加具体。其中一种方式是由功利主义者,以及更广泛的后果主义者所采用的。(1789年的Bentham、1864年的Mill和1907年的Sidgwick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们要最大限度地平衡快乐与痛苦,把快乐和没有痛苦作为幸福的唯一成分。后果主义抽离了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成分;它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平衡好与坏。见Driver 2012)。在他们的计算中,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被赋予比其他任何人的利益更多的重量或重要性。因此,你自己的利益,不能因为是你自己的利益,就被你当作比别人的利益更有分量的理由。一个人(或一个有生命的生物)的福祉是为一个人提供了行动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有理由在实际思考中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但同样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福祉,并具有同等效力。
但这并不是把不偏不倚性的一般概念拿出来并使之更加具体的唯一方法。如前所述,一般的想法是,道德思维,与审慎思维不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想法变得更加具体,把它理解为有一套单一的规则或规范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一个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的标准就是回答“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的标准。一个人的实际推理以这个条件为指导,就是遵守不偏不倚的理想。他不会为自己或他的朋友做出特别的例外。
例如,假设你是一名救生员,一天下午你必须在向北游去救一个群体和向南游去救另一个群体之间做出选择。北方的群体包括你的朋友,但南方的群体要大得多,充满了陌生人。上一段描述的不偏不倚理想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它所要求的仅仅是,面临这种两难境地的救生员是你(而北方的群体包括你的朋友),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救生员,你应该做的就是任何救生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在做这个决定时考虑到友谊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人这样做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每个人选择他或她的朋友的利益而不是陌生人的利益)。
结果主义者对不偏不倚性的含义和要求有一个更激进的解释。他的不偏不倚理想不允许救生员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向北游就能救他的朋友。毕竟,他朋友的福祉并不因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而变得更有价值。就像我的利益不会因为是我的利益而比别人的利益更有价值一样,我朋友的福祉也不会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得到额外的重视。因此,根据后果论者的观点,救生员必须选择拯救一个群体而不是另一个群体,这完全是基于善与恶的平衡。
结果主义者会正确地指出,很多时候,一个人在促进自己的利益方面比别人的利益方面更有优势。一般来说,我对什么是对我有利的知识比我对什么是对陌生人有利的知识要多。对我来说,造福自己所需的资源往往比造福他人要少。我不用问就能立即知道我什么时候饿了,我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食物。但要想知道别人什么时候饿,喜欢哪种食物,还需要额外的步骤。这些关于一个人与自己的特殊关系的事实可能会让结果主义者有理由对自己的福祉给予比其他人更多的关注。即便如此,只有一个人是我;而如果我努力的话,我可以受益的其他个人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通常情况下,利己的理由应该让位于利他的动机。
结果主义显然没有认识到每个人与她自己的福祉有特殊关系的某些方式,这种关系不同于她与其他人的福祉的关系。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成年人时,我们通常被赋予特殊的责任,即必须照顾我们自己的福利。幼儿并不被期望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还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但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他们,以便他们在成年后能够对自己负责。一个完全成熟的人理所当然地被别人期望照顾某个人,也就是她自己。她被赋予了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的空间,但却没有被赋予对他人生活的同样种类和程度的权力。如果她想把自己奉献给别人,她不能在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或者没有采取其他步骤使她进入别人的生活被允许的情况下简单地这样做。相比之下,后果主义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对所有人的福祉负有同等责任。它没有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社会关系是由一种分工所支配的,这种分工要求每个人对自己以及某些其他人(一个人的孩子,一个人的朋友,等等)负有特殊责任。
根据上述对不偏不倚性的较弱解释,道德规则反映了这种分工。(“较弱的解释”是指这样一个论点:道德思维避免了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它坚持了一套同样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规则或规范。) 例如,考虑到我们通常有义务帮助他人,即使他们是陌生人。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并请求你的帮助,这就给了你一个帮助他的理由,你应该这样做,只要遵守这种呼吁不会造成过重的负担。注意这个免责条款:它在援助他人的义务中加入了对每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活的重要性的认识。常识性的道德假定,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也假定在普通的生活事务中,牺牲的程度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我们作为成年人被赋予的责任来寻求自己的利益。道德规则在自我利益的要求和他人的要求之间取得的平衡,是使这些规则有可能被承认和接受为适当的。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自愿做出更大的牺牲;但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战争、灾难、紧急情况),这种更大的牺牲并不要求我们做出。
到目前为止,对“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而行动?”这一问题,我们所研究的三种利他主义方法给出了三种相当不同的答案。
幸福论回答说,那些为他人着想而行动的人因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而得到好处。
结果主义者的回答始于这样的主张:一个人的福祉应该被关心,只因为它是某人的福祉;它不应该只因为它是自己的福祉而是重要的。换句话说,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你是接受利益的人,就应该把利益给你而不是别人。因此,如果一个人假设,就像他应该假设的那样,他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那么他就有同样的理由为任何人和所有人的利益行动。
如果我们对不偏不倚性采取一种较弱的解释,我们只需看到我们有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人,就能看到利他主义的合理性。要求我们帮助他人的道德规则是一个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的规则,它不是作为实现我们自身利益的手段,而是仅仅由于他们的需要。我们认为这个规则是合理的,因为它在我们的自我关注和他人的适当要求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
请注意,后果主义和较弱的不偏不倚立场都与幸福主义者的论点兼容,即具有利他主义动机是一个人自身福祉的组成部分。这两种形式的不偏不倚所拒绝的是更强的幸福论,即一个人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自己的福祉,而且仅仅是这样。
在以下方面,这种更强烈的幸福论和结果主义站在彼此的两极。这两极中的第一极将自我提升到首要地位,因为只有自己的福祉才是一个人的终极目标;相比之下,后果论在另一个极端将自我贬低到它不比任何其他个人更需要关注的地步。弱的不偏不倚主义者试图占据一个中间位置。
4.3 内格尔和非个人立场
在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另一种不偏不倚性的概念,以及关于利他主义的合理性的新论点。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1970年)中,他试图削弱心理利己主义(如上文第2.1节所定义的强形式)和它的规范性对应物(有时称为“理性利己主义”或“伦理利己主义”),后者认为人不应该直接关心他人的利益。伦理利己主义者认为,间接关心是合理的:他人的利益可能有助于自己的利益,或者一个人可能碰巧对他人有一种感情上的依恋。但根据伦理利己主义者的观点,如果没有与他人的这些偶然关系,一个人就没有理由关心他们的福祉。
内格尔怀疑是否有人真的是心理利己主义者(1970:84-85),但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反驳伦理利己主义,表明利他主义是对行动的一种理性要求。他的想法不仅仅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为他人着想而帮助他人;也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是因为我们作为理性人需要从纳格尔所说的“非个人立场”来看待自己和他人。正如他所说:“要完全承认他人是人,就需要把自己看作是与世界上一个特定的、非个人的、可具体化的居民相同的概念,与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居民相同。”(1970: 100)
内格尔把非个人化的立场比作把一个人生命中的所有时间视为同等重要的审慎政策。一个人有理由不对自己的未来冷淡,因为当下的时刻并不只是因为存在而更有理由。同样,他认为,一个人有理由不对其他人冷淡,因为某个人是我这一事实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我而更有理由。像“现在”和“以后”、“我和不是我”这样的术语,并没有指出任何具有理性差异的区别。以后的时间最终会变成现在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因为未来是未来,就对未来打折扣是武断和非理性的。因为某人是我而对他的好处给予更大的重视,也是同样的非理性。
按照内格尔的概念,“非个人立场”是从世界之外看世界,它剥夺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哪个人的信息。(用内格尔1986年的书名来说,这就是“本然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或后果主义者——不需要将善最大化,但可以遵守权利原则的约束。但从非个人的角度来看,某些原则是被排除在外的:利己主义是,以及任何其他给予一个人或团体不被所有其他人共享的理由的原则。例如,如果有人有理由避免痛苦,那一定是因为痛苦——任何人的痛苦——都是要避免的。所以,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我有理由避免痛苦,但其他人却被允许对我的困境无动于衷,就好像这种痛苦不是一种客观的坏东西,这种东西只给感受它的人以反对的理由。纳格尔称这种理由为“客观的”,与“主观的”形成对比。帕菲特在《理与人》(1984)中谈到了“主体相关的”和“主体中立”的理由,随后内格尔自己也采用了这些术语。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对利己主义的批判是基于这样的论点:所有真正的理由都是主体中立的。
内格尔的立场和功利主义的共同点是一个与理性利己主义的自我中心世界相反的视角:从这个无自我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只是浩瀚的道德主体宇宙中的一个小部分,每个人都不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或更有价值。我们的常识观点,从我们的内在生活向外看,使我们陷入一种巨大的孤僻——一种淡化或忽视我们只是一个不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的个体的倾向。我们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而这只能通过退后一步来纠正,把一个人的特殊个体从我们的画面中剔除,并对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对方做出一般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应该做某事时,一些相关的要求也会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一些“应该”的声明适用于每个人。
内格尔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为什么自我利益不会经常被代理人中立的理由所淹没。如果任何人的痛苦都对所有其他道德代理人提出了某种要求,那么一个人的痛苦就是所有人的问题。正如内格尔在《本然的观点》中所说,(用“客观立场”这个词来表示非个人立场)。
当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问题不是价值似乎消失了,而是有太多的价值,来自每一个生命,淹没了那些来自我们自己的价值。(1986: 147)
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从其他人的处境中产生的理由的分量是非常小的,而且随着它们的增加,分量也越来越小。因此,可以说,它们并不经常超过自我利益的理由。但这将是一个特别的规定,与利己主义者关于他人的利益没有独立权重的论点只有一点区别。很难相信我们被迫在伦理上的利己主义(它说只有自己的痛苦应该是自己的直接关切)和内格尔的不偏不倚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每个人的痛苦都应该对我产生影响,因为别人的痛苦和我的痛苦一样糟糕)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对我们没有利他主义的要求,后者则要求太多。
4.4 感性主义和同胞之情
一些哲学家会说,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关于利他主义的方法在道德动机中缺少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成分。人们可能会说,这些方法使利他主义成为一个头的问题,但它更多地是一个心的问题。利他主义者可以说我们应该有一定量的同胞情感,但通过给出一个利己的理由来证明这种情感反应是合理的。结果主义者似乎在我们的道德思考中没有为我们对特定个体的友好情感和爱留下合法的空间,因为这些情感往往与增加世界上善的总量的项目相抵触。软的不偏不倚主义者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被他人的善所感动,但那只是因为有一条道德规则,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要求我们这样做。所有这三种方法——因此反对意见认为——都过于冷酷和计较。它们要求我们按照一个公式或规则或一般政策来对待他人。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可能被一种方法抓住,这种方法从如何对待他人的一般规则开始,并仅仅通过应用该一般规则来证明对待每个特定个体的某种方式是正确的。
如果有人回答说,对他人的利益有情感上的反应是让自己给他们需要的援助的有效手段,那就错过了这个批评的重点。(例如,结果主义者可以说,这一学说确实要求我们在对特定个人的友好感情和爱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因为从长远来看,由这种感情巩固的关系可能会导致比冷漠的关系更多的善恶平衡)。但是,上一段提出的批评的辩护人会回答说,一个人对他人的好坏的情感反应可以独立于一个人的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的有效性而被评估为适当。当我们对某一个人的痛苦感到同情时,这种反应已经是合理的了;另一个人的痛苦应该引起这种反应,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适当的反应。作为一个类比,考虑一下对所爱之人死亡的适当反应;这引起了悲痛,而且应该这样做,尽管悲痛不能消除一个人的损失。同样,可以说利他主义的情感是对他人善恶的适当反应,与这些情感是否导致结果完全无关。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是否为他人的利益做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一个人应该减轻他们的痛苦,寻求他们的福祉;这是因为这是一个人对他们的感情的适当行为表达。如果面对他人的痛苦,一个人没有感觉,也不提供帮助,那么他的反应的根本缺陷是他的情感冷漠,次要的缺陷是由这种情感缺陷引起的不作为。
根据这种对利他主义的“情感主义”方法,“为什么要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而行动?”这个问题不应该通过呼吁某种不偏不倚的概念或某种幸福的概念来回答。这并不比试图通过不偏不倚或福祉来证明悲伤的合理性更好。多愁善感的人只是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个或那个人(或动物)的处境正确地唤起了某种情感反应,而我们给予的帮助是这种情感的适当表达。
5►
康德关于同情心和责任
为了评估同情心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考虑一下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是有帮助的。他指出许多人的灵魂是如此富有同情心,以至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虚荣心或自我利益的动机,他们在传播周围的欢乐中找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4:398)
他决不是蔑视他们——相反,他说他们“值得赞扬和鼓励”(4:398)。但不是最高的赞美或最强烈的鼓励。
他说,他们不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的动机“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这是因为他们所行事的“准则”“乏这种不是出于倾向而是出于责任的行为的道德价值“(4:398)。康德的意思是,这些人在帮助别人时并没有遵循一条规则——一条在理性上为所有人所接受的规则,根据这条规则,所有处于这样那样情况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因为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这样那样的情况”一词是对笼统地说明这些情况的短语的一个定位。) 这些富有同情心的人是在情感的基础上行动的:他们为别人的不幸感到痛苦,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康德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但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人帮助他人的唯一或主要的理由。
康德通过想象这些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中的一个人的转变来阐述他的主张:假设某人的不幸给他带来了悲伤,使他对他人的感情熄灭了。他仍然有能力“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但现在“他们的逆境不再刺激他”。他没有感觉到帮助他们的“倾向”,但还是这样做了,仅仅是因为他认为他有道德上的责任这样做。康德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行动就有了“道德价值”——而他们以前是没有的。他的动机现在是“无可比拟的最高”——不仅比以前更好,而且因为它现在是一个道德动机,它有一种优先于其他各种动机的价值(4:398)。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如果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人的痛苦,并为之感到痛苦,他可能不是出于最令人钦佩的动机。例如,如果你听到有人在哭,这导致你去帮助他,你的动机可能仅仅是想睡个好觉,如果他继续哭,你就不可能有好觉。减轻他的痛苦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这只是让他安静下来的一种方式,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一些安宁。我们可以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但你这样做不值得任何赞美或钦佩。但这远远不能证明康德的主张。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悲行为,因为你关心的不是别人的痛苦,而是他的哭泣,而且只是因为这让你感到痛苦。
在我们接近康德所讨论的那种情况之前,从事一个由于罗伯特·诺齐克(1974: 42-5)的思想实验会有帮助。他想象了一个“经验机器”,在这个机器里,神经科学家操纵你的大脑,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你选择的任何经验。这些体验将是虚幻的,但它们可以像你选择的那样逼真、丰富和复杂。例如,你可以进入机器,以获得与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模一样的体验;你将躺在一张桌子上,你的大脑与机器相连,但你将完全像面对巨大的危险、风、冷、雪等等。诺齐克声称,我们不会选择插入机器,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经验成分之外还有很多价值。
考虑到这个装置,让我们回到康德的慈悲的灵魂,他们“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虚荣或自我利益的动机,……发现在他们周围传播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快乐”。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插入体验机,然后在他们看来,他们好像在“向周围传播快乐”。事实上,他们不会帮助任何人,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好像在帮助别人,这将使他们充满喜悦。显然,那些在这些条件下进入机器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拒绝了这个提议,而宁愿在实际帮助人的过程中找到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看起来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找到快乐,那又如何呢?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为某人提供以下选择。(a)你将在机器中体验到巨大的快乐,想象自己在帮助别人;(b)你在机器外体验到的快乐较少,但那将是在实际帮助别人时获得的快乐。一个真正有同情心的人将选择(b)。他将放弃一定量的快乐,以便为他人所用。而这当然有一些令人钦佩的地方。
然而,根据康德的观点,在这个真正有同情心的人的动机中仍然缺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他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在自己的福祉中做出一些牺牲。他帮助别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不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他会违反一个道德规则,使他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促使他帮助别人的原因仅仅是他倾向于这样做。如果他不喜欢帮助别人,他就不会这样做。
我们应该同意康德的观点,即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拒绝帮助另一个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无论这个人是否对他人有同伴的感觉。例如,假设一个孩子需要被送到医院,而你恰好可以在付出一些小代价或给自己带来不便的情况下这样做。虽然这个孩子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但你是一个觉得孩子可爱的人,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此,你心甘情愿地陪同孩子去医院。你对孩子的爱是令人钦佩的,但你仍然会受到批评,如果这是你帮助这个孩子的唯一动机。根据假设,在我们想象的情况下,拒绝是错误的——然而,根据假设,拒绝的错误性并不是你的动机之一。
但康德的观点适用范围有限,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为他人着想而帮助他人是令人钦佩的,但不是一种道德义务。例如,假设一个小说家每天从她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为她所在社区的盲人读书。她没有帮助这些人的道德义务;她帮助他们是因为她爱书,她想把她在文学中获得的快乐传播给其他人。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她的兴趣会发生变化--她可能不再写小说,她可能不再从为他人读书中获得乐趣。这样她可能就不再自愿为盲人读书了。康德必须说,这位作家提供的帮助不值得我们“尊敬”,“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因为她的行为是出于倾向而不是责任。但扣留这些赞美之词是不可信的。作者给别人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她的事业或她自己的幸福。虽然她喜欢给别人读书,但她可能认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写作项目上对她来说会更好。她做出一些牺牲是因为她相信,如果她能把她在这些书中得到的快乐灌输给其他人,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当然,她的动机具有该术语的正常意义上的“道德价值”:她采取行动的原因是为了帮助他人。
回顾康德的思想实验,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遭受了严重的不幸,使他对他人的感情全部熄灭。他仍然能够造福他人,而且他仍然有强烈的责任感。康德似乎在暗示,如果这样的人继续“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因为他看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那么他身上根本就没有道德缺陷。相反,他的动机是堪称典范的,因为它具有“道德价值”(与那些被倾向性和同伴情感所感动的个人的动机不同)。当然,康德是对的,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他经历了严重的不幸而降低对他的评价——假设这些不幸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说,别人的逆境“不再搅动”这个可怜的灵魂,而且他大概会补充说,这种情绪状况也不是这个不幸的人的错。但是,即使这个人在情感上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与他人的关系受到损害也是事实。他无法对他人做出应有的回应。由于缺乏向他人传播快乐的倾向,当他承担履行促进他人幸福或减少他人不幸福的责任的项目时,他将以一种没有快乐的、尽职的方式进行,从而损害了他与他人应该有的关系。例如,如果他自愿为盲人阅读,他将无法向他们传达对文学的热爱——因为他自己在阅读时感觉不到“内在的快乐”,并且由于自己的痛苦,没有帮助他人的倾向。当他收到成年子女不幸的消息时,他不会以同情或怜悯来回应——这样的消息只会让他感到冷漠(尽管他将履行他的父母职责,如果他的援助是道德上需要的)。因此,说这个人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缺陷是合适的。他缺乏对他人应有的行为动机,也缺乏对他人应有的情感。
6►
重新审视感性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梳理前面几节中被称为“感性主义”的一揽子想法,并认识到有些想法比其他想法更合理。
首先,我们应该接受感性主义的论点,即一个人的感情可以根据其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因果影响以外的理由被评估为合适或不合适的。例如,我们应该关心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的事情,即使我们无法帮助他们;这种情感反应是合适的,因为它是成为一个好父母的一部分。这一点使我们可以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应该努力抑制通常是适当的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有责任为许多受苦的人提供服务,如果他让自己不感受到合适的情绪,那么他可能会更有效地帮助他们。例如,一个在战区工作的护士,如果她暂时训练自己,在听到伤员的呻吟和哭声时,不要有什么情绪,可能会拯救更多生命。她有理由感到同情,但这一理由被采取有效行动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的更有力的理由所压倒。
与此密切相关的情感主义观点应该被接受,即帮助有需要的人,但以明显的冷漠、无感情或敌对的方式去做,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有缺陷的反应。
4.4节中与感性主义相关的第二个观点是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不能被一种方法所掌握,这种方法从如何对待他人的一般规则开始,并且仅仅通过应用这种一般规则来证明对待每个特定个体的某种方式是合理的。
这句话的真理内核是,我们生活中一些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能通过遵循规则来获得。我们不会通过应用一个关于我们应该与谁相爱的一般原则、标准或准则来与人相爱。我们对数学、历史或网球的热情,不是通过将这些追求视为我们所关心的更普遍的东西的具体实例而产生的。我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一些组成部分,只有当它们自发地产生于对世界或其中的人的可爱特征作出反应的情感时,我们才能得到。
但这为按照我们接受的规则待人接物的项目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为这些规则经得起我们的理性审查。例如,如果(但只有在)我们对折磨某人有一种未经训练的负面情绪反应时,建议我们应该放弃折磨他,这将是荒谬的。关于酷刑,我们需要回答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否存在酷刑是合理的情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问:什么是酷刑?)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我们要推理出一个一般的政策--一个规范使用酷刑的规则,无论多么简单或复杂。当然,这样的规则应该是公正的--它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单一规则,而不是为我们所属的某些国家或派别的利益而定制的。
这一点也适用于有关日常规则的问题,这些规则制约着诸如守约、撒谎、偷窃和其他类型的可疑行为。在这里,我们也正确地期望对方有一个一般的政策,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一个承诺是自由作出的,这通常是遵守承诺的决定性原因;一个只有在他对这样做有积极的感觉时才遵守承诺的人,不会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正确地对待他人。(关于反对的观点,见Dancy 2004; Ridge and McKeever2006)。
当我们问及慈善捐赠的适当基础时,关于我们的情感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第三个问题出现了。例如,考虑到某人向一个致力于抗击癌症的组织捐款,他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母亲死于癌症。他的礼物是他对她的爱的表达;当然,它的目的是为他人做好事,但这些人被选为受益人是因为他认为减少这种疾病是他对她的感情的适当表达。功利主义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形式的利他主义,因为它的前提是,慈善行为和其他一切行为一样,只有在做了最多的好事时才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钱捐给其他人道主义事业,分配给癌症研究的钱会做更多的好事。但是,如果不预设功利主义的真理,就不难为根据自己的感情归属选择一个慈善机构而不是另一个的做法进行辩护。如果友谊和其他爱的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适当的地位,即使它们不能使善最大化,那么感情就是利他主义的适当基础。(关于反对的观点,见Singer 2015)。
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决定是否帮助这个人或组织而不是那个人或组织时,跟随我们的感情是永远正确的。假设你属于一个致力于减少溺水事故死亡人数的团体,而你正在前往这个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的路上。如果你错过了这次会议,让我们假设,该组织将不得不暂停其业务许多个月--结果是溺水事件的数量仍然很高。在你的路上,你经过一个有溺水危险的孩子,他哭着向你求救。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你去救这个孩子,要么你去参加会议,从而拯救更多的人免遭溺水。当你听到这个孩子的呼救声时,你不能不在情感上做出反应;如果你与他擦肩而过,那将是冷酷无情和斤斤计较的,即使你这样做将会拯救更多的人。你应该怎么做?
你的情感被孩子的哭声完全唤起的事实,与上一个例子中儿子对离世的母亲的爱一样,对这个问题没有影响。溺水孩子的哭声让你充满了同情心,但他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选择是,是帮助一个陌生人(牵动你心弦的人),还是帮助许多陌生人(你现在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人)。如果认为情感在利他主义中起着适当的作用,当它是长期和有意义的纽带的表达时,而当它是对陌生人的哭声的短暂反应时,这并不是不可信的。
7►
结论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理由怀疑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而且应该是利他的。到什么程度呢?功利主义者和后果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个是对每个人(或每个有生命的生物)的利益给予同等的重视,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普遍利益的一个小部分。如果这超过了对我们的要求,那么更好的选择不是退缩到另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相反,多少利他主义对一个人来说是合适的,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状况。
利他主义不一定令人钦佩。只有在为他人着想的情况下,利他主义才值得钦佩——只有当一个人旨在为他人所做的事情确实有利于那个人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寻求他所认为的利益,但却错误地认为什么才是对他人真正有益的,那么他的行动就是有缺陷的。利他主义只有在与对福祉的正确理解相结合时才是完全令人钦佩的。
那些不为他人着想而关心他人的人有什么问题呢?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人由于缺乏利他主义的动机,他们自己会变得更糟。这是利他主义者必须说的,而我们并没有反对利他主义的这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那些从来没有利他主义或利他主义不足的人中,存在着理性的失败。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利他主义或不够利他主义的人,除了当他们应该关心自己以外的某些人而没有那样做时,我们不应该假定,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注: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王子笔记,原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JK9QeyMmAzX3CbDtxMtyg。
责任编辑: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