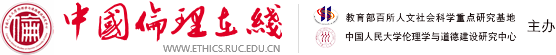邹贵波:中国精神:伦理情怀、时代际遇与逻辑建构
摘要: 在世界文化高地与文化话语权争夺战中, 解构中国精神并且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重新建构中国精神, 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中国精神作为“生成性”的概念, 要使其达到融合性阐发的作用, 则需要厘清其中蕴含的伦理情怀, 打开时代际遇的“天窗”, 把握现实建构的逻辑路径。
作者简介: 邹贵波,布依族,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阳明学研究。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 理解一切。”[1]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意识积淀, 是中华民族谋求永续发展及持久繁荣而形成的文化精髓, 它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饱含东方特色、浓郁历史文化特点及民族主义色彩, 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得”与“失”, 蕴含着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经过时间检验的道德传承、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每当中华民族陷入乱世的泥淖中时, 中国精神总能摆脱一切“前定本质”的规定, 彰显未来的“生成”品格, 利用“永恒在场”作用于文化的坚守、拱卫和开新之中, 彰显出一种如同王夫之“残灯绝笔尚峥嵘” (《病起连雨》其二) 的风骨以及现代新儒家基于“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的求索精神。在世界文化高地与文化话语权争夺战中, 解构中国精神并且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重新建构中国精神, 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中国精神作为“生成性”的概念, 要使其达到融合性阐发的作用, 则需要厘清其中蕴含的伦理情怀, 打开时代际遇的“天窗”, 把握现实建构的逻辑路径。
一、中国精神:伦理情怀之本然阐释
(一) 中国精神蕴藏着文化忧患的基因解码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潜意识, 这种潜意识不仅出自文化本能, 而且显现文化元色和文化基因。”[2]中华文明的潜意识就是对伦理道德一如继往的文化忧患, 这种忧患与紧张伴随着中华文明实践活动的推衍而强化, 进而衍生出“克制”文化忧虑的精神元素。这种精神元素在外界的强烈刺激及引导下, 生成精神基因, 成为中国精神的依附。“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3]在文化忧患的“孟子范式”中, “失道”并不是唐吉诃德式的臆想出来的“幻影式搏斗”, 其内蕴的“超历史性”和“无条件性”成为“天道”与“地道”相融通的异化力量。因此, 孟子以“教以人伦”来缓解因“纤毫毕现地描绘未来”而导致的终极紧张。文化忧患只是中国精神潜意识中文化密码的一部分, 它还携带更深刻的基因意义。
1.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是不变的。
时光的推演、外族的入侵, 改变的只是东方大地物质的形态, 而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则以“颗粒”方式驻存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 文化忧患意识在和平或战争年代, 都以其不同形态发挥着基因稳定性的作用。
2.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具有自我复制的功能。
在中华文化经历“历时性”发展与“空间性”扩展时, 中国精神的内核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新的时代价值, 并且构筑起具有强大吸附性的“文化圈”, 利用文化引力实现横向拓展。
3.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在与环境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变化。
中国精神作为“历史叙事”与“任意叙事”的“事后阐释”与“建构整合”, 具有遗传性、稳定性等特性, 但“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 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4]。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之核心结构、元典精神或轴心文化的基础上, 在“新时代”这个历史起点上, 发生着革命性、时代性的变化。孟子“人之有道”所含“—近于禽兽”“—教以人伦”的辩证体系, 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鉴定, 形成了中国精神文化忧患的真正完整表达和文化自觉。百年前,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曾预警:“伦理之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中国文人的“伦理觉悟”与世界文明风情中的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 其不仅代表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而且具有“最后觉悟”的意义, 完成此“最后觉悟”, 才使得中华民族的“精魂”得以实现“文化自立”并庄严而完整地履行其文化使命。中国精神自孕育之日起, 就饱含着道德忧患和道德焦虑, 这是东方文明一以贯之的文化胎记和标识, 为中华文明后世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调。
(二) 中国精神蕴藏着向上向善的文化本性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彰显了中国精神向上的文化本性。“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阴与阳的辩驳催生万物萌发, 而两者博弈的结果则趋向于阳, “阳为上”“阳为善”。“阳”孕育了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 继而, 有“良知”的国人发出“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振兴中华、一往无前”的呐喊, 对国家的责任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终极任务”, 无论是和平繁荣年代还是战火纷飞的岁月, 始终“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向上的文化本性还表现为“勤”,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它勤劳的DNA仍旧完整如初”[5]。这个“精神自我”摆脱德谟克利特的强决定论的铁笼, 克制意志软弱的桎梏, 在“我思”“我欲”“我悦”三者逻辑循环与顿挫中, 通过“共通感”实现“知其应然”与“行其应然”的统一。如果说西方道路由“工业革命”开辟, 那么“中国道路”则由“勤劳”开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 中华民族能重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离不开中国精神之勤劳向上的精神基因, 正如阿里吉所言:“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 (趋同) 而不是相反, 奇迹才能继续下去”[6]。拥有向上之心, 中华民族方可在重大历史拐点处驱逐外侵而实现民族独立、改革创新而实现民族富强。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彰显了中国精神向善的文化本性。在“人”的本质的争论中, 古人提出人“本体”内涵的仁、义、礼、智四端, 认为“善”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本体论承诺”。人的“良知良能”作为人之为人的本然“功夫”, 是人能弘道的逻辑推演。若人剥离了“善”, 则“祸福无门, 惟人自召” (《太上感应篇》) 。达成“至善”与“共善”是中国儒学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 其终极价值在于未来的“非在场化”, 意味着“不站在对面”和永远向可能性敞开, 意味着对未来无限追求的理念与精神。儒学在其生成场域中经历了由“至善”向“共善”的嬗变, 无论是“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争论, 或是“求善”与“体善”的芥蒂, 其伦理心境皆为“人皆求善”。从《易经》的“善不积, 不足以成名;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到《道德经》的“善人者, 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 善人之资”, 再到《论语》的“见善如不及, 见恶如探汤”。这些至理名言成为中国精神之源泉, 浸透、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善”中取、向“善”中去。
(三) 中国精神蕴藏着国家认同的伦理底线
中国精神的历史镜像蕴含着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与文化性的民族主义两种生成范式。因此, 在分与和的历史双重变奏中, 无论这两种范式谁占据上风, 都秉持着个体性、国家性与民族性三者合一的理念。一方面, 中国精神将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中国”当作一个有机体。无论是在国家构筑的雏形阶段, 还是在民族融合的萌芽阶段, 中国精神作为国家伦理及伦理期待, 其折射的均是一个民族“圆融”的精神状态;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各民族无论以何种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无论其主导思想如何纷繁复杂, 其秉持的核心观念均是“合多为一则为国”, 只有“国”才能发挥凝聚人心、稳固社会的作用, 只有“国”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由“强”向“善”的嬗变, 只有“国”才能体现出“‘我’和‘我们’的种族相似性和共性”[7]。从世界精神文明的发展及交往史中可以探知, 中国精神独具特色的气质始终与国家相伴相生,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各个阶段, 以其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力量为国家发展鼓劲、打气, 中国精神的核心理念与国家认同的价值秉性如河海之系, 同出一源、相融相生。另一方面, 中国精神之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民族品格、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情怀的诞生及延续来源于对民族的认同。当然, 此“民族”并非独立的各个“小民族”, 而是具有身份标识意义的中华民族。只有形成这种“隐性精神力量” (即中国精神) , 才能探知民族自我认同的根与源, 搭建起国家认同的价值与实践基础。概念性的“中华民族”与意义性的“中华民族”无论如何界定, 其最终的认定标准均是基于民族类属特征的国家精神。具有特定文化气质的中华民族只有形成民族属性、生成民族概念、达成民族协议、构建民族逻辑, 方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与心理结构, 进而在民族认可基础上形成具有国家认同伦理底线的中国精神。国家认同来源于历史的逻辑编排以及熔炉式的文化生成, 其核心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中国精神只有拥有国家认同之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域, 才能实现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印记的情感体认和理念认同。
二、中国精神:时代际遇之实然逻辑
(一)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的需要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是对文化视域下民族复兴道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理论解读与实践指引, 其对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推动文化振兴具有时代意义。建构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精神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的现实需要。
1. 中国精神是新时代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支撑。
近代以来, 无数仁人志士追寻的“中国梦”在与当下的“新时代”发生碰撞后, “梦”成为可触及的现实。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是人民群众, 而最强的动力则是让人民群众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8]13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秉性与民族品格, 不仅可以让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历史的永续, 更能让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注入自觉、自信与自强的意识, 继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2. 中国精神是新时代走好新征程的精神动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间表、路线图已经绘就, 实现民族复兴的图景已经清晰, 但建成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不仅要面对国内的发展困难, 还要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阻挠。在这条充满荆棘的新征程中, 离不开中国精神强大的推动力, 只有建立起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自信, 才能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 让社会意识成为社会共识, 铸就勠力同心、砥砺奋进的意志合力, “为文化自强‘安心立命’”[9];才能发挥文化的导向力, 挖掘历史的意义、探究文化的价值, 让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意义都凝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发展路径上;才能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让家国思想、人格理想、知行方法等精神本体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新时代中的每个中国人, 从而彰显文化的感染力, 实现“本体”与“功夫”的交融。
3. 中国精神是新时代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的深厚基石。
近代以来, 人们经历了从精神自负到精神失落的转变, 诸多的历史原因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度不自信, 这种不自信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最大精神掣肘。要破除“西方价值至上”的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及西方“普世价值”神话, 掩耳盗铃的方式只能适得其反。我们只能直面现实并迎难而上, 重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民族禀性、价值信仰与心性观念, 利用“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 增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8]15。中国精神正是确立中华民族精神独立, 重塑中国人民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特精神标识。
(二)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深发展的需要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螺旋递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凝聚着一统、厚德、包容、勤俭、克己、坚韧的传统精神元素。在“新时代”这个全新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新模态的中国化, 离不开中国精神的原动力、引导力、助推力、加速力。
1. 理性、宽容的中国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接纳。
马克思主义内蕴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思想内核让众多“内敛式”的民族望而生畏。中华民族倡导的“内圣外王”理想诉求、“志士仁人”理想人格、“修齐治平”行为模式, 彰显的是实用主义与人文情怀相统一的理性精神, 正是这一精神让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中国人从纷繁复杂的异域文化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遇到的与儒学的汇通融合问题以及在中、西、马对话中话语方式的圆润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古今、中西之争中, 中华民族总能以超乎寻常的博大胸怀和宽广眼界来接纳马克思主义, 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到金岳霖的“道论”, 无不彰显了中国精神宽容的文化本性, 同时也成就了儒、释、道三教圆融为一的文化格局与文化奇迹。
2. 务实、变革的中国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融会和运用。
当马克思主义被中华民族所掌握并成为思想武器后, 中华民族在坚持在其“源”的基础上, 使其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递嬗演进, 让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 让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添上中国元素、绘上中国色彩。在“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影响下, 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中国化都与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 我们也都能“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2]。这种成功实践的根源是中国精神内蕴的务实与变革精神。
3. 革故、创新的中国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历史的车轮并不会陶醉于当下的浮华, 发展与变化永远是历史的秉性。中华民族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传统就是中国精神“返本开新”的重要源泉。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而是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只有秉持革故、创新的中国精神, 不断发展新的马克思主义、探索新的马克思主义, 才能持续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
(三) 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力的需要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伟大革命”[14]1, 也是唤起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自觉的“伟大觉醒”[14]2。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 若把改革看为“过去时”, 则“没有中国的今天更没有中国的明天”[14]4。“新时代”描绘的美好蓝图需要改革来完成, 需要依靠中国精神凝聚改革共识, 以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中国精神锤炼中国改革的领导力量。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如何持续激发进取意识、进取精神、进取毅力, 是作为中国改革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所必须完成的“必答题”。在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中国精神锤炼改革能力与改革思维, 坚持自主性, 以中国实际为基点、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国家富强为主线, 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循环中站稳脚跟, 成就超越自我的历史业绩;必须坚持首创性, 形成中国特色, 具有中国品格, 让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走向世界, 成为世界未来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最优选项;必须坚持先进性, 以“历时”与“历史”的标准判断改革的得失, 形成符合时代特质、彰显民族意义的改革方法、改革思维与改革模式。改革任务越繁重, 越要保持攻坚克难的冲锋姿态, 越要树立改革必成的坚定信念, 满怀“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 让中国改革的领导力量沐浴中国精神之光, 让中国精神在时代改革中愈发明亮。
2.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改革的支持力量。
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 必然伴随着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 改革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征程中遭遇的困难与困境需要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方能得到解决、突破并实现跨越发展。《尚书·泰誓》言道:“受有亿兆夷人, 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 同心同德。”中国精神内蕴着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当改革的目的指向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改革成为人民群众毫无置疑的共识与愿景时, 当改革的落脚点为“促进社会公正、增进人民福祉”[15]时, 强大的社会合力将推动改革向新阶段、新层次、新境界拓展, 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重建中国制度文明。中国精神将引领中国人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不畏强权、自力更生并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威严, 引领中国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奋斗、拼搏创业并彰显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强, 引领中国人民在新一轮改革浪潮中稳立潮头、开拓进取,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注入持久动力, 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红利。
三、中国精神:现实建构之应然路径
(一) 中国精神建构的出发点:精神自觉
后现代性、后物欲时代的运作方式以“知性因果关联”与自利的原子式“自我”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目的论世界观”与价值本体秩序, 社会价值本体的建构从“诉诸逻辑力量转向倚重感性力量”[16], 精神的世俗性与高贵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整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张力相互排斥, 使得社会模块由“生命过程”嬗变为“生产过程”。中国精神“自由王国”的建构须使“‘名称’上升为‘概念’”[17], 从本源上回答“终极性问题”。
1. 中国精神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现实利益的契约式同意。
当文化创新与文化革命衍生出来时, 无论是近代“德先生”与“赛先生”对于批判封建专制、重审传统文化、反思传统道德伦理的深远影响, 或是历代饱含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关于民族振兴的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大理论观点, 都是中国人的“本真”与“本然”抉择。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互补互融的独特结构, “礼失求诸野”与“文胜质则史”相互激荡、僵化腐朽与生机活力相互碰撞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化, 彰显的是现实的“普遍性意义”。当牟宗三开出“自我坎陷”的药方, 林毓生、杜维明等人提出儒学的创造性转换时, 中国精神衍化的文化自知、文化自尊、文化自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时空转化, 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日常意识”与“社会心理”成为人们隐性的精神契约。中国精神每次“价值分化”及“价值共识”都是全体中国人民现实利益的契约式同意, 修复了“本体世界—生活世界—个体世界”断裂的精神链, 夯实了精神自信的根基。
2. 中国精神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道德式承诺。
中华文明作为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重要文明类型之一, 其不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 更不是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 相反, 它饱含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礼—仁”结构所蕴涵的伦理本位的文化价值形态是“家—国”一体, 其“普遍性的形式”与“普遍性的意义”相融合后, 形成的价值理念并非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质的纯粹“普世价值观”。该价值理念通过人们的精神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 从而获得“现实性”意义, 其追求的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路径, 而是重新审视与建构国与国之间经济生活与社会文化生活密不可分的“总体性的结构关联”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价值互通性, 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道德式承诺。精神自觉的意义不仅在于探求其中的普遍性真理, 更在于在自我审视中实现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转换及意义彰显。由史观之, 古老文明“往往因承受沉重的文化之累, 深陷文化自恋而墨守陈规”[18], 中华文明史中书写的赞誉之词在现时代也可能会演变成为“糖衣炮弹”。但是, 中华文化传统“传不习乎”的自我省思, 形成了中国精神内在生发与自我更新的传承逻辑与实践路径。因此, 精神自觉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自我觉悟和高度体知, 不仅仅要实现“个体”与“实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相互转换, 并将之聚合为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之间生态整合的实践形态, 更要防止封建糟粕死灰复燃并以辩护式的神秘化“歪曲形式”占领精神高地。
(二) 中国精神建构的驱动点:精神自省
缺乏根基而局限于纯粹意识领域的批判意识是虚假的意识, 缺乏反思而局限于纯粹物质领域的文明形态是脆弱的文明。中华文明能跳出“脆弱文明”的历史黑洞, 实现除旧革新, 离不开“历史主体”生存境域的独立形态。在新时代这个历史阶段, 中国精神想要其思想体系置入社会结构并赋予意识形态以战斗功能, 想要在世界文明中彰显“信仰属性”及“文化公共性”, 就需结合中国传统文明、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性”做出自我精神反思。
1.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明。
世界历史浩浩荡荡, 繁若星辰的文明“或已夭折, 或已转易, 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19], 只有中华文明“屹然独立, 继继绳绳, 增长光大, 以迄今日”[20]。“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2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民族延续与富强之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宝贵资源, 彰显着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互补、易变革新、经世致用、天人合一、民惟邦本等方面的文化品格为社会成员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精神性内化提供了动力。中华文明之止于至善、美美与共、修齐治平、各正性命等价值品格为造就中华文化共同体增添了人文底色。但是, 小农经济导致的思想启蒙缓慢、等级观念强烈、“梦回唐朝”臆想等文化劣根性需要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与自省意识, 建立起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异质落差式互动”模式, 以辨证的思维、坦荡的胸怀开拓“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22]三位一体的提升路向。
2. 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18世纪以来, 西方文明长期占据着世界历史制高点并延续至今, 这与其文化中积蓄的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等积极因子不无关系。从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的理性批判, 从“重估一切价值”到“西方的没落”, 西方文明的“否定”精神使得其“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及巨大的历史意义”[23], 我们需要正视其历史合理性与时空逻辑性。但是, 西方文化“常识层面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层面的世界观”皆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意识折射, 从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资产阶级话语系统的辩护与呐喊皆直指“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策略”[24]。长期以来, 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以“绝对自由”为前提的宗教信仰, 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知识体系, 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都在侵蚀着国人的头脑, 而部分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置若罔闻, 将问题归结为“‘去中国化’不够彻底”[25]。取精华、去糟粕、防渗透才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
3.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6], 其作为我国时代发展的道路选择及“社会转型期的理论再选择”[27], 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需对零零种种悖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杂音保持高度的理论警觉。在其中国化的境遇中, 不仅要“回到马克思、回到文本”[28], 更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诠释与实践诠释, 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文化保持解释的张力。
(三) 中国精神建构的立足点:精神自信
在实践的现实性与文化的传统性上, “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是民族复兴之实践性与时代性的具体概念。其彰显的是“实践演绎”, 以反驳“理性的疲软”和“理性的颠倒”, 作为由实践向智慧方向展开而生成的“实践智慧”, 与“善”或“好”紧密相关。在新时代, 重塑精神自信成为跨越发展局限并从历史根源中展现中华文明“整体善”与“普遍善”的题中之意。
1. 强化文化主体意识是实现精神自信的根本保证。
当世界陷入“生长着的个人主义的时代”[29], 洋奴文化、封建腐朽文化、功利主义文化打着“自由与平等”的旗帜大行其道, 就有人故意夸大封建糟粕的影响并将之视为中华文化“天生的劣根性”, 使得“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甚嚣尘上, 鼓吹“去中国化”、全盘西化, 甚至有人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衡量一切并企图以“活得好不好”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此类思想均源于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铸牢文化主体意识, 不仅要彰显独具中华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人格品性、审美情趣, 更要分享、传播本民族文化, 敢于同“异”和“变”作斗争。
2. 用包容并存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竞争是实现精神自信的必由之路。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动力, 一切以霸权为基础想实现文化“大一统”或构筑文化乌托邦的想法只能随着“太阳城”的倒塌而陷入汪洋大海。全球性文化交汇、交流与交锋此起彼伏, 我们若没有从辩证法的视角去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沟通, 进行“说明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沟通, 仅仅为了实现所谓的“造就社会”而放弃民族的坚守与核心话语体系, 将会让民族意志在弥漫硝烟中分裂成“碎片”, 最终导致价值混乱与价值空场, 而“造就的社会”也只会成为国际文化斗争的牺牲品。中华文化想要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属性, 须在世界舞台上拼搏, 让历史来甄选、让实践来认证, 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转化再造的方式实现凤凰涅槃。
3. 着眼未来的长远发展是实现精神自信的动力之源。
如果一个民族仅能产生物质财富, 而不能传给后人产生物质财富所需要的意识力量, 不能通过“涵养人性”而建构与彰显本民族的哲学智慧与道德魅力, 那么这个民族则不可能避免与各种可能变成“真理”之主张的虚构共谋, 就难以承担起民族延续的历史重任和民族繁荣的使命追求。中国精神的“根”源于东方土地及东方文化, 但其历史使命及历史担当则不能囿于此, 铸就“兴国之光”要需积极建构“世界精神”, “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30]。
四、结语
“根之茂者其实遂, 膏之沃者其光烨。”20世纪初, 罗素曾向世人急呼:“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 现代世界极为需要。”[3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 中国精神以实践智慧成全“智慧的实践”, 其作为主体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统一,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统一, “修德达善”与“太上立德”的统一, 必将产生“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妙用, 这种“家园之感”[32]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源泉和价值支撑。
【参考文献】
[1]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78.
[2]樊浩.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8 (1) :5-14.
[3] 孟子.孟子[M].方勇, 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5:96.
[4]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90.
[5]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 刘曲,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178-179.
[6]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29.
[7]舒隽.文化自信: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J]求索, 2018 (5) :39-4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9]刘波.习近平新时代文化自信思想的时代意涵与价值意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 (1) :97-104.
[10]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69.
[1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34.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62.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5]赵付科, 季正聚.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论纲[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 (6) :29-34.
[16]成长春, 张廷干, 汤荣光.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 2018 (2) :4-25.
[17]孙正聿.辩证法与精神家园[J].天津社会科学.2008 (3) :13-19.
[18]顾銮斋.西方民族精神自觉的本义与逻辑[J].东岳论丛, 2013 (7) :102-103.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7:2.
[2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4.
[21]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 吕乐,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440-441.
[22]邹贵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维图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8 (2) :18-25.
[23]谢地坤.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批判主义[J].哲学动态, 2010 (10) :5-16.
[24]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M].潘亚玲,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12.
[25]王岳川, 胡淼森.文化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83.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332.
[27]房广顺, 郑宗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当代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 2015 (2) :29-33.
[28]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 (3) :81-90.
[29]江畅.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 2018 (4) :4-23.
[30]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 郭小凌,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394.
[31]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6. 154.
[3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 王太庆,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157.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