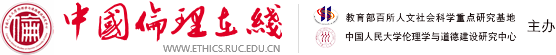武卉昕|“聚合性”与俄罗斯政治伦理的理论和实践
摘要: 从俄罗斯的经验来讲,“聚合性”既是政治与道德、公民社会与“个体道德”、伦理传统与政治诉求、伦理原则与政治决策的同一性,又是沟通上述理论实践范畴的纽带,是含有具体内置物的伦理要素。从当代俄罗斯实施的具体政治策略上,“聚合性”的作用更不能小视。

作者简介:武卉昕,女,1973年10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苏联-俄罗斯伦理学研究,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位专门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学者。教育部“斯拉夫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伦理学十大杰出青年学者。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论文60余篇。《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系统研究苏俄伦理思想史的成果。
摘要:“聚合性”是俄罗斯文化价值空间内的本质性内容,也是独属于俄罗斯的政治伦理原则。在认识论上,“聚合性”的理论发生沿着从历史到哲学的路径展开,并进入伦理学领域。从历史上,“聚合性”缘起“村社精神”,承载“东正教精神”,促成“集体主义精神”,凝聚“俄罗斯精神”。在经验上,“聚合性”既是政治与道德、公民社会与“个体道德”、伦理传统与政治诉求、伦理原则与政治决策的同一性,又是沟通上述理论实践范畴的纽带,是含有具体内置物的伦理要素。在实践上,“聚合性”凝聚人心的情感纽带,是指引发展的价值原则,是平衡利益的实践手段。
关键词:“聚合性”;伦理传统;政治实践
“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是俄罗斯文化价值空间内的本质性内容,也是独属于俄罗斯的政治伦理原则。无论是在罗斯时代还是俄国时代,无论是在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基础属性和根本价值的“聚合性”都对国家发展起隐秘而重要的作用,更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抉择。
一、“聚合性”逻辑释义
从语言学、哲学和伦理学的生成逻辑中能够理解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特质的“聚合性”之民族文化特质、世界观和价值原则。
(一)基于语言释义学的“聚合性”之民族文化特质
奥日科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辞典》对соборность的理解“是许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的精神同一性(общность)”;《大百科辞典》将соборность作为“东正教文化传统中的特殊财产,它区别于新教旨主义的宗教个人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独裁主义,是宗教人士的群体智慧……是统一的、共同的、神圣的自我认知”;《俄罗斯文化百科辞典》认为:соборность代表“完整性、内部丰盈和多数,是由爱的力量聚合成的自由和有限的统一”;《新哲学百科全书》将соборность作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础概念来界定,指出这一概念“意味着宗教或世俗生活中人的自由精神的统一以及在情谊与爱中的交往。此术语属俄语独有”。
综上概念所述,可以看出соборность一词是基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生长起来的民族文化特质,具有文化心理上的“共同”“同一”“聚合”等意义。从词源学角度上看,“соборность”的根词“собор”(“聚集地”“教堂”)和同根词“соборный”(“集合的”“聚合的”“教堂的”)均具有“聚合”“聚集”“聚集地”之意,而“собор”一词本身也具有“因出于一致精神祈望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的含义,后来这一词汇才逐渐衍生出“教堂”之意。所以,将作为东正教文化传承的独有价值的“соборность”一词译做“聚合性”更合适。
(二)基于哲学范畴的“聚合性”之历史—逻辑和世界观意义
遵循文化传播和变迁的规律,基于东正教传统的“聚合性”特质渗透到了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方式引领俄罗斯社会生活,在历史地凝结成为稳定的认知方式后,具有了哲学意义。在宗教视阈内寻找自由的俄国哲学家А.С.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ым)最先正式赋予“聚合性”以哲学意义,“聚合性是人们共同探索真理和拯救之路时基于宗教的自由的统一,是建立在对基督耶稣的一致的爱和神圣的正义基础上的统一”。霍米亚科夫将“聚合性”作为建构公共生活的总原则,即在有限的“自由”和有限的“限制”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平衡并不是“两离”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霍米亚科夫以“聚合性”为理论根基,试图用宗教哲学的方法合理揭示社会关系的辩证特点。
以基督教人学为研究立场的俄国哲学家С.Л.弗兰克(С.Л.Франк)将“聚合性”作为“建立在全体人的交往和全部社会团结基础上的、内部的有限统一”。С.Л.弗兰克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探索大多数人命运和生活的共同性。很显然,С.Л.弗兰克将“聚合性”提炼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内核的层次上。在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家П.А.弗洛连斯基(П.А.Флоренский)那里,“聚合性”更是直接被看成“俄罗斯东正教特殊力量和精神的表达”。当代哲学家В.Н.萨卡托夫斯基(В.Н.Сагатовский)将“聚合性”简洁地表达为“俄罗斯思想的本质、俄罗斯精神的最初直觉”。
看得出,纳入哲学范畴的“聚合性”被赋予了历史—逻辑和世界观意义。“聚合性”在历史上源于东正教,是东正教的价值基础,同时“聚合性”又是在东正教历史演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罗斯哲学的基础范畴,建构了俄国哲学的逻辑范式,即以“聚合性”为精神原点向外伸展;还是俄罗斯民族对待世界的观念原则。
(三)基于伦理学范畴的“聚合性”之价值原则
在认识论上,“聚合性”的理论发生沿着从历史到哲学的路径展开,接着进入伦理学领域。作为俄罗斯精神的实质和东正教的思想基础,“聚合性”具备价值哲学的直接特性。在价值论上,可以用“聚合性”作为标准来考察和评价俄罗斯社会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发展对个人、阶级、人类的意义,包括道德意义。或者直接说,在俄罗斯历史传承和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聚合性”本身被赋予了道德意义。
“соборность”的基本意义在于能将很多人聚合起来的某种精神,或者可以将其看成组织社会生活的某种准则。这种准则毫无疑问是与个人主义相逆的,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致力于将个体纳入群体之中。“‘聚合性’拒绝‘个人幸福’的概念,认为单个人的幸福对于人而言是无法实现的。‘聚合性’从利他主义原则出发,鼓励为公共事业的自我奉献”。当代哲学家季米特利·奥格玛(ДмитрийОгма)将“聚合性”看成当代组织社会关系的协同机制,“对于‘团结一致的人’来说,生活的策略在于形成彼此承认的道德价值体系,完善自己以创建人道的、公正的社会”。事实上,在相当多时候,俄罗斯人将这种“聚合性”等同于“同心同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同心同德”的道德原则维系了俄罗斯历史的完整。
二、“聚合性”的历史源流
从“村社精神”“东正教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俄罗斯精神”的历史流变中能够寻找到培育“聚合性”的社会基础、信仰依托、道德原则和当代价值。
(一)“聚合性”缘于“村社精神”
确切地说,起家于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人的祖先,他们生活的东欧平原以森林为主要覆盖物,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元性社会组织结构的“村社”伴随“砍烧农业”(P124)文明的生成。мир在俄语中有两个基本意义:一为“村社”,二为“世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村社”就是整个“世界”。“村社”从基辅罗斯时代起源,经历了蒙古人(鞑靼人)统治时期、沙皇俄国和苏维埃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村社”制度,作为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维系了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村社”执行集体居住、土地公有、协作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私有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培养了村社成员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他们将自己与村社看成一体,较少注重个人权力,强调整体和谐。村社成员少有个性,自愿与村社结为一体,对于他们来说,“村社是伟人,村社是伟业,哪儿有村社的手,哪儿就有我的头”(Мир-великчеловек;мир-великодело.Гдерука,тамиголова)。组织结构与人民精神二位一体的关系赋予了“村社”以宗法共同体的特性,它让“聚合”在一起的人将同心同德的“聚合性”作为“村社精神”流传下来,直到今天。
(二)“聚合性”承载“东正教精神”
罗马帝国分裂后,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为中心的基督教被命名为东方正教,以示自己正统基督教的身份。公元9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并被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定为国教。这样,基辅罗斯的“先祖”称号再加上拜占庭的荣光使得东正教事实上成为斯拉夫文明的基础。
俄语中的“东正教”(правосравие)从构词角度可以分解为“斯拉夫规范”“斯拉夫权力”“正确的斯拉夫(价值)”。правосравие在旧词当中,还用作俗语,意为“同胞们”,曾用作对俄罗斯民众或一群人的称呼,表示“俄罗斯人民的,俄式的、俄罗斯的”(PP3877-3878)。可见,东正教与俄罗斯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它本身就代表俄罗斯范式和俄罗斯价值,承载俄罗斯精神。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根词собор之本意———“宗教会议”“大教堂”“聚会”等词义中也能看出来,这里的“教堂”就是东正教教堂,因为在最开始,“教堂”(собор)就是东正教教徒们聚在一起商议事情的地方。看得出来,东正教是将人们聚合起来的现实依托,这是它独有的特点。
与其他宗教比较起来,俄罗斯的东正教在历史的流转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特色,如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而不是参与性。这种依附性更多表达了东正教的顺从取悦色彩,它不是离心的,而是向心的、聚合的;再如“神—人”色彩。俄罗斯的东正教永远游走于“神—人”之际,它既不纯粹入世,也不决然出世,它力图弥合神人鸿沟,它是将神性和人性聚合在一起的力量;俄罗斯的东正教纳悦多神教,多神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础来源,后者包纳并聚合了前者,而不是排斥它……
可以说,聚合性在历史上是作为东正教的精神载体传承下来的,直到今天。
(三)“聚合性”促成“集体主义精神”
“聚合性”不是集体主义,但它敦促“集体主义”的形成并通过“集体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聚合性”与俄罗斯民族的公共生活密不可分,在俄国时代,它反对极权和自私的个人主义,在苏联时代,它促成了更加注重人民共同性和精神一致性的“集体主义”的成长,“集体主义”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框架中与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基础高度契合,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事例。
集体主义精神塑造了整个苏联的价值世界。从列宁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强调再到Н.К.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对集体主义的深入论述,从А.С.马卡连柯(А.С.Макаренко)提出集体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到М.И.加里宁(М.И.Калинин)将集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再到А.Ф.施什金(А.Ф.Шишкин)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单独阐释,从1927年集体主义被苏共十五大(XVсъездеВКП(б))采用到1951年将其作为伦理学专业教学大纲中的主体内容(P40)再到1961年被写入《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集体主义都是苏联社会的核心价值原则,这一价值原则一直伴随苏联国家的兴衰。
苏联的集体主义原则虽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也将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但从民族特色上看,苏联致力于集体主义传统与国民生活相统一、集体主义与生产实践相统一、集体主义与专业知识相统一(P44)。在苏联时代,集体主义原则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是单纯的道德原则,而是以价值线索的形式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空间中贯穿下来的同时,将个人和社会聚合在一起,其中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要素被凸现出来。不难发现,在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中,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聚合性”仍与“集体主义精神”相辅相成,同心同德。
(四)“聚合性”凝聚“俄罗斯精神”
“俄罗斯精神”是当代俄罗斯的核心价值。“‘俄罗斯精神’反映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的生活方式,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其生命意义的核心。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数千年的发展敦促了“俄罗斯精神”的形成”。根据这样的认识,学者们将“俄罗斯精神”的本质提炼为“勇敢善良”“合作参与”“自由包容”“休戚与共”“团结互助”等。分析“俄罗斯精神”的本质,会发现这些本质特征都与民族文化上的“聚合性”密切相关。这里的“勇敢善良”中“善良”一词不是“добро”(“善”),而是具有合作意义的“友善”(незлобливость),表达了交往中的非恶意态度,即在群体中以友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合作参与”不仅是交往方式,更是处理个别与整体的平衡手段,这一手段能够保证在共同与个别的有限同一中找到“一致性”;“自由包容”是文化精神的辩证统一体,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包容是限制内的包容,体现了东正教哲学中自由与限制的统一思想,是宗教精神与社会创造相契合的典范;“休戚与共”“团结互助”则更加直接地标明它们内涵的聚合意义。
“聚合性”凝结成当代“俄罗斯精神”。今天,无论抽象的“俄罗斯精神”本质的,还是具象的“俄罗斯精神”的内容,都是被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意识养成的“聚合性”的精神成果,它对于在艰难中跋涉的俄罗斯民族,对于秉持希望之火前行的俄罗斯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三、“聚合性”的政治伦理拷辨
俄罗斯的政治伦理学虽然锋芒独秀却算不上正统规范。政治伦理学在俄罗斯风起云涌是迎合社会制度变迁对新制度进行伦理论证的要求。在政治伦理学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同是:它应当反映制度关系、社会与个体关系、社会团体组织关系的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实现这一认同的基础仍是“聚合性”。
(一)政治与道德的“聚合性”
俄罗斯传统的政治与道德关系具有特殊的一致性。Б.Г.卡布斯京(Б.Г.Капустин)总结了政治思想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道德与政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二者互为对方的“学问”。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研究注重从政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视角出发,论述政治实践中政治和道德的融合可能,将政治伦理学发展为真正的哲学科学。政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同向关系,正如伦理学要为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一样;政治实践中政治与道德的融合是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目的,这样的伦理学研究仍然带有目的论和规范伦理学的特色,从这一点上说,“聚合性”原则功不可没;探讨政治领域中人道主义的生成方法是政治伦理学的主体,而人道主义则恰恰是最具俄罗斯精神特色的伦理价值,于俄罗斯人而言,人道主义从来都既是政治的,又是伦理的。“聚合性”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历久弥新。
(二)公民社会与“个体道德”的“聚合性”
俄罗斯的政治伦理学关注新的公民社会中的道德选择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们通过探索公民自我意识和价值定位形成的途径,即如何从家庭、教育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性建构,最终在“个人—社会—国家”框架下实现“精神—道德—法律”的合理“在位”。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历着政治环境逆转、道德价值观嬗变的命运,从前集体主义的核心道德价值被摒弃,个人主义上升为主体道德价值,国家政治前途和社会道德状况均混乱不堪。如何在困难面前解决问题,让人们在接纳新制度的同时又保有优秀的传统道德,如何在集体主义退隐出价值世界的同时又能把人心凝聚起来?“聚合性”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俄罗斯在寻找非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价值观念,它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能够表达新的价值属性的基础,这时“聚合性”顺势呈现。“聚合性”反对极权,也不肯定无性格的同一,如果把它当成政治正义的话,它是弥合多项要素的有限统一:“聚合性是我们时代的概念,它生长于两种极端对立的体系之下———绝对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集体主义。”“聚合性”是个人和社会的融合,它是价值也是手段。俄罗斯人通过“聚合性”力图填补知识分子和文盲、宗教与世俗、男人和女人、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以形成共同意志。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意识不可能毫无差别,与其说它是个别的,毋宁说它是聚合的”。“聚合性”将个体道德渗入到“公民社会”中了。
(三)伦理传统与政治诉求的“聚合性”
伦理传统必然影响政治抉择,历代各国,概莫能外。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伦理原则与自己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向一致,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渗透。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伦理学在向西方看齐的范式下,仍然有基于自己传统又迎合发展需要的特色,比如“非暴力伦理学”。“非暴力伦理”缘起于东正教的教义,到托尔斯泰那里被体系化。到了苏联社会末期,以А.А.古谢伊诺(А.А.Гусейнов)为代表的伦理学家重新将其作为伦理学研究的主题推广开来。继承了俄罗斯传统宗教伦理的“非暴力伦理学”的兴起是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安的社会心理的本能反应,也是抚慰大众忧伤,防止社会动荡的良剂,更为国家平稳度过动荡提供了帮助。不难理解,在社会制度急剧变革而导致礼崩乐坏的特殊时间内,俄罗斯民族为什么能够在忍耐中扛过来?忍耐、顺从的“非暴力伦理”的传统伦理观念作用不可小视,忍耐、顺从、皈依在文化力学的角度上,都是聚合力,而不是分散力。基于“聚合性”的非暴力伦理传统迎合制度剧变后的平稳发展的政治诉求,这是伦理原则影响制约政治抉择的作用,也是政治抉择依赖伦理传统的范例,二者相互渗透。
(四)伦理原则与政治决策的“聚合性”
伦理原则服务于政治决策,政治决策依据伦理原则行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理论与实践的依据。俄罗斯的“全人类道德”“保守主义”与仿效西方和主权民主的政治方略证实了伦理原则与政治决策的“聚合性”。“聚合性”仍是伦理依据。浸润在民族血液里的“弥赛亚”意识,表现为伦理原则上“全人类道德”,在苏联时代导致了人道主义原则从具体走向抽象。在后苏联时代的初期,基于回归西方民主主要目的,俄罗斯在国家道路发展的选择上极力向西方靠拢。“欧亚一体”的出身背景使其迈向西方的脚步急促而沉重,俄罗斯伦理传统中的“全人类道德”则是它演绎西式政治伦理的舆论托词。“欧亚一体”不但是地缘政治上的纽带,更是文化心理的纽带,其中跨不过的仍是“聚合性”的桥;后来,当俄罗斯自己意识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办法行不通,又开始尝试主权民主的发展范式的时候,伦理学又做出了相应的回复,即保守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的伦理内核依然是以“聚合性”为基础的、保有民族发展底线的发展思路。
从俄罗斯的经验来讲,“聚合性”既是政治与道德、公民社会与“个体道德”、伦理传统与政治诉求、伦理原则与政治决策的同一性,又是沟通上述理论实践范畴的纽带,是含有具体内置物的伦理要素。
四、“聚合性”的当代政治实践
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判断、政治选择和政治决策中,“聚合性”意义重大。“聚合性”是情感纽带,以凝聚人心;“聚合性”是实践手段,以消解矛盾;“聚合性”是价值原则,以指引发展。
(一)“聚合性”是凝聚人心的情感纽带
“聚合性”是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标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面临再次解体的风险。高加索战火纷飞,来自外部的恐怖分子公然入侵车臣。在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几无保障的前提下,在要么坚守,要么永无机会保卫祖国的两难选择中,俄罗斯政府选择了前者。普京明确了车臣反恐的含义———“为了神圣土地的同胞”,与恢复祖国尊严、促进国家发展相比更重要的是“防止俄罗斯再次分裂”。后来,“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不应四分五裂,要‘统一法律空间’,各地区权力一律平等不能搞特殊性”(P278)。通过成立联邦区,实行总统亲自任命和管理的方式统一了地方。如果说,战争和政令是政治手段,那么“聚合性”就是非政治手段,是情感纽带。“聚合性”不但在空间上把人民聚到一起,更拉近了俄罗斯人的心理空间,为政治策略的实施奠定社会心理基础。
俄罗斯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都与凝聚人心的目的相关。整治政党、削弱寡头、治理腐败、抗击外扰……以人民为旨归的“聚合性”在关键时期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在艰难的转型时期,“聚合性”培育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挽回了民族自尊心,也给了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自信心。今天,俄罗斯进入常规发展轨道,这种发乎情感中的“聚合力”能够为国家发展起凝聚人心的作用。
(二)“聚合性”是指引发展的价值原则
新世纪的俄罗斯可谓千疮百孔,社会“乱成一锅粥”,政治腐败透顶、经济空前恶化,社会混乱不堪,百姓孤苦无望……俄罗斯在策略上甚至找不到现实的突破口来收拾烂摊子。那时,“聚合性”起到了树立主导价值、匡正社会风气的作用。
普京上任之初提出的“俄罗斯思想”成为新时期俄罗斯发展的价值坐标。新的“俄罗斯思想”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与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统一体,其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概念、社会团结。普京在接见企业界创新积极分子时表示:“我们想不出其他理念,也不必绞尽脑汁去寻找。除爱国主义外,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其他具有凝聚力的思想……这便是国家思想,它并未被意识形态化,也与任何党派的具体活动无关,它事关整体凝聚力。倘若我们希望生活得更好,便要提升国家之于所有公民的吸引力,令它效率更高。”看得出,普京将爱国主义看成是最具凝聚力的国家思想,它对于公民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此外,树立强国意识,实施国家主义,实现社会团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聚合性”。
今天,俄罗斯的民调结果证实了俄罗斯社会的系列思想回潮:重树民族统一思想、重塑爱国主义、重现集体主义。回潮反映了在“聚合性”作用下俄罗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选择重归人民性、价值构成重现基础性、价值内容重树道德性。无论是民族统一、爱国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有哪一种社会思潮不是被“聚合性”所牵引呢?无论是人民性、基础性还是道德性,有哪一种价值取向不包纳“聚合性”的内涵呢?
(三)“聚合性”是平衡利益的实践手段
欧亚一体的地理位置、联邦制的政治体制、多民族国家的构成、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变都给当代俄罗斯国家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让当代俄罗斯在政治实践中举步维艰,平衡利益、消解矛盾是俄罗斯主要的政治任务,而“聚合性”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
从当代俄罗斯主要社会思潮的发展上看,“欧亚主义”弥合因地域特点形成的“亦亚亦欧”与“非亚非欧”的特色,“爱国主义”聚合民族意识上的“分离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国家主义”平衡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以统一认识为政治目的的反映。
从当代俄罗斯采取的主要政治措施上看,“主权民主”表明了,俄罗斯力图在划清与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叶利钦时代“寡头自由”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俄罗斯历史现实特点的民主之路。一些人更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有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对民主道路的探索,不应割断历史。可见,“主权民主”是由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传承下来的精神品质支撑起来的民主模式,没有了“聚合性”便没有了属于俄罗斯的主权,也更谈不上真正的民主了。
从当代俄罗斯实施的具体政治策略上,“聚合性”的作用更不能小视。人们能在每一年的胜利日阅兵和阅兵之后“不朽军团”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在政府为保护儿童、提高出生率实施的各项措施上,在国家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的法律条文里寻找到传承、统一、团结的印记,触摸到“聚合性”的本质。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