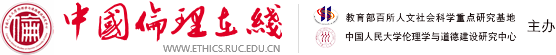杨松: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
摘要: 内在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必然能够激发人们的行为动机,而外在主义认为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生活中出现的“非道德者”现象就是例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内在主义强调,“非道德者”的主要缺陷是其不具有实践理性,因而在面对道德判断时也就无法被激发去行动。但是,内在主义关于实践理性的解读要么与现实有悖,要么是“乞取前提”。为解决这些问题,从道德判断的实践目的入手,像贝德克那样构建一种相对于特定实践目标和社会共同体的内在主义或许是可行之策。
作者简介:杨松,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关键词:道德判断/道德动机/内在主义/外在主义
我们在看一部关于贫困山区的纪录片,结束之后你对“我”说:“应该为贫困的人提供帮助。”然而,当募捐人员真的上门时,你无动于衷。这时,“我”可能会质疑:“你不是说‘应该为贫困的人提供帮助’吗?为何你却连开门都不愿意?”“我”的看法代表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直觉:如果你主张一个道德判断,那么你就有动机去做这一行为。既然你认为有义务去捐助,那么你就应该被这种信念所激发并付诸行动。这种主张在伦理学中被称为“道德动机内在主义”。相反,有一种理论认为,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人们在形成道德判断的同时还因此有动机作出相应的行为,两者的关系只能说是偶然的,我们将之称为“道德动机外在主义”。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元伦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沿着两条路径就该问题展开研究:其一,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其二,通过开展科学实验并分析实验结果的方式,为解读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关注第一条路径,并着重阐述双方争论的三个焦点问题:非道德者(amoralist)、实践理性和道德拜物教(moral fetishism)。
一、非道德者
道德内在主义者的观点并不统一。有的人认为道德动机是道德判断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任何道德判断都具有激发行动的作用;有的人则不强调这种内在关系,而只是认为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任何作出真诚道德主张的人总是有动机去从事相应的行为。前一种观点更多地需要诉诸非认知主义的立场,一旦非认知主义遭到反驳,这种内在主义就很容易被化解。①因此,目前大多数内在主义者并不试图直接去维护非认知主义立场,而主要采取后一种方式来阐述其观点。
外在主义者否认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认为一个人作出道德判断但毫无道德动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的,特别是“非道德者”,他们可以像“道德者”一样作出各种道德判断,却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道德动机。例如福特(Philippa Foot)认为,一个人可能完全是一个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称赞勇敢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他可能因为性格上的懦弱或者考虑到勇敢的人可能会陷入险境,所以没有任何行动的动机。②再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例子,“非道德者”虽然承认应该帮助穷人,但言之凿凿之后并没有任何行动的意向。
“非道德者”的例子或许不能表明内在主义是错的,很多内在主义者认为,“非道德者”作出的道德判断只是在形式上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道德判断一样,但其实这只是在“引号”的意义上转述别人或者社会上人们的通常看法,就像一个人按照书上所写念出“X是善的”一样。“在这种用法中,我们自己并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暗示他人的价值判断。”③这一论证并不会令外在主义者信服,就像布林克(David Owen Brink)所说的,“内在主义并没有严肃地对待非道德者的挑战”④。“非道德者”并不是在主张别人的观点,也不是在言说社会上通常所谓的道德是什么,而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真诚地提出道德判断——“我应该是勇敢的”“我应该为穷人提供帮助”,这时他确实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交谈。他可以与他人进行激烈的道德讨论,可以指出矛盾的道德判断,甚至可以在新的环境中正确地使用道德判断并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⑤所以,“非道德者”的判断并不是一种在“引号”中的用法,他们想质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按照道德要求来做?难道道德判断本身就能够提供这种动机性的力量吗?内在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常识——例如,生活中人们总是由道德判断激起了道德动机——来证明“非道德者”是错误的,因为常识同样可以确证这类人的存在,它需要更多的理论阐释。
对于“非道德者”的挑战,史密斯(Michael Smith)在《道德问题》中提出了一个类比论证来进行应对。他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天生的盲人,对颜色没有任何感觉,不过幸运的是她可以通过触觉、听觉等其他感官以及先进的教学技术来掌握各种颜色对应的感觉状态。通过长期、反复和刻苦的学习,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正确地将各种颜色语词运用到不同的对象上去,从而形成关于颜色的判断。那么,她的这些判断是否可以视为和普通人一样的颜色判断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感觉过颜色,她的所有颜色判断与实际的色彩没有关系,而只与她的触觉等感受有关,所以这些判断确实只能算是在“引号”中使用的“颜色判断”。⑥同理,“非道德者”的判断仅仅在字面上与我们的一样,但就其内容来说,就像盲人的颜色判断不能含有视觉内容一样,他们的道德判断也不含有道德内容,而这种道德内容最为重要的就是规范性,即能够激发判断者自身的行动。⑦
布隆维奇(Danielle Bromwich)则提出另一种论证。她认为语词的意义往往是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通过区分不同语言的含义、使用大量的语言素材、提出反例、塑造语言的准确性等,我们形成了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既涉及语词本身的内涵,也涉及外延。一般来说,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我们使用的语词应该符合其他共同体成员语言使用的方式,与他们形成理解上的一致性。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掌握语词可以用于哪些对象,而且必须以符合常人的方式来使用语言。一个仅仅掌握语词外延的人,无法在实践中与他人达成语言意义的共识,也背离了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则。在“非道德者”的例子中,他们对于道德语词的理解仅仅是外延性的,即他们知道道德语词所表征的性质是什么,它可以用于何种事物上,所以能够形成和我们完全一样的道德判断;但他们没有遵循道德语言形成的规则,而以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将道德判断和行动完全剥离,从而无法将语言用于交往与实践。⑧同样,我们可以说,虽然通过后天的学习,盲人完全可以掌握各种颜色语词的外延,但其“颜色”在内涵上与常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尽管可以使用在拼写和外延方面与我们一样的颜色判断,但这些判断仍然不能表明盲人充分理解了颜色的含义。
尽管内在主义者言之凿凿,然而这并不能说服对方。布林克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主张。第一,外在主义者只是强调,“非道德者”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的,而当内在主义强调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的必然联系时,无疑将这种可能性取消了。第二,在“颜色”的案例中,盲人尽管没有任何视觉,但当他使用颜色判断的时候,完全可以和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在一个共同体中有意义地言说。如果这可以承认的话,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非道德者”的判断就没有把握到道德判断的意义呢?第三,前面谈到的是先天盲人的例子,假设这个人是因为后天突遭横祸而致盲,也就是说,他之前是有视觉能力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只有其失明前的颜色判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之后的颜色判断则不然?同样,对于一个后天的“非道德者”而言,虽然他的道德动机消失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判定他所作出的道德判断在意义上是有缺憾的。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反驳:对于布林克来说,后天的“非道德者”不仅在理论上可能,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的,但内在主义通过否认其信念是真正的道德判断而拒绝了这一点。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非道德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道德判断不能激发行为的动机,例如脑的部分区域遭受后天损伤的人、无精打采或郁郁寡欢之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去行动但又没有现实能力去动起来的人、在利益和道德的权衡下选择前者的人等,他们也都能够与常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提出有意义的道德判断,而差别仅仅在于他们没有道德动机。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的密切相关性,面对每一个作出道德判断者我们总是期待其能够被激发去行动,而结果往往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即便道德判断和道德动机之间不存在先天的必然联系,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弱化了的必然性联系。(11)因此,诉诸常识和直觉,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究竟何者能够胜出,似乎终将取决于统计学的数据,而这无疑削弱了这一争论的哲学意蕴。从哲学上来说,双方不仅已经陷入僵局,而且在阐释“非道德者”问题时各自陷入了“乞取前提(begging the question)”的窘境:内在主义者之所以认为“非道德者”的主张不是有意义的道德判断,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判断总是会激发道德动机的,而他却没有道德动机;外在主义者之所以认为“非道德者”虽然没有道德动机,但其道德判断仍然是有意义的,是因为他们主张道德判断不必然激发道德动机。
鉴于这一窘境,内在主义者率先作出让步。从理论上说,这种让步至少有两种方式:第一,通过弱化“动机”的强度,强调道德判断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的道德动机,这种动机甚至可以很弱,弱到当事人既没有意识到它,也没有被激发出实际的行动。换言之,道德判断作为对行动的指示必然能够带来某种程度的动机,但它并不能必然促使人们真正行动起来(如果能够实际地行动起来,则是动机很强的表现)。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改变。一方面,外在主义要想反驳这种内在主义,就不得不说明,“非道德者”提出道德判断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意向性。这实际上已经无法在哲学层面解决问题,因为“非道德者”是否具有哪怕最弱的动机(即行动意向性),这是一个心理问题,需要深入的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另一方面,这种内在主义虽然很难从哲学上来反驳,从而或许能够得到外在主义的认同,但其代价是承认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接受道德判断具有行为指南的特征是一回事,接受其引导而实际地遵从它又是另外一回事。(12)如此一来,道德判断的规范性特征将被大大弱化甚至被消除,这当然不是内在主义者愿意看到的结果。第二,通过限定判断者特征的方式强调,“道德判断必然与道德动机相联系”。仅对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有效。这种观点被称为“实践理性内在主义”,史密斯将之表述如下:“如果当事人判断对她而言在C环境下做Φ是正确的,那么,要么她被激发去做Φ,要么她在实践上是非理性的。”(13)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与“实践理性内在主义”有关的问题。
二、实践理性
将判断的主体限定为具有实践理性者,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非道德者”的现象。内在主义者可以强调,只有那些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能够在作出道德判断的同时也产生道德动机,而各种类型的“非道德者”(精神异常者、利益最大化者、性格懦弱者等)都不是拥有正常实践理性的人,所以他们并不能构成对“实践理性内在主义”的挑战。内在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知行合一”的传统几乎是一致的,特别是其关于“实践理性”的主张与心学中“良知良能”的看法也有颇多契合之处。应该说,这种解读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关系问题的理论在古今中外似乎都能够得到广泛地接受。但是,分析伦理学最为重要的任务不仅是提出主张,而且要澄清概念。对于“实践理性”这样一个在内在主义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概念,不进行深入的研讨和批判,是无法令对方满意的。那么,什么是实践理性?
内在主义者往往通过行为理由来解读实践理性。我们可以用事实判断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认知上的不理性。假设你认为地球是方的,“我”为了纠正你的认知偏差向你展示了诸多证据,其中不仅包括权威科学家的论述,而且还包括宇航员在外太空给地球拍下的照片等。在如此多的证据面前,你将有理由相信地球是圆的,从而改变自己最初的信念,那么我们就会说你在认知上是理性的。反之,如果你在面对如此多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说“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地球是方的”,那么你在认知上就是不理性的,因为你没有形成有理由的认知判断。实践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形。如果你想操作显微镜,“我”给了你一个显微镜的操作指南,但是你并不打算接受它,而是我行我素,结果处处碰壁,那么这就是实践上的非理性,因为你没有去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同样,如果你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虽然作出了道德判断或形成了道德信念,但是你没有任何动机,无动于衷甚至行为与道德指示完全相反,那么你也就是没有去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情,也是道德上非理性的。所以,“实践理性”就是人们去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情的能力;如果没有做,就是非理性的。总的看来,这种解答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它似乎是要告诉我们:一方面,根据内在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上理性的人都会在自己道德判断的基础上形成道德动机甚至采取相关的行动;另一方面,所谓实践上理性的人就是在面对道德判断的时候将之作为理由,从而形成动机乃至产生实际的行动。如此一来,它就很难逃脱“乞取前提”的指责。
第二,它所谓的“实践理性”实际上就是指我们在行动中去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有意向去做自己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反之则是不理性的。但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我”给你出示了很多证据想让你相信地球是圆的,甚至拿出照片作为直接证据以试图改变你的观念,但假设你认为这都不是你改变观念的理由,那么坚持己见就不能说是不理性的事情。比如,你可能认为照片是伪造的;或者你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经验现象都不能有效支撑信念,只有理性推理才能承担这一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把照片作为改变信念的理由,仍然坚持认为“地球是方的”,就不能算是不理性的事情。在道德实践中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有时候人们虽然真诚地主张一个道德判断,但他可能认为这并不是行动理由,或者不是什么很重要或者恰当的理由,因此没有形成行动意向,这也不能表明其是不理性的。(14)例如,虽然“我”认为保家卫国上战场是自己的义务,但是对“我”而言留在家里照顾家人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因此在两种理由的权衡下,“我”选择后者并不能表明“我”在实践上是不理性,毕竟“我”的选择也是有行动的理由的。甚至有时候道德信念提供的理由完全是错误的,例如中世纪狂热的基督教徒相信自己应该维护上帝的权威去杀死持各种“异端”者,但若其中一人X突然心生怜悯,最后不把自己的道德信念作为理由而放了“犯人”,这当然也算不上不理性的。这个例子说明,“当道德判断是错误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按照道德判断去行动,或者意欲行动,或者打算行动”(15)。所以,X的行为在实践上并不意味着不理性。
第三,这种“实践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手段/目的”理性。如果“我”的目的是获得关于地球形状的真实信念,那么遵循获得真实信念的手段——如采纳各种证据作为认知理由——就是认知上理性的。如果“我”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取得观测成功,那么意欲将操作指南作为行动的理由就是理性的。同样,如果“我”的目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自我实现,或者是功利主义式的获取最大功利,又或者是康德所谓的人本身,那么,当“我”的道德判断所指示的行为能够成为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时,“我”将之作为理由从而意欲甚至直接遵循就是实践上理性的。所以科斯嘎德(Christine M.Korsgaard)认为,手段/目的理性的模式可以被用来解释实践中的情形:在意识到行为是你实现目的的手段的情况下,仍然未能被激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实践上的非理性,而这是迎合内在主义的最好方式。(16)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梅森(Elinor Mason)的质疑。她认为,科斯嘎德的论证实际上是这样的:若A是目的,B是手段,因为人们相信A作为目的是值得追求的,由此产生了追求A的动机;而鉴于B是达成A的手段,所以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会相信“应该做B”并被激发着去做B。也就是说,科斯嘎德关于实践理性的手段/目的解释建立在“A值得追求”这一信念以及它能够激发动机的内在主义观点基础上,所以若借助实践理性来说明内在主义,仍然是乞取前提。(17)
实际上,任何关于实践理性的理解都应该超脱于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立场,这似乎已经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的关系”这一话题之外,在不预设道德判断能否产生道德动机的情况下,从另一个角度给予“实践理性”独立的解说。笔者认为,关于“实践理性”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并不需要假定存在任何先天的、关于某种目的值得追求的道德判断,而应该着重了解道德判断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功能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会明白:任何在实践上理性的人,都能够理解人们道德活动和道德判断的功能,并且恰当地运用道德判断,否则他就会被特定的社会共同体评价为“不理性”。也就是说,在道德领域中实践是否理性,是通过其是否可以参与人们共同的道德生活、实现道德判断的功能来评价的。
贝德克(M.S.Bedke)通过其不乏创见的论述告诉我们,人们的道德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在面对自然选择时,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不断调整行为而生存、适应的结果。总的来说,道德是有利于他人和整个群体(甚至也会在利他的同时利己)的,从而使得整个种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优势。这种道德的生活模式自祖先开始,通过基因的复制和遗传,逐步就成为后来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行为模式,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不断进化的过程。(18)如此一来,个体在道德生活中是否理性,就不是由其自我来进行评判的,而应根据其与生存其间的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行为模式的契合度来评价。那么,社会共同体的道德行为模式又是什么呢?贝德克说,为了激发道德行为,我们必须具有某种心理状态,通过它实现把人们关于道德行为的认知转变为实际行动的功能,而这种心理状态就是通过提出道德判断来表达内在的行动意向。(19)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道德生活中所谓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指的就是:他遵从社会共同体使用道德判断的基本模式,能够实现道德判断的基本功能,始终以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为旨归(因此,像“应该杀死异教徒”这样的道德理由在很多社会共同体中是不被认可的),同时还需要有效地从中激发出行为动机。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以实践理性为精神条件、以特定共同体为社会条件的内在主义理论,就是可能的。(20)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批评外在主义所提出的“非道德者”犯了不理性的错误,而不必诉诸于内在主义的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内在主义容易为我们带来隐忧:它将道德生活和道德判断局限于特定社会共同体中,内在主义的常识——道德判断能够引发道德动机——也将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才会有效,而实践理性也将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因此,就像有的学者承认的那样,关于道德判断的形成、功能以及理性与否的刻画,终将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内在主义或许和相对主义(甚至是一种个体的相对主义)是相容的。(21)此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某一个社会中,人们全都是“非道德者”,他们仅仅作出道德判断,既无道德动机也无道德行为,因此他们的生活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关于是否理性的评价也将必然与我们不同。
当然,人们的道德生活模式本来就不可能相同,甚至道德判断的内容也会彼此冲突,所以有的人使用道德判断的方式与我们有很大差别也是可能的。然而这并不令人苦恼,就像摩尔(G.E.Moore)在《伦理学原理》中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假设我们身边有一把椅子,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把椅子”是真实的。当然,可能有一个疯子进来说这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头大象,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向他证明他错了,但是可以引导他形成和我们一样的判断。(22)同样,虽然他们是“非道德者”或者其关于道德判断的目的的理解以及是否具有实践理性的标准与我们不同,但除非我们不打算彼此交往,否则一旦社会交往得以展开并不断扩大,就可以引导他们参与我们的道德生活,去接受我们的道德判断的用法。当然,假如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就像我们无法说服疯子那是一把椅子一样,但也能够通过让其退出有意义的对话、商谈的方式来排除这类特殊观点。国际社会对个别国家加入共同体的“不接纳”,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对无法改造的各类“失范者”剥夺其参与政治商谈资格的惩戒,都是该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三、道德拜物教
下面来看史密斯对外在主义另一条重要的反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判断的改变往往能够引发行为动机的变化。(23)例如,“我”原本认为吃狗肉是正确的并且也有吃狗肉的动机,但是后来“我”的道德判断改变了,认为保护犬类动物才是正确的;而随着道德判断的改变,“我”的动机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具有吃狗肉的意向性,反而具有了保护动物的意向性。如果“道德动机总是循迹(tracking)道德判断”这一现象不可否认的话,那么不管是内在主义还是外在主义都必须对之作出解释。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具有道德行为的动机,实际上是指具有道德行为的意向。那么这种意向为什么会产生呢?不管是内在主义还是外在主义都承认,道德信念和行动的欲望一起才能够产生行动的意向。不过,内在主义认为这种行动的欲望是由道德信念本身直接产生的,正是因此我们才说道德判断必然能够激发道德动机。而外在主义认为,欲望不是道德信念产生的,它是外在的、独立的东西。换言之,内在主义认为道德信念能够产生欲望,欲望内生于道德信念;而外在主义认为道德信念不能产生欲望,欲望是外在于信念的东西。
内在主义很容易解释上述“循迹”现象,因为道德判断总是产生相应的欲望,因此当你说吃狗肉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有吃狗肉的欲望并形成了吃狗肉的动机。而当你的道德信念改变了,欲望也会随之改变,道德动机自然也就随之改变。这样一种直接来自于特定道德判断的、非引申性的(nonderivative)欲望被史密斯称为“从物欲望(de re)”(24)。而外在主义在解释“循迹”现象时则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既然道德欲望不是道德信念直接产生的,那么道德判断本身的改变并不能对人们的欲望产生影响,所以尽管道德判断变了,但是欲望并不一定发生变化。为了使得欲望能够同步变化,从而产生道德动机,外在主义就不得不诉诸更为一般的欲望,即“总是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当道德判断变化了之后,由于其所认为的正确的事情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当事人可以从“总是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种一般欲望中引申出新的、外在于道德判断本身的欲望,即“保护犬类的欲望”。这种从一般的、关于“正确”本身的欲望中引申出来的欲望,被史密斯称为“从言欲望(de dicto)”(25)。史密斯认为,通过诉诸“从言欲望”,外在主义无法为我们塑造一个真正具有美德的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史密斯引用了一个来自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例子。
在《道德运气》中,威廉姆斯说:假设你的妻子和一位路人同时落水,两个人有均等的机会被你救上岸,最后如人所料你选择救自己的妻子。如果上岸之后,妻子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救她,而你的回答是:“因为一般而言,救自己的妻子在道德上总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有了救你的欲望。”这时,你的妻子失望的表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你把她和普通的陌生人完全同等对待,只是由抽象的道德原则本身来决定其命运。虽然最后她被救助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丈夫对她本身的关心和疼爱,仅仅因为这是符合道德的。换个角度来说,妻子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当然是“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有直接下水去救你的欲望”(26)。在史密斯看来,只有后面这种诉诸“从物欲望”的人才符合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个有德之人的理解,他直接关注朋友、妻子、孩子、友谊、诚实、信用本身,而不是处处需要首先诉诸一个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欲望。因此,史密斯说:“一个强外在主义解释导致我们对一个好人的动机的内容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它使得道德拜物教成为唯一的美德。当然,补救的方法就是退回到另一种选择——内在主义——那里来解释道德判断和动机之间的依赖关系。”(27)
对于“道德拜物教”的指责,外在主义者主要采取两种策略来应对。
第一,通过各种方式来使得外在主义避免“道德拜物教”的指责。例如,考普(David Copp)不再诉诸“从言欲望”来解释人们的道德动机,而是重新启用了一个词:倾向(disposition)。他认为一个善良而且意志坚定的人总是会有这样的倾向:直接欲望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28)因此,当一个人认为不吃狗肉是正确的,就在这种倾向的推动下直接产生不吃狗肉的欲望,而不必再去诉诸关于一般的“善”或者“正确”的欲望。德莱尔(James Dreier)通过其关于“二级欲望”的阐述告诉我们,欲望抽象的、有意义的事物其实也就等于是在非工具意义上来欲望其组成部分,后者虽然是“二级欲望”,但是每当我们面对道德信念时,这种“二级欲望”就油然而生。例如,医生欲望“有意义的事业”,但欲望“有意义的事业”实际上就是欲望“救治病人”“勤奋工作”“同仁认可”等,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所以每当“救治病人是正确的”这一道德判断出现的时候,“救治病人”这一二级欲望也就从外部直接参与进来共同形成道德动机,而此时的一级欲望“有意义的事业”并不在场。(29)同样,关于“善”“正当”的欲望也是如此。利勒哈默尔(Hallvard Lillehammer)认为,所谓一般的“善”或者“正确”其实是由各种具体的行为或者事物构成的,对它们的欲望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些组成部分的欲望。关心家庭、关怀生命等都是善的组成部分,对善的欲望也就是对这些事物的欲望,因此,“关心家庭”“关怀生命”的欲望本身就是直接的而非引申的,它们与道德信念一起构成了道德动机。(30)事实上,正如斯坦伯格(Caj Strandberg)所言,在现实生活中说人们总是有关于一般的“善”或“正确”的欲望,并且在每一个个例中都需要从中推演出“从言欲望”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每时每刻都在意识到这种一般欲望,并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境去作出推演,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无论对于外在主义还是内在主义来说都是如此。所以,这种道德拜物教是否真的存在值得商榷。(31)
第二,承认外在主义诉诸的是“从言欲望”,但否认这种所谓的“拜物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实际地作出行为的时候,确实需要诉诸一般的道德原则。例如赞格威尔(Nick Zangwill)认为,在威廉姆斯的例子中,如果丈夫就在水塘旁边,当然他没有时间去思考,可能不得不出于“从物欲望”而直接行动。但是,假设当时他不在水塘旁边,而是5公里之外的家里,他在开车去现场的时候将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的问题,那么将一般道德原则纳入思考的范围之后,既有“救妻子”的欲望,也有“做正确的事”的欲望,这并不是道德错误。(32)另外,依从“从言欲望”而行动有时候确实塑造了高尚的人格。我们秉持了坚定的道德原则,将每一次出现的个别情况都置于原则的考察之下,从而得出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论。因此,一旦从一般道德原则中引申出“从言欲望”,我们将会总是欲望那些正确的事情,并且不以自身的利益、喜好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有时候“从言欲望”的产生往往还会令我们遭受损失,或者必须去关照自己不愿关照的人,但是每一次即便如此也要遵从道德的举动,无疑就是在塑造一个完善的人格。(33)
生活是复杂的,“道德拜物教”固然有很多缺陷,但很多时候它又非常必要。正如内在主义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批判它那样,外在主义可以捍卫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或许确如科沁(Simon Kirchin)所言,在关于“善”的拜物教的评价中需要作出一些适当的平衡,对其予以适时的褒扬和拒斥。有时候人们为一种理想的目标而奋斗,就像士兵孜孜不倦地追求“勇气”、法官追求“正义”那样,将一般的抽象物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可能并没有什么坏处(34),只要他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守财奴”或者陷入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的异化状态即可。比如,在威廉姆斯的例子中,当“我”去救妻子的时候,仅仅考虑一般的“善”,而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妻子身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似乎把妻子看作了实现一般“善”的工具,而恰恰忽视了道德行为的对象本身。(35)
其实,所谓“从言欲望”和“从物欲望”的区分反映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关于“信念与欲望关系”的不同看法。当双方的争论进入“道德拜物教”这一步时,意味着不管是内在主义还是外在主义实际上都已经承认,信念和欲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关于“知”的,而后者才关乎“行”。但是,对于内在主义来说,信念本身是可以产生欲望的,所以我们面对道德判断才会产生行为的直接动机。但是根据又在哪里呢?信念本身为什么能够产生与它完全性质不同的欲望?如何解读信念与欲望的形而上学特征,又该如何构建彼此沟通的桥梁?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话,那么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的关系问题其实亦可迎刃而解,双方僵持的局面本不应该出现。而对于外在主义而言,因为他们认为信念和欲望本身是异质的,所以欲望只能够从同质的其他欲望中产生——信念产生不了欲望,只有欲望才能产生欲望。但问题在于,最初始的、最一般的欲望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它是凭空产生突然就有的;其二,即便是一般的欲望,也是从一般的信念中产生的。例如,关于“做正确的事情”的欲望实际上是从“做正确的事情总是道德要求的”这个信念中产生的,并且欲望的内容越抽象,信念的内容也会越抽象。然而,如若是前者,外在主义无疑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而后者就等于是向内在主义妥协。
当前关于信念与欲望、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已然陷入僵局。或许改变现有的研究问题的方式,如借鉴病理学、脑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开展实证研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注释:
①Cf.Russ Shafer-Landau,"A Defense of Motivational Externalism",Philosophical Studies,97(3),2000,pp.277-279.
②Cf.Philippa Foot,"Moral Belief",The Is-Ought Question,W.D.Hudson(ed.),Macmillan,1969,p.209.
③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19页。
④David O.Brink,Moral Re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7.
⑤Cf.Sigrún Svavarsdóttir,"Moral Cognitivism and Motivatio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08,1999,pp.188-189.
⑥⑦Cf.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Blackwell,1994,p.69,p.70.
⑧Cf.Danielle Bromwich,"Motivational Inter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Amoralism",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24(2),2016,pp.455-459.
⑨Cf.David O.Brink,"Moral Motivation",Ethics,108(1),1997,pp.22-24.
⑩Cf.Russ Shafer-Landau,"A Defense of Motivational Externalism",pp.272-274.
(11)Cf.Evan Simpson,"Between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in Ethic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49(195),1999,pp.202-203.
(12)Cf.Sigrún Svavarsdóttir,"How Do Moral Judgments Motivate?",Contemporary Debates in Moral Theory,James Dreier (ed.),Blackwell,2006,p.171.
(13)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p.61.
(14)Cf.David Copp,"Belief,Reason,and Motivation:Michael Smith's 'The Moral Problem'",Ethics,108(1),1997,p.52.
(15)Nick Zangwill,"Externalist Moral Motiva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40(2),2003,p.150.
(16)Cf.Christine M.Korsgaard,"Skepticism about Practical Reas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83(1),1986,pp.12-13.
(17)Cf.Elinor Mason,"An Argument against Motivational Internalism",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108,2008,p.152.
(18)(19)(20)Cf.M.S.Bedke,"Moral Judgment Purposivism:Saving Internalism from Amoralism",Philosophical Studies,144(2),2009,pp.196-199; pp.199-200; pp.200-201.
(21)Cf.James Dreier,"Internalism and Speaker Relativism",Ethics,101(1),1990,pp.14-17.
(22)参见乔治·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74页。
(23)(24)(25)Cf.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p.71,p.74,p.75.
(26)Bernard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7-18.
(27)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p.76.
(28)Cf.David Copp,"Belief,Reason,and Motivation:Michael Smith's 'The Moral Problem'",p.50.
(29)Cf.James Dreier,"Dispositions and Fetishes:Externalist Models of Moral Motivation",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61(3),2000,pp.634-637.
(30)Hallvard Lillehammer,"Smith on Moral Fetishism",Analysis,57(3),1997,p.193.
(31)Caj Strandberg,"Exter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Moral Motivation",Philosophia,35(2),2007,p.259.
(32)Nick Zangwill,"Externalist Moral Motivation",p.148.
(33)Cf.Hallvard Lillehammer,"Smith on Moral Fetishism",p.192.
(34)Cf.Simon Kirchin,Metaethics,Palgrave Macmillan,2012,p.158.
(35)Cf.Michael Smith,"In Defense of 'The Moral Problem':A Reply to Brink,Copp,and Sayre-McCord",Ethics,108(1),1997,p.113.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