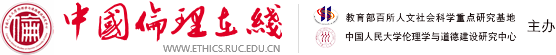高兆明:仁爱:有无正义边界?
摘要: 无论是主动态还是被动态的仁爱实践,均有行为合理性及其限度问题,均有权利边界。即便是自愿的仁爱行为,亦会受到正义的限制,不得以施予仁爱为理由强行伤及他者或社会的重大利益。在特殊条件下,甚至可以有合理理由拒绝仁爱行为,这种拒绝既可以来自施予方,亦可来自接受方。在对本民族国家成员负责基础之上,不伤害受援对象的尊严、自我责任感与生产性精神,构成对非本民族国家及其成员仁爱行为的合理边界。
作者简介:高兆明,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
关键词:仁爱/仁爱的正义边界/权利/Kindheartedness/the justice boundary of kindheartedness/rights
一、问题的提出
此处“仁爱”在仁慈、博爱精神及其实践意义上使用,此处“正义”在政治正义意义上使用,其核心是“权利”。所谓“仁爱”的正义边界问题,是指“仁爱”实践是否受“正义”限制,有无条件性,“仁爱”实践的这种条件既合乎人类一般文明价值精神,又合乎正义理念。所谓合乎“正义”理念是罗尔斯“公平正义”意义上的,是活动所有相关方都认为“公平”的,进而可以理性认肯接受的“正义”。此“公平正义”不仅是政治关系范畴,而且内在地具有某种道德价值规定,是一种具有道德“善”属性的价值范畴。正义的核心问题是“权利”,所谓“仁爱的正义边界”问题就是要追问:仁爱实践是否受“权利”限制。
近年来,世界呈现出明显“右”转的保守主义倾向,一度被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被强烈质疑、批评。世界“右”转固然有偶发、个体因素,但是,对重大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归之于个体、偶然,而应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精神实践的历史演进进程中把握。总体上看,这种“右”转的保守主义倾向是对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化进程、和平发展实践的一种反思形式。毫无疑问,人类近代以来所确立起的仁爱、人道价值精神当然是人类社会极为珍贵的基本价值。一个合乎人性自由生长的美好世界不可或缺仁爱、人道精神,现代社会亦不例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爱、人道价值精神的日常生活实践。如何在具有丰富人性内容的日常生活中实践仁爱、人道精神?这种实践切合人性而不陷于浪漫,它能洞察人性中的恶,激发人性中的善。如果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无法否认人类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某种形式的仁爱精神及其实践,那么,就有合理理由追问:仁爱精神及其实践是否有其历史形态?如果有,能够构成现代社会仁爱精神及其实践的独特历史内容是什么?如果人类社会有丛林社会与文明社会之分,那么,丛林社会与文明社会仁爱实践的历史样式何以区别?是什么构成现代文明社会仁爱、人道精神实践的基本底线与基本范式?
人们通常习惯于从美德论、义务论角度谈论“仁爱”,基本缺失正义论视角。“仁爱”是否可以有来自正义论角度的理解?当然,换个角度理解并不意味着否定美德论、义务论,只是要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前行。其实,从正义论角度谈“仁爱”早已有之,黑格尔、罗尔斯即是代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财产权为所有环节的起点,以思辨方式表达了道德行为主体首先是权利主体,全部道德问题的关键只是经过雕琢将特殊性提升为普遍性而已。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责任义务划分为自然、职责与分外义务三类,并认为尽管分外义务是种令人敬仰的美德,但是社会不能强制要求其成员履行。黑格尔、罗尔斯均以自己的方式揭示道德主体的权利主体特质。如果能够承认当今人类生活样式与既往有重大区别,那么就应当承认仁爱实践的古今样式有所不同,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主体等构成了这种基本区别的核心内容。换言之,主体及其权利是现代社会仁爱道德实践历史样式的基本特质之一。
几年前,笔者曾针对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的基本命题,探讨过仁爱与正义统一的可能,不过那是从仁爱活动主体角度提出并思考问题,旨在揭示仁爱精神及其实践的层次性、正义的内在道德属性[1]。尽管该思考从美德论、义务论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仁爱的某种边界性,但那种认识仍然有待推进。也许转换视角,即由仁爱行为施予者的视角转向仁爱行为接受者的视角,可以有新的发现。随着视角的转变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一个人能否以仁爱为理由向他者提出无限要求?一个人以仁爱为理由向他者提出的道德义务责任要求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合理的?一个人的施予仁爱要求是否可以被合理拒绝?等等。这些问题均有助于引领我们深思仁爱的正义边界问题。
二、仁爱是否有正义边界
对仁爱问题观察的视野可有两个维度:实体维度与状态维度。一般说来,一个仁爱道德行为至少有两个实体,仁爱行为的行为者(施予者),仁爱行为的行为对象(接受者);其状态亦有两类,主动态的与被动态的。行为者所施予的仁爱行为既可以是主动态的,也可以是被动态的,与其相应,对于被施予仁爱行为的接受者而言,在此具体道德行为中,其既可以是被动态的,也可以是主动态的——其根据仁爱的道义理由要求潜在仁爱行为施予者施予仁爱行为。一般说来,一个具体仁爱行为会有如下四个象限组合的两种类型的道德行为状态。
仁爱活动施予者 接受者
主动 A a
被动 B b
Ab(或bA)状态。通常说来,这种主动施予活动状态被认为是合理的并值得赞美。一个社会是否美好并值得珍视,尽管可以给出诸多理由,但核心在于它是富有人性的。如果一个社会缺失这种仁爱施予精神,缺乏对同胞的同情、怜悯之心,这个社会则是冷漠、病态的,不值得留恋。然而,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基于主动仁爱关怀的道德精神实践是否是无条件的?罗尔斯在澄清“分外义务”时就曾明确揭示:主体出于自愿可以做出根本利益牺牲,不过,尽管这种美德值得欣赏与赞美,社会却没有理由强迫一个人如此做,即主体出于自愿的仁爱义务可以是无限、无边界的,但此“无限”“无边界”仅仅在自愿主体的自身范围内。这样,此“无限”“无边界”就意味着有进一步规定:其一,主体自身基于自愿可以在仁爱精神实践中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有限自身的无限牺牲。在此,“自己的”权利构成了仁爱精神“无限”实践的最初边界。其二,主体不可以仁爱为理由强制要求他人施行仁爱行为,如,擅自做主或者强迫他人牺牲重大乃至根本利益。在此,他人的自由权利构成了主体仁爱精神实践的现实边界。其三,在通常情况下,仁爱行为施予者应当尊重仁爱行为施予对象的意志,不应当违背其意志强迫其接受仁爱施予行为。在此意义上,可能仁爱行为施予对象的权利亦构成仁爱行为的现实边界。如此看来,即便是Ab状态中的仁爱行为,亦有某种权利的正义边界。
Ba(或aB)状态。对于仁爱精神实践,我们通常考虑的是Ab状态,往往忽略了Ba状态,而Ba状态恰恰值得重视,它内在地蕴含着一系列重要的道德哲学问题,蕴含着政治与道德、美德与权利等关系。关于仁爱美德及其限度问题的可能答案隐藏其中。
用泰勒的话说,一个好的社会具有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精神两个好的“背景性框架”。作为背景性框架的社会文化价值精神,以尊严、尊重、自尊为核心。在具有尊严、尊重与自尊的社会文化价值环境中,人性得以健康生长,人格趋于健全。在一个富有人性的美好社会中,不仅社会成员具有人道、仁爱精神,关爱同胞,而且一个人身处紧急、危难状态需要帮助时,也有合理理由期待并要求他人给予必要帮助。这正是“义务”的根据之一。此时,一个人的“权利”要求就构成了他者或社会的“义务”。一个社会如果漠视身处不幸者的这种仁爱施予求助,甚至否定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合理性,那么,这个社会必定在普遍意义上是道德冷漠、病态的。这表明Ba状态存在有其合理根据,主体处于危难状态时有合理理由基于仁爱精神要求他人、社会提供仁爱帮助。不过,这里的问题关键是,提出施予要求的主体有权利根据仁爱精神要求他者、社会施予仁爱行为,是否意味着这种要求可以是无限度的?
黑格尔的“紧急避难权”思想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黑格尔在肯定每一个人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一个人在紧急状态下有“紧急避难权”,且以一片面包为例对此具体说明[2]130。当一个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有权利要求同类给予仁爱关照,且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合理理由的行为此时也可获得某种合理理由。在通常情况下,他人的正当权利不能伤害,偷窃不合法、不道德,然而,在一片面包即可救命的紧急危难情况下,活命使其具有了某种合理理由。如果一个人或社会在面对同胞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冷漠无情,甚至落井下石,那么这个社会不会有真实的自由。不过,正如黑格尔明确揭示的那样,“紧急避免权”是有限权利。“紧急避难权”有其前提:在坚持普遍(而不是特殊)自由权利基础之上坚持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权利,每个人自由权利毫无例外地得到实现就是普遍自由的真实实现;承认每个人的人格及其尊严平等,保护与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对权利、财产权的承认、尊重。根据黑格尔的论述,“紧急避难权”的要旨有二。其一,当一个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可以有合理理由期待他者的援助,也可以有合理理由对他者正当权利在有限范围内做出有限伤害。如,在一块面包可以救命时,可以去偷一块面包。其二,此种有合理理由伤害他者正当权利的行为具有严格限制:处于“紧急”危难状态,为了“活命”,且只能是为了“当下”活命,不能伤及他者的根本权益。不能以我以后可能没吃的、得为以后贮存食品为理由,抢劫他者的全部财富,甚至要了人家的性命、鸠占鹊巢。“紧急避难权”的这种严格限制既是对生命及其尊严、人道精神的捍卫,亦是对自由权利本身的捍卫。
“紧急避难权”表明,社会成员有合理理由基于“仁爱”向他者、社会提出施予仁爱救助的权利,但这是一种有限权利,它不能伤及他者、社会的根本权利。为什么不应当以仁爱为理由而不顾及权利?用黑格尔抽象语言说是仁爱、权利的普遍性、必然性,即无论是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无一例外地沐浴仁爱阳光,权利都会被尊重。仁爱与正义既是一种社会精神,也是一种社会客观制度机制;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社会系统体系。
黑格尔思辨体系中的道德行为主体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主体。黑格尔给出的道德义务命令首先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2],即黑格尔的道德行为主体是普遍意义上主体——每一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有平等的人格及其尊严,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会得到尊重。黑格尔以思辨方式揭示:自由以自由自身为限制,他人的自由即为自己自由的边界。显然,在黑格尔这里,道德主体首先是权利主体,而且作为权利主体最根本的是财产权——一个人之所以有独立人格与尊严,最根本的就在于有财产权。这正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思辨结构体系中以所有权为开端的基本缘由。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有平等生命及其尊严的权利,有广义财产权。这意味着,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一切道德行为必须奠基于对权利尊重基础之上,除非是出于本人自愿,否则任何人不能以道德(仁爱)的理由伤害他者的根本权利;另一方面,伦理共同体有其内在伦理精神,正是此伦理精神使得伦理共同体成为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生命家园。“爱”正是此伦理共同体的原初性精神,在黑格尔那里通过伦理实体中的“家庭”向我们敞现。此爱,不仅是父母之爱,更是每一成员之间的爱。每一个人既是平等的权利主体,又彼此间具有“爱”心,即在普遍意义上,道德行为不仅是善的,还应是正义的;仁爱实践应当兼备或平衡善与正义二者,既是善的,亦是正义的。当然,这里需要追问,为什么在以法治社会为标识的伦理共同体中正义的行为具有善的属性?这是因为当我们在现时代说到“正义”时,一定是“公平的正义”,它获得具有不同善观念人们的共同认肯。正因为如此,在普遍意义上,善与正义才是可以平衡兼顾的,且这种平衡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过,这种内在性的平衡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在具体实践中可能会对彼此有某种伤害,或者须对方付出某种代价,如“紧急避难权”中所呈现的那样。善与正义的平衡意味着,即便在特殊情境中一个道德行为会对善或正义造成某种伤害,也有须坚守的底线,不能从根本上伤害善(仁爱)与正义(权利)。
至此,我们有合理理由说,“仁爱”实践,无论是主动态的还是被动态的,均有行为合理性及其限度问题,均有“权利”边界。即便是自愿的仁爱行为,亦会受到正义的限制,不得以施予仁爱为理由强行伤及他者或社会的重大利益。仁爱有层次,不能以最高层次否定其他层次,更不能以仁爱否定权利,否则,仁爱就可能成为一种浪漫空想精神,非但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实践,反而有可能在仁爱之名下伤害平等权利,进而伤害仁爱精神自身。在现代文明社会,应当在社会法治规范性秩序基础上理解与实践仁爱精神。也许这正是丛林社会与文明社会中“仁爱”精神实践的根本区别之一。
三、是否有合理理由拒绝仁爱行为
仁爱实践受到正义的限制意味着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拒绝仁爱行为。这种拒绝不仅可以来自施予方,亦可来自接受方。我们以“哈丁救生艇”“泰坦尼克”号为例,对此做进一步简要讨论。
哈丁的“救生艇”理论有其特有含义。哈丁将整个世界比喻成汪洋大海,发达国家所有的人都在救生艇上,尽管救生艇还有承载空间,但承载能力有限。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救生艇,有些人不得不落在救生艇之外。对此,那些尚有空余位置的艇上成员应该怎样做?哈丁认为有四种选择:其一,救助所有漂落在水中的人,但结果是因超载带来彻底灾难;其二,救助一部分落水者,但无法确定究竟应救助哪些人;其三,为了保证救生艇安全不救助任何人;其四,救生艇上的人面对漂落在大海中的人良心不安,主动让出位置给救生艇以外的人,结果可能是整个救生艇上坐着的都是无羞耻感的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一个漂落在大海中的人如果有羞耻感就不会让别人以死换来自己的活[3]561-568。我们此处并不具体讨论哈丁本人理论的得失长短,只是借用哈丁的“救生艇”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漂落在茫茫大海中人员的紧急救助要求及其合理性限度问题。为了便于讨论,对“哈丁救生艇”条件做进一步极限修正:假设艇上没有任何冗余空间且没有任何可以用以施救的多余物资。漂落在大海中的人面对此救生艇,当然有合理理由期待救生艇上成员施予仁爱救助。不过,在救生艇已经处于极限状态下,就有几种行为选择可能,其中包括:其一,当他们明白救生艇已处于极限状态时,他们是否还有合理理由要求艇上成员施予仁爱救助、让其上艇?其二,甚而言之,他们是否有合理理由根据仁爱精神(保护生命)将艇上的人拖下海让他们自己上船,如果艇上的人不让就强行扒艇,哪怕同归于尽一起沉入大海?其三,艇上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位置,放弃自己生的希望,让艇下的个别人上艇,但这又可能面临艇下诸多人一哄而上扒艇倾没的灾难。
泰坦尼克号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泰坦尼克号在沉船逃生间所显现的人性光芒与日月同辉,那优美灵魂深刻隽永长驻人心。就与本文主题相关范围而言,泰坦尼克号船上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合理理由根据仁爱精神要求得到逃生救助,但是救生艇资源极为有限。泰坦尼克号最后阶段有诸多涉及人性深处的现象值得特别关注。其中包括:其一,一些人主动放弃上艇逃生的机会,甚至有人已经上了救生艇却主动让给更为需要的人,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其二,船员坚守职责,维持秩序,让妇女、儿童、老人优先上艇,阻止那些想混上救生艇的年轻力壮男人。
基于泰坦尼克号与改造过了的哈丁“救生艇”案例,我们可以为特殊情况下拒绝仁爱行为的可能合理理由做具体归纳。
其一,抽象地说,在一般情况下,所有人都有平等人格及其尊严,有在紧急危难状态中获得同胞仁爱相救的合理理由(或权利)。但是,在具体情景中,仁爱的日常生活具体实践受具体条件规定,由于条件限制,拥有平等人格及其尊严者的具体存在状态具有差异性,甚至在特殊条件下强行阻止某人或某些人享有仁爱施救亦是合理的。哈丁“救生艇”中的那些在大海上漂泊者,泰坦尼克号中的那些想逃生的年轻男子,当然内在地具有平等人格与尊严,当然有要求获得仁爱相救的合理理由。不过,由于资源极其稀缺就进一步引出:抽象的平等权利及其享有仁爱救助资格在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实现问题。在资源极其短缺的紧急危难状态中,这些具有平等人格及其尊严者之间就有了某种优先性关系,这种优先性关系不是人格、身份、等级差别,而是抽象的平等权利在现实情景中具体实现时的优先性排序。既有伦理共同体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伦理文化价值精神,是此种优先性排序的依据。这种伦理文化价值精神作为传统、风俗、习惯存在,成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价值根据。在现代文明社会,人格平等、尊重所有权、优先关爱妇孺老弱、忠于职守,等等,就是此种伦理文化价值精神中的基本内容。
其二,一个人面对处于紧急危难状态中的同类,应当有仁爱心,有施予仁爱相救的义务,不过,履行此仁爱相救义务可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如,给予在大海上漂泊者可能的食物、水,受托并给予承诺等,甚至一个人也可以出于自愿宁愿以自己的死换取他人活的可能。这种行为选择本身所呈现的精神当然是一种崇高,值得人们仰慕赞美,然而当事者却不能强迫要求艇上的其他人亦如此做。这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分外义务。在此意义上,拒绝来自外部强制要求的、以牺牲根本权利为代价的仁爱义务,无论是当事方还是其他人员,亦是有合理理由的。
其三,是否在此等紧急状态中任何个体的自愿牺牲行为均是可取、值得欣赏的?仔细想来也未必。即便是个体自愿牺牲,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代价仁爱相救他者,其行为也未必就是完全合理的。在哈丁“救生艇”中,如果一个本已在救生艇上的人自愿跳入大海,换取空间让大海中的一个他者上艇,如果此时艇周围有许多迫切求生者蜂捅而上,救生艇很可能就会倾没。一个人自愿牺牲的仁爱行为本身固然令人赞美,但是,若在特殊情况下此行为有极大可能导致共同体重大灾难,则此个体自愿牺牲行为的仁爱属性则有可能发生了某种微妙但又根本性的变化:对大海中漂泊者的仁爱即意味着对艇上同胞根本权利的根本伤害。这表明,个体的自愿仁爱牺牲行为亦有限度,不应当伤害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共同体整体的根本利益是拒绝某种仁爱行为的合理根据。阿伦特曾区分“私人美德”与“政治美德”,并强调要警惕将私人美德政治化,警惕将私人美德当做政治美德[4]561-562,其本意就是要提醒人们:警惕离开共同体根本利益简单地对待仁爱精神。
其四,处于紧急危难状态的人们当然有合理理由要求同胞施予仁爱相救,但是却没有理由强行要求他人牺牲根本权利来换取自身的获救。每一个人的人格、自由权利是平等的。一个尊重他人人格及其权利者,值得令人尊重,反之亦然。一个不尊重他者人格及其权利者,尽管身处危境令人同情,但却不能赢得人们的敬重,更不能赢得人们倾心相助。一个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自然有“紧急避难权”,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身处紧急危难要求获得仁爱相救为由,突破“一片面包”的底线,无限度地侵占他人的正当财产,反客为主,则不仅不会赢得人们同情,相反只能招来鄙视、痛恨,唯恐避之不及。即超出合理限度的仁爱施予要求,亦可以有合理理由拒绝。
四、民族国家的仁爱行为有权利边界吗
上述关于仁爱精神实践是否有权利边界的讨论基本是在同一伦理共同体内部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同一伦理共同体内部揭示仁爱精神实践存在权利边界,那么,在逻辑上就能推论出对不同伦理共同体成员的仁爱精神实践同样存在权利边界的问题。不过,这需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而且这种说明同样不是通常美德、义务论的维度,而是权利、正义、政治的维度。
在哈丁“救生艇”一例中事实上已经涉及两种特殊仁爱实践主体及其类型:作为整体的救生艇共同体及其成员,作为自愿牺牲自己让出空间的个人及其权利,艇上个人的仁爱实践受艇上全体成员权利约束。这意味着,共同体整体可以作为仁爱实践主体出现,且共同体整体的仁爱实践可能明显不同于个人,在个人看来可行的在共同体看来却未必可行。共同体对其内部成员的仁爱行为未必适用于对共同体以外成员。这里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与政治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是个人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共同体,政治国家共同体则不是个人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在其现实性上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有机体,它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有其内在文化精神与运行机制。民族国家是政治国家、政治共同体。尽管民族国家自身内部亦有多元群体,但是正如罗尔斯所揭示的,这些具有多元完备性学说的多元群体具有重叠共识,这种共识内在性地维系着民族国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族国家政治有机体不仅有宪法法律为社会基本结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更有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文化与民族国家情感。民族国家认同、基本文化认同、基本社会结构体系认同、国民身份认同,等等,是政治国家区别于社会共同体的根本之处。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据在于本民族国家人民,民族国家首先须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现象是,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尽管均追求人类永久和平、世界政府理想境地,但是他们在永久和平、世界政府面前均停下脚步。这是为什么?至少他们均以自己的方式意识到永久和平、世界政府的至善状态属于彼岸世界,此岸只能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探索前行。民族国家间的仁爱精神实践既不同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也不同于私人间的。每个民族国家当然应当对其他民族国家成员有仁爱精神,对处于不幸中的其他民族国家施予帮助。帮助落后国家的人民摆脱贫穷、愚昧、落后,是一切先发民族国家对人类的责任;对其他民族国家发生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是人类走向和平不可或缺的美德。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具体实践。
作为政治有机体的民族国家是其成员的生命家园。一方面,个人总是生活在民族国家中,人性、人格在此共同体中塑造,权利、义务在此共同体中成为现实。在政治国家中,一个人在拥有相应权利的同时负有具体义务,包括维护自己生命家园的义务,如果不能履行这些必要义务,会受到强制性要求。离开了民族国家,个人及其权利、义务均是空洞抽象的。这就如同一个身处国际机场入关者,如果既入不了关又退不回去,只能待在此“国际空间”,尽管在抽象的意义上其享有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但是,在其现实性中,除了个别方面,这些所谓权利、义务均为浮云。另一方面,个体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怀有一种天然的眷念情感,这种情感发自内心深处。也许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其多有不满,但在内心深处却极为珍视。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国家有一种内在承诺:尽自己一切可能维护与建设好生命家园。这种内在承诺会演化为一种对自己民族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这就如哈丁“救生艇”上的人,尽管各自有不同偏好与认知,甚至自愿牺牲自己,但有一种基本共识与承诺,尽全力不让救生艇沉没。正是这种共识与承诺,使“救生艇”作为整体获得希望与未来。一般说来,那些非本民族国家者不具有此种特殊的民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身份认同,缺失基本共识与情感,缺失维护与建设此民族国家的义务责任感。
民族国家是基于内部不同成员、群体间彼此承认与尊重构成的伦理共同体:承认并尊重此伦理共同体的基本文化价值精神,承认并尊重此伦理共同体的风俗习惯与生活秩序,承认并尊重此伦理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权利。这种承认不仅是个体间的,更是群体间的;不仅是社会的,更是政治制度的。恰如救生艇上的人,尽管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不同认知与偏好,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均彼此尊重权利,承认彼此的尊严与人格,不让救生艇沉没,彼此承诺及其基本信任,等等。这些构成了“救生艇”的一种价值精神与内在凝聚力。正因为如此,即便有人出于仁爱让渡自己的生命空间救漂落大海中的人,也会因为救生艇整体沉没的可能而不得不放弃。对非本民族国家成员当然也有承认问题,承认其人格、尊严及其权利,这种基本承认正是对非本民族国家成员施予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理由。不过,一方面,承认具有双向性,对那些不承认本民族国家及其基本文化价值有基本秩序者,对那些不承认他人财产权、平等人格及其尊严者,对那些不知感恩、尊重甚至反客为主、贪得无厌者,是否有特殊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问题?是否在仁爱实践中应有特殊考量?另一方面,对非本民族国家成员的人道主义救助仁爱行为有某种边界。道德义务不是教条,道德行为是实践智慧及其创造性活动。对非本民族国家成员的仁爱行为,只要不是出于幼稚、天真,就得承认存在某种边界。这种仁爱精神实践的边界主要有二。其一,以对本民族国家伦理共同体负责的态度实践仁爱精神。本民族国家这一伦理共同体是自己民族所有成员的生命家园,首先对本民族国家成员负责,在此基础之上对其他民族国家及其成员的不幸、灾难施予可能的人道主义救助。显然,这种仁爱、人道救助是有限度的。其二,不伤害受援对象的尊严、自我责任感与生产性精神,有助于受援民族国家及其成员对自己负责任,使其成为生产性的而不是寄生性的,进而是有尊严的存在。
原文参考文献:
[1]高兆明:《“仁爱”与“正义”:和解及其可能》,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3]Garrett Hardin,"Commentary:Living on a Lifeboat",BioScience,Vol.24,Issue Oct.1974.
责任编辑: